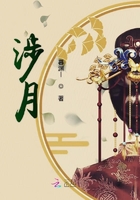滂沱大雨一直到太阳落山才停下,整个金陵城被冲刷得干干净净,郁闷了几日的暑气一扫而空,这舒爽宜人的时刻,凌云书院里,却有一个学生要走。
不论如何,乘鹤在这里也学了些时日,多少有些学子与老师是喜欢她的,得知她要走,纷纷来送行,皆惋惜地说:“好好的,为什么要走?”
但很快,施夫子等人就张榜告示,指叶乘鹤成绩低劣,且屡次违反书院规章,故而未能通过试学,勒令其即日离开。
众人唏嘘,不知乘鹤究竟如何冒犯了夫子,凌云书院已好些年不曾劝退过学生,且对一而再失踪不见的钟子骋也是诸多包容,这一次,竟做得那么决绝。
可笑的是,叶乘鹤只知道允澄要自己走,却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己走。
“这么晚了,又下了大雨,城外的路一定不好走,今晚你去容家住一宿,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允澄又这样命令乘鹤,而后者更照单全收。
子骋在一旁暗暗奇怪,在慎龙寨比她爹爹还霸王的叶乘鹤几时变得这般逆来顺受?自然先前已明白了一些事,对此便了然于心了。
于是叶乘鹤被允澄所派之人“押送”至容家,恰巧那会儿容许夫妇带着女儿和采薇等出门逛街乘凉,冯梓君便接待了,她对这个孩子并不知道,只是奇怪照面时分明是个小子,一转眼竟换了女儿装。年轻人的事她算是琢磨不透,又是太子所托也不便多问,故容她和雨卉住一间屋子,便不再管了。
雨卉有了同龄的伴儿,自然喜欢,两人早早洗漱罢,各抱了一床毯子在窗下的躺椅上坐着喝茶吃瓜果,本说些无聊的话题,叶乘鹤却突然问道:“你喜欢钟子骋那小子,是啥感觉?”
听这样直白的问题,容雨卉的脸儿扑红,手里捏着的香瓜不知是吃是放,扭捏之态叫乘鹤看得肠子痒痒。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见不到会想他,无事便担心他是不是好,若能让他好,做什么也心甘情愿。”雨卉说完这番话,红晕已经从脸颊顺延至了脖子根。
叶乘鹤满腹狐疑地看着她,许久才问:“真的?”
雨卉羞赧地点了点头,忽而一个激灵问:“叶姑娘作甚问这些?难道你……”
这回轮到乘鹤脸红了,她大声嚷嚷着堵回去:“我不就是问问你么,不过你说得还真没错,钟子骋那小子平日里也动不动就提起你,让我和殿下都觉得心烦!”
“殿下?”雨卉一愣,“叶姑娘知道了?”
“是啊,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要离开书院?”叶乘鹤脸色不展,捧着茶杯转过脸去,只管呆呆地望着天空。大雨过后,一切都那么澄净,好像一眼能看穿这深蓝色的夜空。
实则雨卉不明白,她不晓得叶乘鹤知道了允澄的身份与她必须离开书院有什么关系,不过本就觉得女子混迹在全是男人的书院里是不妥当的事,故而也不会去计较。
书院里,子骋终于在叶乘鹤空荡荡的屋子里找到了允澄,允澄笑语:“这疯丫头一日不见,便想了。”子骋不语,又听他说:“等过了这些事,想娶她。”
“殿下,您知道乘鹤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子骋还是将心中所虑说了出来。
允澄悠悠地看着他,“总不见得我喜欢的女人,都得不到吧。”
子骋无语,默然。
夜色清美,容许夫妇与采薇、奶娘迟迟才披星归来,穆穆早已扛不住疲累伏在父亲的肩头睡着,这小丫头毕竟是大了,份量不轻,除了容许抱得动,其余人怀抱片刻便支持不住了。
佟未笑言:“难怪这丫头跟你好,关键时刻还是爹爹靠得住。”
容许自然骄傲,将女儿交付给奶娘后,便与妻子回房去,合上门,见佟未忙碌着铺被褥,立着看了须臾,忍不住问:“那会儿我若没出现,你会对恒聿说什么?”
佟未一愣,手停在当空,丝绸被面被她的手指抓着,出现痛苦的褶皱。一整个下午丈夫都没提过那件事,晚上逛夜市时也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为何突然提这个?
放下被褥转身来,看一眼丈夫,摇头,低语:“不知道。”
容许一步步走来,轻轻握起妻子的手:“可是你知道么?那一刻我后怕,后怕如果我没有出现,就再也要不回你了。”
佟未的心被硬生生揪起,她笃定自己那一瞬对恒聿有的只是兄妹间的情感,她只是伤心了、难过了、感觉无助了,才会想去找一个地方倚靠和逃避,可是这小小的一个念头,竟给丈夫带来如此深重的伤害。
“我错了……相公对不起,我错了……”佟未哽噎,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容许静静地望着她,没有如以往那样伸手拂去她的泪水,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他想要一个答案,必须由佟未亲口告诉他,方能安心。
可是无问何来答,但那样的问题,他真真问不出口,倘若未儿与己心灵相通,是不是该明白此刻自己的想知道什么?
“丫头,我今日真吓坏了。”这句话容许在心里说,不在口中说,那是他的骄傲,作为人夫的骄傲。
佟未的手在丈夫的掌心里微颤,她不敢抬眼正视容许的眼睛,她害怕从那里面看到忧伤,她娇声啜泣:“那些话都不是真心的,对我而言那些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好,重要的是以后、将来、一辈子能在你身边。我跟他早就结束了,从我在你面前掀开红盖头起就结束了……不要生气,我们都不要生气……好不好?”哭着扑在丈夫胸前,与其说容许害怕妻子的心会远离,不如说佟未更怕丈夫会真正离开自己,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把生命都系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她终究是明白自己的,高悬的心终于归位,容许知道这份幸福是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谁也抢不走的。
炽热的红唇贴上那张委屈害怕的脸颊,一点一滴地吻去酸涩的泪水,那柔软的身体在自己的怀里微微蠕动着,娇美的红晕从双颊开始向周身漫延,打横将娇妻捧起,轻轻地放在床榻上。佟未羞涩地别过头,宛如当年的模样……
深夜,万籁俱静,雨卉已卧床而眠深深睡去,躺在一侧的叶乘鹤却无心睡眠,似总有秋波盈动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那从窗户投射进来的光影,从掠过的黑影来计算因被雨打而飘落的树叶,一片,又一片,期待着下一片……
“我们,真的不会再见?”问罢,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在衾枕上晕出一抹忧伤的痕迹。
如是,乘鹤几乎一夜未眠,翌日起来眼圈儿发青,神色恹恹的,不明就里的雨卉还以为是她病了,想来找二嫂商议是否为她请一位大夫,却见兄长嫂子的卧房门紧闭不开,采薇微微笑着示意她暂莫打扰。
雨卉分明记得那夜他们吵得厉害,怎么一转眼便和好了?自然是盼他们好的,可这样委实奇怪,回到自己的屋子难免嘀咕了两句,彼时乘鹤也穿戴整齐想去见容许并询问自己之后的“安排”。听雨卉嘀咕,便问:“将军与夫人和好,难道你不高兴。”
雨卉则道:“自然不为这个,我只记得那一日听他们吵,好像我二哥又要有什么大事情要离开,我二嫂似乎因那个怒得,还有就是牵扯到我们家一些过往的,连我也记不得的事情。”
“这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二哥二嫂再和睦,也会像牙齿舌头那样偶尔有个磕绊,你就别担心了。”乘鹤胡乱地安抚雨卉,却不料引来她那句话。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子骋,每每我二哥有要紧的事情,大多是要扯上子骋的,我不想他总不能在凌云书院安心念书,可我也知道,他跟着太子,怎么可能安心呢?”
雨卉叹叹则已,乘鹤却记在了心头,她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这些日子容许在书院近进出出的,总不会无事找太子叙旧吧。
“可他有什么事呢?”乘鹤自问,又愤愤自答:“与我何干,人家已赶你走了。”
雨卉似听见她嘀咕,又听得不真切,见她脸色不好神情忧虑,便不敢多问,无论如何她都没敢往那一层上去想,大抵她心里对太子生不出情感,便以为天底下的女子皆如此。
然不知,叶乘鹤一颗芳心,已悄然系在了允澄的身上,任谁也牵不走了。
很快,允澄与子骋从书院而来,容许夫妇也起身准备好了一切,众人几句客气的话说得不咸不淡,便见恒聿姗姗来迟,自然他另有任务在身不便与外人道。
似乎一切都是恒聿在安排,雨卉帮着乘鹤收拾好细软,众人便要送她出城了。
允澄就在面前,然碍于那么多的人无法亲近说话,乘鹤心里头一肚子的疑惑和难过都不得发泄,好不容易忍下来,但素昔爱将事情写在脸上的她,还是摆了一张臭脸。
允澄竟后知后觉,到了城门还问她:“你到底是不是身体不好?若这样,不如再等等回去。”
乘鹤那么多话要说,被这么一问,便完全变了味道,只是充满火气地顶回去:“这个地方与我不合,还是早早走了好。”
允澄这辈子都少有人敢这么与他说话,被这么一顶撞,反不知说什么好,心念来日方长,不在乎这顷刻间的言语,便好言哄了几句,就让恒聿安排好的人送她出城。
乘鹤临登车时,还不舍地望了允澄一眼,然后者却只是不带任何情感地朝自己挥了挥手,这般叫小妮子甚伤心,他便是露出半分舍不得与思念……呵,叶乘鹤啊叶乘鹤,分明是你自作多情,人家太子爷又岂能和你有一样的心思?
莫名地,叶乘鹤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只以为就此离开了,一切便结束了。
然,她的离去,只不过是另一段的开始。
马车出城门后不久,众人便要打道回府,容许携妻妹回府,恒聿送允澄回书院,允澄上轿时,却突然喊了佟未,她缓步走过来,笑问太子何事,允澄却将她引到一边去不知低语什么。
恒聿静静地看着,忽而周身感觉异样的警惕,本以为是容许对自己有敌视的目光投过来,然抬首去看,却见他目光游走、神情紧张,眼睛似乎在周遭的楼阁之间寻找什么,不由得跟着他的目光而去。便就在电光火石间,两人都飞身出去,扑向了一边说话的允澄和佟未。
“嗖嗖……”是利箭划过空气的刺耳声。
随即有街边妇孺惊声大叫,慌乱中,有人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