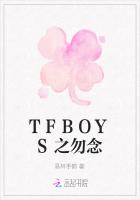“金哥儿,我带人来看你了。”丫鬟轻声细语,好似怕惊扰了什么。
沉寂,无人答话,那丫鬟也习惯的样子,对我颔首:“姑娘就在屋内椅子上稍坐片刻,想必苟嬷嬷不久便有吩咐。”
话毕知礼地退下,倒比苟氏多了几分风范。
我有些好奇地四下张望,不过是下意识,其实依旧黑暗一片,不过这屋里感受不到一点温度,想必阳光也是被遮得死死的,徒留一点冰冷的绝望以及窒息。
是绝症吗?以苟氏的眼界,已经到了买妾这样非冲喜不可的地步。
我竖起耳朵,静静听了许久,才感受到不远处微弱的呼吸。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出于同病相怜的感慨,我一步步地摸索过去。
尽管铺了厚地毯,我微不可闻的脚步声还是被对方发现,只听窸窸窣窣衣料摩擦的声音,好像撑起身子探望。
“咳咳——”也许动作过大,惹得他一阵咳嗽,而且停不下来,似乎肺里装了个满是破洞的风箱,一吸气就是破碎支离的呼呼响。
这样的情况,不是痨病就是哮喘,不管哪种,在古代,都被称为不可治愈的绝症。
很想安抚几句,但开口却是“咿呀啊”,对方动作蓦地停下,咳嗽声渐歇。
我扶着床柱在床边的椅子坐下,脑中浮现的是一个形容枯槁面黄肌瘦的男子形象。
“你不会说话?”长久的沉默后,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一愣,然后点头。又是窸窣的声音,那人该是艰难而缓慢的坐起来。
“你是新来的丫鬟?”
我摇头。
“...冲喜丫鬟?”
他意料之中地询问,让我惊觉,两者同样是丫鬟,不过多了个前缀。看来苟氏一家从来认为小妾和丫鬟是同等的,怪不得才给十两。
我不愿点头,就这么坐着,最初的同情消散不少。
“呵呵,咳咳!”他却笑起来,又是止不住的咳嗽,“咳咳...你不是自愿的吧?”
那语气中不知为何有种不易察觉的凄凉和自嘲。
我诚实地点头,他咳得更厉害,把院子里的苟氏都引来了。
一见儿子这情况,勃然大怒的苟氏照面对我就是一耳光,被我早有防备地躲开,更是怒不可遏,嘴里的脏话连珠炮般投出。但是顾及儿子安危没再动手,只是叫桂丫头去找大夫。
“要是金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看我不抽皮剥筋让你陪葬!”恶狠狠的对我说完,立马慈爱又担忧地拍着儿子的背。
我冷眼旁观,大夫想是相熟的,来的迅速,看了病情只说是老样子,开了些调理的药便走了,吩咐情绪不可再过激动。
这茬刚过,苟氏便想对我发落:“定是你说了不该说的或做了不该做的,才惹得我儿病情加重,你这个贱婢!我真是眼睛生疮了把你买来!”
可不是生疮了吗?我暗道,只听她冷厉地吩咐:“桂丫头,找府里几个年轻力壮的家丁来...”
“娘。”虚弱的声音蓦地打断,“不是她的错,是我自己不争气...别责罚她。”
“金儿你!”虽生气他帮着外人,好歹是软了语气,“你帮她作甚?莫不是被她美貌迷了心窍?”带着些赌气成分。
虚弱的声音一顿,有些无奈:“娘,你怎么又胡言乱语,我们不过初次相见,不到须臾你便进来,哪有时间被她‘迷惑’?”
苟氏被儿子堵得一噎:“哼!总之她就是来伺候你的,别妄想给个名分什么的。冲喜丫头又怎样,奴婢就是一辈子的奴婢。”
到底是不会处罚我的意思了。苟氏没好气地叫我去端药,可是因为眼疾我犹豫了。
“怎么?这点事都叫不动你?我还买你来干嘛?”苟氏又刻薄地开始叫唤。
“算了娘,她初来乍到,对府里所知甚少,还是让月桂去吧。”
苟氏拗不过,没好气地对我冷哼几句,外头有人找才出去了。
而我察觉到他对我有意的偏帮,不禁奇怪。
“我叫秦金。”他介绍自己,语气没有多犹豫,“你...眼睛也看不见?”
我有些吃惊,他居然发现了?是作为一个病人所有的敏感吗?
我一颔首,没有掩饰,因为时间一长早晚会被发现。
“呵呵,”他第二次笑,依然是虚弱的,“如此说来我俩真是般配。”
他大胆的地说着玩笑,我却笑不起来。
“抱歉,我并不是幸灾乐祸,只是...”他以为我生他气,解释道。
我微微点头表示理解,他又问:“你会写字吗?”
我迟疑了下,还是点头,尽管难看,好歹算会写吧?
“那便太好了,以后你想说的话就写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交流了。”感觉秦金像终于找到玩伴的孩子般开心,有种淡淡的心酸。
之后由于秦金的庇护,我没有受罚,并且月桂告诉我,秦金的病情恶化,偶尔发病就像疯子,可怕至极,苟氏就是被吓到了才急急忙忙寻冲喜丫头。
多次警告我后,苟氏置办起简陋的婚礼,或者说,冲喜仪式。请来神婆做法去除晦气,我被要求洗了一天一夜的澡,结痂的伤口已经泡软翻皮,脑袋也晕乎乎的。
仪式前一天,我遇上秦金发病。因为无法看见,所以那种凄厉的叫声越发刺耳,像某种野兽被围攻的绝望大吼,整个院子都能听到,伴随惨叫的是不断以头撞墙的沉闷声,以及结实的木床快要散架的悲鸣。撕心裂肺的咳嗽始终是主旋律。
苟氏带人手忙脚乱地把秦金绑起来,阻止他自残行为,感觉像对待一个吸-毒成瘾的人。
于此,苟氏更迫不及待地送我们入洞、房,可是秦金事先跟我承诺,他不会碰我。那种语调中蕴含着淡淡的自卑与痛苦,他是不想拖累我,尽管我又瞎又哑。
我不知道苟氏为什么生得出秦金这样的儿子,或许真是上辈子积的福。
也许真是喜事带来的祥瑞,据月桂说,秦金自仪式以来一直红光满面、精神十足,我嘴上虽然微笑,心里却不太好受,我怕是...
我每日给秦金背诗,唱歌,偶尔也写字,当然他会毫不客气地嘲笑我的字迹,谈笑间如相识多年的朋友,鉴于我安静又少走动,最重要是逗得自家儿子开心,苟氏对我的成见放下不少。
然而这一天,秦金似乎特别有精神,竟然自己下了床,他牵着我逛园子,外人以为是我扶他,殊不知是他在为我领路。
“我曾经是齐二少的伴读,后来得了病才被特许待在馨园里养病,说起来,二少爷对我有大恩的。”他絮絮叨叨,不时咳上一声,我感受到他单薄的身躯在颤抖。
绕了许久到了一处院子,秦金敲门,开门之人见他大吃一惊:“秦金!怎么是你?你不是在养病?”
“呵,想二少爷了,便来看看他。”
那人想是熟识的,忙邀我们进去,急匆匆去禀报了。
“阿金!”一个清润的男声高兴地迎上来,看到他语调立马低下去,难过道,“你你,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
“呵呵,”秦金不甚在意,“生病之人都是这样,二少爷不必伤心。”
“这位是?”齐二少才注意到我,“莫非,就是苟嬷嬷找来的...”冲喜丫头毕竟不是光彩的事,良好的教养让他没说下去。
我和秦金都心领神会,他却是笑语:“这是我的新朋友,叫秋秋。还不拜见二少爷?”最后一句却是对我说。
我依言福身,大致点了点头。
“免礼。”齐二少有些激动,“阿金,我们许久没见,今日定要彻夜长谈。”
我本想提醒,秦金的身子经不得整夜的折腾,却感觉他压了压我的手:“秋秋,你就在这坐着等我。”
然后他和齐二少进来屋,我以为我要苦等一夜时,没多久他们就出来了。
“阿金,你放心,你拜托的事我一定办好。”
“如此,就多谢二少了。”
秦金带着我告辞,一路上,我却感觉他的身子越发佝偻,有些不堪重负的样子。
我张口“啊咿呀”想问他还好吗,他竟听懂了,安慰我:“老毛病,不碍事。”
我只觉得心上越来越沉,直到第三日清早,我照常叫他起床,却发现他身体冰冷一片,甚至有点僵硬。
我瞬间失去了呼吸,轻轻地触了触他,确定已无半分生机,然后双唇颤抖地出去叫人。
被我巨大的拍门声吸引而来的众人,一进来也发现不对,苟氏瞬间爆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嚎。
失去儿子的母亲是疯狂的,苟氏把秦金的死都归咎于我,对我拳脚相向,要不是及时赶来的齐二少,我兴许会被打个半死。
齐二少把我带回明轩院,我才知道秦金拜托他的,竟然是给我自由。以他的敏感,不会察觉不到我眺望墙外的渴望,以及对墙头阳光的痴迷。
有他这样一个朋友,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却又是无尽的悲伤,这段友情太短暂,短暂到我感觉才遇到他,他就已不在了。遗憾的是,我永远没法知道他的长相。
他曾说过,此生他是来赎罪的,等到被求宽恕的那个人,他便可以安心的离开。
我以为他有意中人,可是相处中他从没透露过只言片语,所以这句话大概是个永远的迷了。
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死别,并没有让我过多的感伤,相反觉得豁然开朗,朋友是用来祝福的,不管这个世界再冷酷,总还是有温暖的地方不是吗?
齐二少问我想去哪,由于金吾阿九之事,我暂时不想回风祈,便说让我好好想想。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了解到齐府在琉璃京城是个怎样的地位,京城四富之首,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进齐府,就为了那丰厚的职薪,以及极少能参加顶级宴会和大人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
抱歉,因为看电视剧耽误了时间,更新晚了,请亲们尽情的鞭笞吧~~只求爽过后留下各种票,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