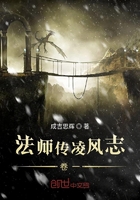第十二章 今朝有酒明朝醉
“孜禹,你不气我了?”
望着站在群群兵士中那个恍若战神的男子,远远的,君卿鸢就带笑地问候了句。还记得呀,她不肯跟他离去,他那副青青紫紫的脸色着实吓坏了胆小的弘儿。
刘孜禹眼神莫测,只是定定地看着她的一声脏污,眼角里满是戏谑的味道,“如果我还气你,怎么办?”
“那就罚我一整年不写毛笔字如何?”可爱地歪歪头,她狡黠一笑。说话间,她已近在眼前,只可惜中间隔了好多带着武器的士兵,还有个怒目而视的矮个男子。
刘孜禹作势思忖了下,坏笑地摇摇头,“我觉得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
“什么?”
“做我一辈子的老婆如何?”
老婆啊,她常常说夫人这词儿太慎重,完全比不上老婆的亲昵自然,她只愿做老婆不要做那高高在上的夫人。他一直都知晓的,她是为了吕岄,那个做了他三年夫人的可怜女子。
她摸着腹部笑得无比甜蜜。
“够了!”被忽视得够彻底的吕产终于怒吼出声,眼中的怒火熊熊燃烧,最好是烧掉眼前这对可恶的男女!他愤然转身,用力地将君卿鸢扯到身前,也不管她是否吃痛地扯动嘴角,“朱虚侯,人你也见到了,还不快交出虎符。”
刘孜禹陡然阴沉了脸,动也不动地看着吕产。
无形中,一股强大的压力笼上吕产心头,肥胖的面皮抽了又抽,斜眼瞪向身前表情煞是无辜的女子,手不由自主地松了松。随即,脸上又现蛮霸之气,不管不顾又紧扯住她的身子,狞笑道,“朱虚侯,你再不交出虎符,我让你的心头肉更痛!”
刘孜禹像是认输地叹气,伸手出袖中拿出那个绣囊。紧接着,一道金黄色的奇妙弧线直直地向着吕产的方向滑了过去。
吕产心喜,急忙抖着肥胖的身子上前去接。那一瞬间,一道更快速的光影从他身边一闪而过。
结果当然是众望所归的皆大欢喜。
吕产得到了绣囊,刘孜禹拥着佳人入怀。
君卿鸢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轻声问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忘了告诉你,那秦虎恰恰是个做铜制器皿的高手,那个小玩意儿,对他来说,实在是不算什么。”同样在他耳边低语。
另一旁,吕产手持虎符笑得无比猖狂,“哈哈哈,朱虚侯原来是如此愚蠢,你以为我会放了你们吗?来人呐,给我押下去,等我攻破汉宫的那日,我要你们与汉宫陪葬!哈哈哈……大汉江山是我吕产的了!”
而愚蠢的朱虚侯只得耸肩拥着佳人,很是顺从地被兵士押了下去。
一待身旁无人,君卿鸢就好奇地端坐刘孜禹身前,“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你知道我朝虎符必须骑缝刻铭,只有两方合铭后才可以调动人马……”说罢,他亲昵地点住她的鼻子,“提示完了,猜猜看?”
“你老人家还真是高估了我了呀。”睨着他,君卿鸢一下子也来了兴致,“那上面没有刻铭?”
“再猜。”轻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任着馨香满怀满足地叹息道。好久没有这般自在逍遥了,似乎又回到在长风街的日子里,偶尔想起,恍若隔世。
“铭错了?”倚在他厚实的怀里,她突然感觉到很是困倦,哈欠一个接上一个,止不住了,“不猜了,不猜了,你直接说给我听。”
贪看她撒娇的俏模样,他一时间挪不开视线,许久才在她不豫的瞪视中,举手认输。
“那铭确实有些差错,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当吕产拿着那些虎符与另一半也加工过的虎符合铭时,手握虎符的将领们会与他假意合作,待全部兵士汇集攻打汉宫时,真正的虎符一出,所有将领立刻‘弃暗投明’。”
那结果是……她瞠目结舌。
替她捡起掉落的下巴,在那唇上印上重重一吻,“聪明!到时候吕产就成了被反抄的饺子,不需要损耗一兵一卒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然后,我们就可以找个安静地地方生养出一只只的小鬼头,看着他们变大,我们慢慢变老。”
“孜禹……”很想感动地埋入他的怀抱,可是不能。君卿鸢睇向他眉飞色舞的脸,务实的耸肩,“那弘儿是不是也和我们一起?我同意让他离开皇位,但是我不会让他待在有心人的监视里。”
“……好吧,我会想办法。”
君卿鸢满意的颔首,眼睛瞟向那个在他们身后神情落落寡欢有一阵子了的女子。她发誓,她绝对没有拈酸吃醋哦。只不过她家这口子的魅力未免太好了些,老是招惹一些失意女子,像是未婚有孕而心上人不告而别的吕岄,又像是眼前这位看透人生百态在青楼里摸滚跌爬了许久的美娇娘。
是他太好,还是她的眼光太烂?
唉……想叹息呀。
“睡着了?”察觉到她的心不在焉,他戏谑地低首看她。
不理他的取笑,她直接将他的头转向后方,“有人找你。”
“打扰了。朱虚侯。”桃喜盈盈作揖,举手投足间是百般妩媚的风情,抑郁的轻愁越发使得她楚楚可怜了。
可惜某人偏偏不欣赏这幅美人图,面孔冷得像块冰,眼里是慢蕴的风暴。
君卿鸢暗自拧了下他的手臂,不知道是不是不够重的缘故,某人还是一张死人脸。
“桃喜,是我们打扰了才对,我们三人怕得待在这里会有一段时间了。呃,我们继续到前院散步顺便种草如何?”
不知道那棵野草怎么样了,她记得刚才走的时候似乎有听到花盆破碎的声音。
桃喜也不答话,只是痴痴地看着某人的脸。压抑了许久感情才对着正主儿时,完完全全地流露出来,浓烈而绝望的爱呀。
君卿鸢翻翻白眼,看来那半日的说教算是白费工夫了。
“卿鸢,醒醒!醒醒!”
君卿鸢睁开惺忪的睡眼,迷迷茫茫地坐了起来,“怎么了?”
肚子越发大了,这几****好似睡不够般,真怕哪日里孩子就这么在睡梦里就这么生了出来。最近她突然想起她那对极度不负责任的爸妈,不管他们如何,至少他们生下了她。
刘孜禹将她扶坐起来,为她穿上厚重的曲裾,“吕产带人围住了这里,我们得出去,否则就迟了。”
“为什么?”窗外,还可以看见外面闪闪烁烁的火把,耳畔尽是吕产气急败坏的怒吼以及杂乱不整的脚步声。
“因为他临死也想找个垫背的。”
她陡然一惊,抬首望他。
将貂皮大氅牢牢地裹住她的身子,快速拥着她往外走,时不时戒慎地看向身旁。
“刚才盃耳送来消息,今日汉宫一役,吕产兵败如山倒,带着残兵逃脱,大哥他们正到处缉拿。现下看来,他是不甘心了。”
来到一处似乎颤颤巍巍随时会倒塌假山前,刘孜禹上前搬开一块石头,一个一人高洞口露了出来,阴阴深深的,看不到底。
“呀!”君卿鸢诧异地捂唇轻呼,不置信地低叫,“你早知道这里有路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才走?”
他睇了她一眼,“因为你想。”
君卿鸢失笑地瞪着他,心里的蜜却快要满溢了出来。她真的很享受这种懒懒散散只有彼此的平淡日子,没有其他,只有幸福。可惜,他是汉朝的侯爷,她不可以那般自私。所以她从未提过。
原来,他还是知道的。
被推着先走入洞口,昏昏暗暗中走了几步后她猛然回头,“孜禹,我们忘了桃喜!”
他撇撇嘴,还以为她会走出山洞时再想起的,“她是吕产的人,他不会伤了她的。”
“孜禹!”警告。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找她。”
“不要,我不要在这里等,要去就一起去!”君卿鸢摇首,灿若星光的眼里是不容置喙的固执,“我不是女子,我不是孕妇,我是你的老婆,所以,我要和你一起!”
四目相视,妥协的一方是毋庸置疑。
他宠溺地拥住她,“我认输了,我的老婆。”
外面火光通天,隐隐有兵器相击的声响,接着,就是响彻天地的厮杀声。战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打响了!
待他们走出洞外时,到处都是吞噬着房屋的橘红色火苗,炙热的火气一阵阵地烘烤着他们的皮肤,像是最无法无天的恶魔。
“孜禹!她在那里!”透过浓重的烟雾,君卿鸢咳嗽连连,手却指向他们正前方的走廊。那里,一个红衣女子落寞地站着,自顾自地看着手中那一盆野草,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她过来,别担心,只有十来步的距离。”将她强塞入洞里,他疾步飞跃过去。
嘈杂的战斗声离这里越来越近,似乎一个转身就可以见到鲜血淋漓的战场。
君卿鸢心惊胆战地用力捂住嘴,生怕一个出声就将那些杀得红眼的兵士们给引了过来。
她看见孜禹到了桃喜那里,似乎有些争执,那桃喜泪光盈盈却连连挥去孜禹的手。目光错眼间,不知何时,吕产狞笑着站在不远处的,手中的弓箭想着孜禹高高举起!
陡然间,所有的声响都消失了,全世界死寂一片。
她似乎有在叫什么,可她听不见。她似乎有摔倒,但是一点都不痛。她所有的目光都集聚在前方走廊上两人身上。
弓弦紧绷的声响,一道箭镞穿过空气,冷冽流光,声音破空得可怕尖锐。
“不!”
她终于找回自己的耳朵了,耳畔尽是她自个凄厉的尖叫声,极度尖锐亦是极度惊恐。
那箭簇直冲向孜禹完全没有设防的后背!
这是她昏迷前最后的意识。
公元前178年,少帝刘弘染疾,身故前让位于代王刘恒。刘恒仁善勤勉,是为文帝。
汉宫一役,朱虚侯立下大功,文帝特意封其二千户,黄金千金,晋封城阳王,创建城阳王国。
“不,不……不!”尖叫!
猛然睁眼,冷汗潺潺地湿透一身厚重的衣服。一转眼又是春天了,清冷的空气中微带凉意,但毕竟不若冬日冷冽。
瞪着翡翠色的床帏,晃晃悠悠的涟漪间,一时间有种莫名的错觉。去年的是是非非都只是一场梦而已,梦醒了,她还在长风街的药铺里,平静地过着他们的日子。
可惜呀,那不是一场梦。
时光荏苒,一下子两年都过去了。
她现在身在许县,齐国里一个偏远的城镇里,民风淳朴,单纯得像个世外桃源。
有人掀了竹帘走了进来,是一位中年农妇。虽然粗衣陋装却还是掩不住她的美貌与气度。
“怎么了,卿鸢?”农妇将一碗麻油鸡汤端放到桌上,关切地上前问道。
“没事,做了个噩梦而已。琦姨,我可不可以不喝?”厌恶地扫了眼麻油鸡汤,她下了床榻,“弘儿和柳叔又抱着宝宝出去打猎了?”真是没见过这种父子,居然打猎还要带着一只不足两岁的小女娃,真是苦了她家宝宝了。
“嗯,那孩子现在看什么都新奇得不得了,等再过个一年半载他就要喊苦了。那野鸡也是弘儿打来的,说特地为你补身子用的。你可别辜负他一番心意。呃,你放心,他们爷俩不会摔着宝宝的。”
那小子哪是一片心意,还不是想看她的好戏。君卿鸢撇撇嘴,不在人家母亲面前说儿子的坏话,说了也是没用。转入屏风后,她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换下这一身湿漉漉的衣服。
刘琦替她拿来一件绯色曲裾,担在屏风上,看着她的影子,突然叫了一声。
“卿鸢。”
“嗯?”
“我一直想对你说声对不起,当初是我太自私了,我让你一个小女子去保护我的儿子,压根忘了你的幸福。我感谢老天,更感谢你。真的!你不仅保住了弘儿,还让他平安回到我的身边……”
君卿鸢低低呻吟了声,脱衣服的动作也慢了下来,“琦姨,你都说了许多遍了,当初可是我是自愿的,况且,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和小诡,我们现在早就是一堆白骨了。”
“可是……”
“琦姨,你帮我去小诡那里取件衣服来好吗?这衣服也太厚重了些了。”
“啊,好!”
房屋里总算恢复了一片宁静,君卿鸢侥幸地叹了口气,继续脱那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呼,这汉服虽然飘逸漂亮,可未免也难穿了些吧。
呀,她最近又胖了好多,肚子又隆起来了。盯着小腹,她很是悲惨的叹息。
咦,等等,她好朋友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着?
不在意间,竹帘又轻轻掀起,一个头戴毡帽的人走了进来。望着屏风上慢吞吞换着衣服的影子,毡帽下的眸子突然暗沉了好多。他脱下毡帽,悄悄地走了过去。
“谁!”猛然被人拦腰抱住,君卿鸢直觉想尖叫,但一察觉到那熟悉的气息时,紧绷的身子顿时绵软温柔了下来。
“怎么有空来了?”君卿鸢仰首瞟向埋在她肩窝处的男子,语气酸酸溜溜的,“真是稀客。”
“淘气!”刘孜禹抬起首宠溺地捏了下她挺翘的鼻尖,“我不是天天都过来?”
“是是是,您老人家的一日是半个时辰不到,和我们的十二个时辰不一样。”
“放心,以后不会了,我保证满十二个时辰。”
君卿鸢猛然转身,惊喜地盯着他,“你可以死了吗?”
“事实上,我这个城阳王现下已经病入膏肓,不过三日,就得一命呜呼见先帝去了。”他叹息地点头,着迷地看着眼前一片迷人窈窕的好风景。以他老婆的身姿,实在是看不出生过一个宝宝了。再不死,他怕他老婆这只美丽的红杏就要被人给觊觎去了,“你刚才又做噩梦了?都已经过去了呀。”
“可是,我还是忘不了呀,那天,那支箭就这么直直地向着你的背后刺了过去……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不是桃喜用花盆挡了下,那箭就不会仅仅射入他的肩部了。回忆往昔,她眼神略微黯了黯,抚上他受伤的肩部,“孜禹,答应我,不要再吓我。”
突然笑了起来。打死也想不到,那桃喜居然因为那一箭而突然醒悟,继而开出一家纯卖艺不卖身的书斋来,两年下来,倒也是口碑斐然。
“我保证。”一双手慢慢地抚上她****的肩,细滑的皮肤柔柔嫩嫩的像是块可口的豆腐,引得他垂涎三尺,“只要你答应我,等城南王死了以后,我们就离开这里好不好?”
这儿人太多了,太多的人喜欢围着他聪明的老婆,使她都没有空闲理他这个正牌老公了。再不走,他怕他会相思成狂。
“为什么?我倒是觉得这儿挺好,小诡、弘儿,还有吕琼,甚至桃喜儿开的长春斋也靠着这儿,多热闹呀。”狐疑地点点他一动不动的身子,“孜禹,你在听我说话吗?”
循着他的视线望去,恰恰看见她不知何时完全****在空气中的身子,顿时绯红满颊,直直地捂住他侵略的眼,“色狼,不准看!”
刘孜禹邪佞一笑,笑容里是忍了许久的暧昧,眼神越发深沉闪亮。
在她的尖呼声中,将她打横抱起。
春日里,屋内屋外春意盎然,谢绝打扰。
公元前177年,城阳王刘章病逝,表字“孜禹”,谥号“景”。
长长的驿道看不到头,细细窄窄像是一条直线了。直线旁,即是苍茫无际的耕田,绿绿油油是生命的迹象。
夕阳西斜,苍浑的太阳是古朴的天神,慷慨地将金色光芒恩赐四方。
傍晚时分,驿道上人烟稀少的只有一只毛驴晃晃悠悠,潇洒得不得了。再细看,才发现毛驴身上还侧坐着一女子,一颠一颠颠得她昏昏欲睡,眼眸半合半开。毛驴左侧,男子抱着酷似毛驴上那女子的宝贝女儿,私语窃窃,生怕惊扰了女子的好梦。
“爹,我们去什么地方?”
“随你娘,等她醒了我们来问她。”刘孜禹摸摸宝宝的头,做出噤声的动作。
半晌,宝宝又扯住亲亲爹爹的衣服,凑到他耳边问道:“爹爹,小诡姨说娘改了名字,为什么要改呢?原来的名字不好听吗?”
“是呀,不好听。”刘孜禹轻笑,也不管宝宝是不是懂,自顾自地说着,“卿鸢卿愿,好名字呵!”
望着女子的眼,是毫无遮掩的柔情辗转。
毛驴悠悠前行,前方的广阔的天涯。
(完)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