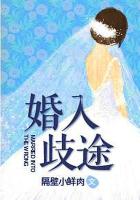年后,庄晓梦给朵晶联系了一下,一块去见那位高人,朵晶带她来到一座寺庙,到达寺庙门前,她看见门楼上写着“枫林禅寺”。
走进禅寺,她发现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普通寺庙,道路两旁微弱的路灯把这座四合院建筑风格的小庙隐隐展现在眼前。院子中央的香炉还残留着善男信女们进香的星火,四周殿堂的门都关着,偶尔见到匆匆行径的僧人,转眼又不知道拐进了哪扇门。小和尚把她们引进了后院的一座瓦房,房里桌椅板凳床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简朴却不穷酸,没有一件多余的摆设。
小和尚说:“施主请休息片刻,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待清除一路风尘之后,请到隔壁用膳!”
她们随着小和尚来到隔壁的房间,一股清香的米粥气味迎面扑来,看见一位身着袈裟,脑门儿锃亮的和尚正坐在饭桌旁的一张椅子上,静心看书。和尚仿佛听见了她的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他抬起头来,起身行礼,嘴里念念有词:“阿弥陀佛,施主远道而来,悟明不胜荣幸,请先入座用膳。”
庄晓梦惊呆了!
这不是阮浩波吗?虽然剃光了头发,但一看就是阮浩波,明明是阮浩波,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这个慈善谦和的和尚跟他曾经认识的那个阮浩波联系起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一阵强烈的意外、反差、崇敬仰慕混合起来的感触从她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这就是佛门的力量?
她条件反射似的发出一声:“阮……”马上想到,人家已经出家了,又改口叫道:“悟明禅师。”
这顿饭庄晓梦吃得很沉重,她每咽下一口饭菜,仿佛都有一个声音在她耳边轻轻地吟诵:“阿弥陀佛”。在她吃饭的工夫,阮浩波一言不发地静静地翻阅着手里那本线装的,可能是佛经之类的书。
茫然中的庄晓梦时不时地发愣出神,阮浩波在她身边,却静得出奇,脸呼吸的声音都没有。
悟明放下手中的书,起身为她收拾碗筷,“庄施主吃好了?阿弥陀佛!”
庄晓梦赶紧起身把碗筷收拾好,盘坐在他身边,说:“悟明禅师,我心里有很多结,希望您给我指点一下迷津。”
悟明淡定地说:“我来这时间不长,但已经有一部分施主来找过我,来的人大部分是有心结,却结不开。庄施主,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吧。”
庄晓梦认真地听着,悟明讲了起来。
大为山大安禅师有一次对会众说:“有与无(的概念)如同藤绕树。”
疏山在听到这段传闻之后,立即长途跋涉,要去弄清大安这句令人大惑不解的话是什么意义。走到那之后,他见大安正在抹泥墙,就走过去问:“你真的说过有与无(的概念)如同藤绕树吗?”大安道:“是啊,我的朋友。”疏山再问:“如果突然树倒藤枯怎么办?”大安丢下了他的抹泥板,大笑回到他的屋子中。疏山跟随在后面,抗议道:“我走了三千里才到这里,卖了我所有的衣物做旅费,就是为了向你求教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却同我开玩笑呢?”大安可怜这个和尚,就叫侍者凑足旅费,打发他回去,对他说:“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名叫独眼龙的和尚,他会指明你这件事。”后来疏山遇到明招,把他见大为山大安的事说了出来。明招道:“大安完全是对的,只是他没有遇见一个真正懂得他的人。”于是疏山又把原先的问题对明招提了出来说:“如果树倒藤枯怎么办?”明招答道:“你又要叫大安大笑一场!”这句话突然使疏山悟出了意义,大叫道:“原来大安笑里藏刀!”于是恭恭敬敬向着大为山的方向行礼。
我们一切思想都是以有与无的对立为开始;没有这种对立,我们就不可能有推理行为。因此,疏山的问题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如果有与无的概念枯萎掉,我们的思想体系会怎么样呢?”当树倒下来,藤子也自然枯死。有必须以无为伴,才成其为存在,反之亦然。只要我们还停留在相互对立的世界,我们就永远不能觉得满足;就以其眼前的状态而言,又十分不能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生与死,有与无的对立似乎并不是最终的阶段,而我们又永远都希望超过它;它指向某种更高和更深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我们希望抓住的。相互的对立状态是必须超越的,但如何超越?事实上这就是疏山所提出的问题。疏山的心相当倾向于形而上学,因而会诉诸有与无这样抽象的概念,但他的实际心灵又使他把这种抽象概念化成为松树与藤子之间的具体关系。然而疏山的这种实际性却被大安更进一步的实际性彻底搅乱了,大安丢下了抹泥板,大笑着回到他的屋子去。大安完全是实际行动的,而疏山则还在语言象征的层面;这即是说,他还在概念层面,而离开了生活。有与无,可以引申出对与错、生与死等等,也就是矛盾。
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我要再引一段关于有无问题的禅宗故事。有与无的问题到了宋朝又在圜悟与大慧间做过讨论。圜悟要他的弟子大慧对树与藤的问题表示意见。但每当大慧表示意见,圜悟就说“不是,不是。”这样约过了半年,大慧终于问圜悟说:“我知道你在随侍五祖法演时,曾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五祖怎么回答。”圜悟不言,大慧又说:“你这个问题,是在会众面前问的,我想你现在告诉我,也没有什么不妥。”圜悟无法拒绝,就说:“当我问五祖关于有与无的问题时,他回答道:‘无可描述!’我再问道:‘若突然树倒藤枯怎么办?’五祖说:‘你设网自陷!’”圜悟的这一段话,立刻开启了他弟子的心,因为大慧现在完全了解了这个问题的意义,于是圜悟说:“你看,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临济在黄檗门下修习几年之后,首座和尚问他:“你来此多久?”“三年。”“有没有参问过?”“没有。”“为什么不去试问呢?”“因为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首座和尚就告诉临济说:“你去见和尚,就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临济照着首座和尚的话去问道:“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但他的问题还未说完,黄檗就给了他几棒子。首座和尚见临济回来,问他参见的结果。临济沮丧的说:“我照着你的话问师父,师父却给了我几棒子。”首座和尚鼓励他不要丧气,再去问黄檗,如此,临济三次参问黄檗,三次被打,而可怜的临济比原先一点也没聪明。最后,临济想还是跟随别的师父算了。他向首座说,首座叫他先向黄檗辞行。等他向黄檗辞行时,黄檗叫他去见大愚。临济见了大愚,大愚问他:“从何处来?”“从黄檗处来。”“黄檗有什么言句?”“我三次问他佛法的大意,三次挨打。不知我错在什么地方?”“黄檗为了给你解困,慈悲得象个老婆子,你还问错在什么地方?”这一提醒,临济突然悟到黄檗那种表面上粗厉的行为所含藏的真意,于是大叫道:“原来黄檗的佛法也不过如此啊!”大愚立即抓住临济的领子,说:“你这个尿床小鬼,刚才还说不知错在何处,现在竟然喊起黄檗佛法不过如此来,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快说快说。”临济没有开口,却在大愚的肋间轻打了三拳。大愚推开他,说:“你的师父是黄檗,干我何事。”临济回到黄檗处,黄檗问他道:“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只因为你老婆心切!”黄檗道:“待大愚来,我非好好给他二十棍不可。”临济说:“不必等,现在就打!”说着便开心的打了黄檗一掌。老黄檗则开心的大笑起来。
在临济的故事里,答案不是用笑的方式给予,而是用一种更为令人却步的方式,因为他挨了许多棒打。然而,不论是笑、打、踢或掌,就从它是来自禅师的直接体验而言,却没有什么大的分别。临济同样未能了解黄檗的用意,因此跑去见大愚,想求得启迪,而这个启迪则因一个好心的注释“黄檗真是老婆心切!”而达成,原来临济所挨的棒打是为了唤醒他在矛盾中的沉睡。
悟明讲完后,对庄晓梦说:“庄施主,回去后,你把这个故事反思一下好不好,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够我们去参悟很长时间的。好多心结就源于此。”
庄晓梦感慨道:“您的一席话让我疏朗不少啊,我回去后一定好好琢磨一下这个故事。”
悟明说:“你如果想开悟,可以随时过来找我,我们一块探讨一些感悟。”
庄晓梦高兴地说:“好的,我还会来的。”
两人出去后,庄晓梦意犹未尽地说:“朵晶,你知道这个人原先是干什么的吗?”
朵晶说:“原先你们认识?”
庄晓梦说:“他原先是我们的总经理,我给你说过他,只是你们没见过。世界很大,又很小,我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他。”
朵晶惊叹不已。
回去后,她把这个事情跟林平之说了说,出乎她意料,林平之对禅学也充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