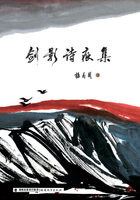在夜郎故国的高原上,一个人能站出一种高度:举目,四野苍茫;远眺,群山相拥。我很想成为一个歌者,无私的歌者。面对大山,我想唱出一种风格,一种与生俱来的心吟。
——题记
一头单独的牛
远远地就看到了那头牛。在这一览无余的山峦中,像是一块石头挡住了我的攀延的脚步,那头牛却挡住了我的目光。它让我的目光打了一个美丽的浪花,高高抛起,然后轰然散落在它的周围。
我慢慢地向它走去。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一头什么样的牛。
我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登上这座大山。我甚至不知道是朝着哪个方向攀延的,我对方向一直带有天生的迟钝。所以,我至今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一直认为,在大山上,无论你从哪个地方攀延,都是在朝一个方向攀延。所有的方向,只是一个方向,这使我想起国人常说的“条条道路通北京”这句俗语。这多么像我们的人生,向南向北向东向西,最终走向了尘埃堆满的大地。而这绿得一塌涂的山野,我更像一棵青草。
一棵青草,向一头牛走去。
极目望去,那头牛四周没有其他的牛,没有村落,没有牧童,也没有伙牛,只有一条小溪,幽灵般地流淌着。有一瞬间,我觉得那条小溪,就是山里人拴着那头牛的绳索。只是,不知道这绳索攥在什么人手里。也许,那个人叫命运。那头牛孤零零地镶嵌在一片绿里,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我想,它应该是一头勤劳的牛,说不定会是一头为山里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牛呢。
渐渐地近了,终于看清,那是一头毫无特别之处的牛。至少,在我看来,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普普通通,像我见过的许多牛一样。
那是一头黄牛,但那种黄不是纯粹的黄,它黄黄的绒毛白头的心。牛尾巴轻轻摇着,舌头伸出,舐舐这舐舐那,蹬蹬蹄子又刨地,一看就知道是有力气能干活的样儿,真是爱煞个人。牛耳怯怯地翘着,眼睛一闪一闪的,像是注视着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看,空空的。我轻轻地拍着它,像拍着我那久违的儿子。它结实的肌肉,让我的手掌激动不已。但它对我似乎不感兴趣,对我不屑一顾,沉默得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它的不屑和沉默,让我手足无措。我悻悻地看着它,看着这头离群索居的牛。它那么平常,毫无非凡之处,却信心十足,理所当然地独自挺立在这茫茫苍苍的山野。
或许,我也是一头牛,因为我是属牛的。所以命运让我和一头单独的牛相遇,必有深意。
是什么原因,让一头牛远离伙牛、牧童和栅栏。它从哪里来?它要去时么地方?为什么默默地站在这里呢?在这连绵起伏的大山,它高大的身影也许并不十分显眼,但它却十分孤单。它默默地站在这里,不屑于答理我。众多的青草和花朵簇拥着它,但它却和天空一起,默默地低下了头。像一棵扎了根的草。似乎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众多青草和花朵中的一员,似乎它内心也涌动着不可遏止的芬芳。而当它抬起头,不远处的河水,闪电一样,照亮了它的眼睛。
我和一头牛,一个懒散的人和一头单独的牛,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了一个下午。
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在写到牛时说:“……在甩动尾巴赶苍蝇,摇晃着脑袋,好像醉了一样,懒洋洋地迈开步子走着,那神态仿佛是女奴群中的一位皇后似的。”但我敢肯定,我面前的这头牛,它来到我们中间,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一定会那样悠闲。当然,它也许还要寻找一棵青草。它也许是在寻找自己,它也许连它自己也懒得寻找,它也许什么也不寻找,它只想那么单独地、默默地伫立着。
一头单独的、默默伫立的牛,让一座大山,始终保持着警惕……
冬天,去看看大山
我漫无目的地攀延着,寒冷紧一阵慢一阵地跟着我。满山坡的草仿佛被寒冷冻得缩回了大地,原本空旷的山野更是空旷得踏踏实实、理所当然。阳光明晃晃地站着,一脸青春,倒仿佛春天里的草。远远地,有一伙牛缓缓地移动着。我慢慢向那伙牛走去,它们的缓慢与我的漫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不是一伙纯黄的牛,那种黄是一种陈旧的黄,而且当中夹杂着几头灰色的牛。那寥寥的几头灰色的牛,像是我们生活中碰到的几个标新立异的青年,让人侧目。放牛人骑着牛,高瞻远瞩着这些卑微的生命。是啊,这伙牛,放牛人,我,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一年中,被什么驱赶着,在时光中游走。而我的懒散和悠闲,又何尝不是一种匆忙。
我默默地注视着缓缓移动的这伙牛。在冬天的大山,并不是每天都可以碰到一伙牛的。我仔细地凝视着它们。我凝视好久之后,突然发现:那些伙牛正吞食阳光。这个奇迹我激动不已。偌大的山野,除了我的心跳声,我只听见这伙牛咀嚼阳光的声音。当我走出好远之后,我都能看见它们的嘴角阳光四溢。
仿佛一夜之间,有人卷起了那座花团锦簇的宫殿。昨天还绿得生龙活虎的大山,今天已是一派萧瑟。但大山的那肿苍茫与庄严一以贯之,就像一个人也许他会老,但他的本性至死也不会改变。
也仿佛一夜之间,有人在大山上铺了一张雪白的地毯。又像是有人在天空的花园里,修剪那些雪花。剪下来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它们美,不能承受自己的轻。美丽的雪花们风姿绰约,就像舞台上的模特一样扭着腰肢。大山一点点地洁白起来,直到白得耀人眼睛,直到你的心也一片洁白。
整个大山成了一座座雪山。一片片雪花,就覆盖了大山。那么美丽的雪花,竟然创造出了一个苍凉、寂寥和空旷的世界。我像往常一样,嘎吱嘎吱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一抬头,看到一只鹰在我的头顶低低地盘旋。它要干什么?它把我当作猎物?我跑起来,它就跟着我,仿佛我是它的一个向导。我们就那么一上一下地跑着。满世界的雪,只有一只鹰和一个人。满世界的白,只有一上一下两小团黑。说不清,人是鹰的影子,还是鹰是人的影子。满世界的雪白啊,只有两团黑火苗相互鼓励着,在缓缓燃烧。不知道,是谁点燃了谁。因为只有一只鹰和一个人的存在,大山的苍凉、寂寥和空旷便有了切实的依据。。
冬天,去看看大山。这种看,不是旅游者的那种观光,也不是商人的那种考察,更不是领导一样的视察。这种看,是一个懒散的人自由的漫步,是一颗心海阔天空的遐想,是一个赤子回家一般的期望,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相互照耀。
我总在冬天想起大山,这就像一个人总是在寂寞和孤独时想起另一个人的孤独与寂寞,应该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吧。套用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如爱只有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我说,多少人爱你绿草如茵的美丽,爱慕你花团锦簇的繁华,独独我爱你苍凉、寂寥和空旷。
因为,我是一种苍凉、寂寥和空旷……
一棵草的辽阔
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大山里的那些青草。我不是研究它的绿,也不是研究它的生长,我研究一棵青草与另一棵青草的区别。
我在一个地方拔出一棵青草,然后沿着大山走,有时候走半天,有时候走一天,在走到的那个地方再拔出一棵青草,我仔细地对它们做着比较。除了大小略有不同,一棵青草与另一棵青草没有什么区别。细细的,绿绿的,几片窄窄的叶子随便地附和着。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大山里,所有的青草,都是同一棵草。或者说,一座大山,只是一棵硕大的青草而已。
我们从一个村落迁移到另一个村落,走了几十里、几百里,其实我们也没有走出一棵小小的、瘦瘦的青草。我们的一生,都在一棵青草的怀中盘桓。
每一棵青草都是同一棵草,这就像我现在住着的城市,每一间房子都是同一间房子。我们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一间房子。我们的一生,只是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即便是死亡,也不过是从几十平米的房子走到几十厘米的房子而已。我们不了解一间房子的辽阔,就好像我们不了解一棵青草的辽阔。
所以,与其说我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走出一座大山,不如说,我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也没有走出一棵青草。五十年来,我在一棵青草里散步、吃饭、做爱,写自已想写的东西。五十年来,我在一棵青草的里天马行空地做着这样那样的梦。五十年来,那些无数海阔天空的梦,仅仅凝结成了一滴露珠。为此,有时候我看着这颗露珠,看到我的那些梦,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
有一次,我在大山上遇到一头小牛犊。它似乎刚刚学会行走,走起来孩子一样前仰后合,像是舞台上专门逗人笑的可爱的小丑,天真的样子真让人心疼。它那绒黄色的小身体风一样柔软,似乎可以像一本书似的打开或者合上。它黑黑的小眼睛清澈见底,无畏的辉映着低低的天空和空旷的大山。它尖尖的小耳朵盲目地立着,它还听不到一棵草走动的声音。
它天真地蹦跳着,这大山的心脏,它还没有学会严肃和沉重,它还不了解一棵草的辽阔。虽然,再低的天空也低不过它行走的四蹄。时光漫漫,在长成一头黄牿之前,它得先炼就艰辛、疼痛和一副厚实的脊背。它像一条河一样活泼,它迈动四蹄,它向前彳亍着。它行走的样子,像一个日出……
当我返回来时,已是日暮。在落日的余晖中,我看到一头老牛。“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它迈着沉重的步子,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皮毛稀疏眼睛浑浊,跛着脚,似乎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坑坑洼洼。不长的一段路,它走了整个一个傍晚。它气喘吁吁地走到我的跟前,我看到它身上的黄毛像一座风化的沙丘。一头老牛,终于怯生生然而又理直气壮地说:我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一棵青草。它说完这句话,就像是放下了一生的重负。
我走在那一座座大山上,看着那满山的树儿,静静地凝望,久久地思量:我知道这是新生活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