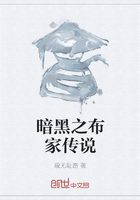于是莉萨维塔·彼得罗芙娜用一只手向列文举起那个奇怪的、摇动的、在襁褓里藏着小头的、红色的生物(另一只手只用指头托着摇摆的后脑),但他还有鼻子,斜视的眼睛和咂响的嘴唇。
“好看的宝宝!”莉萨维塔·彼得罗芙娜说。
列文悲伤地叹气。这个好看的宝宝只引起了他的憎恶与怜悯的情绪。这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情绪。
在莉萨维搭·彼得罗芙娜把婴儿放到未见惯的****上时,他掉转了身。
忽然笑声使他抬起了头。这是吉蒂在笑。婴儿在吃奶了。
“哦,够了,够了!”莉萨维塔·彼得罗芙娜说,但是吉蒂不放婴儿走。他在她的怀里睡着了。
“现在你看。”吉蒂说,把婴儿向他侧转着使他能够看见。打皱的小脸忽然更加打皱,婴儿打喷嚏了。
列文微笑着,几乎不能约制动情的眼泪,他吻了妻子,走出黑暗的房间。
他对这个小生物所感到的情绪,完全不像他所预料的。在这种情绪中没有愉快的欢乐的地方;相反的,这是一种新的痛苦的恐怖。这是对于新的易受伤痛的范围的意识。这意识在起初是那么痛苦,怕这个无能为力的生物会受痛苦的恐怖是那么强烈,以致在婴儿打喷嚏时,他没有注意到那奇怪的无意义的喜悦甚至骄傲的心情。
十七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的家务是在恶劣的情况中。
三分之二的森林的售款已经用去,他按照九折向商人预借了几乎全部的其余三分之一。商人不肯再多付钱,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冬天,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第一次露骨地宣布了她对于自己财产的权利,拒绝在契约上为收到其余三分之一的森林的售款签字。所有的官俸都花在家用和偿付不能拖延的小债务上。钱完全没有了。
这是不愉快的,为难的,照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的意思,是不应当这么继续下去的。这件事的原因,在他看来,是由于他的官俸太少。他所担任的位置显然在五年以前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银行经理彼得罗夫的收入是一万二千;斯文齐次基——公司的董事——是一万七千;银行创办人米清的是五万。“显然,我在做梦,他们把我忘掉了。”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想到他自己。于是他开始打听,观望,到冬末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缺,并且向它进攻,起初是从莫斯科进攻,通过姑妈姨妈们,伯叔娘舅们和朋友们,后来当事情成熟时,他亲自在春间到彼得堡去了。这种官缺现在比从前更多,这是年俸自一千到五万的、那种舒适的事易钱多的一种官缺;这是南方铁路与银行的相互信托清算联合办事处的委员会的委员的缺。这个缺和所有的这种缺一样,需要那么多的学问和办事能力,这是难以在一个人身上兼备的。因为兼有这两种资格的人是找不出的,所以这个缺由正直的人来补,总比由不正直的人来补要好些。而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不但是正直的(并不强调这个字眼)人,而且是有那种特别意义的正直的(强调的)人,那意义是在莫斯科大家说正直的政客、正直的作家、正直的报纸、正直的机关、正直的倾向的时候“正直的”这个字眼所有的,那意义是表示不但一个人或机关不是不正直的,而且他们遇有机会就可以抵触政府。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在莫斯科的用这个字眼的那些团体中出入,被人认为是正直的人,因此比别人更有权利补这个缺。
这个缺有七千到一万的年俸,奥不郎斯基可以担任它不必辞掉他的政府的职位。这件事决定于两个大臣,一个太太,两个犹太人,所有的这些人虽然已经被疏通过,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还需要到彼得堡去看他们。此外,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还答应他妹妹安娜从卡列宁那里去求得关于离婚问题的确定的答复。于是,他向道丽要了五十卢布。便到彼得堡去了。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听着他的关于俄国财政恶劣情况的报告,只等着在他说话完毕的时候,就说到自己的事,说到安娜。
“是的,这是很真实的,”当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取下了他现在不戴便不能阅读的pince-nez(夹鼻眼镜),疑问地望着他从前的舅子的时候,他说,“这在细节上是很对的,但是我们这时代的原则还是自由。”
“是的,但是我提出了另一个原则,包括着自由的原则。”阿列克塞·阿列三德罗维奇说,强调着“包括着”这个字眼,并且又戴上pince-nez(夹鼻眼镜),准备重读那段说到这句话的地方。
于是翻开了字迹优美余白宽阔的原稿,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重新朗读论断的地方。
“我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主张保护制度,却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同样地为了下层的和上层的各阶级。”他把眼光从pince-nez(夹鼻眼镜)的上边望着奥不郎斯基说,“但是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他们只关心私人的利益,热心唱高调。”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知道,当卡列宁开始说到他们——就是那些不肯接受他的计划书的和造成俄国一切不幸的人们——所做所想的事情的时候,话便快要完结了。所以他现在乐意地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并且完全和他同意。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沉默着,沉思地翻着他的原稿。
“呵,顺便提一下,”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我想请你在你有机会和波穆尔斯基见面的时候向他谢一声,我很愿意得到南方铁路与银行的相互信托清算联合办事处的委员会的委员的缺。”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已经习惯了他所那么渴望的这个缺的名称,他没有错误地迅速地说出了它。
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问了这个新委员会的职务是什么,便沉思着。他在考虑,这个新委员会的职务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违反他的计划。但是因为这个新机关的职务是很复杂,他的计划包括很大的范围,所以他不能够立刻考虑明白,于是脱下pince-nez(夹鼻眼镜)说道:
“当然,我可以向他说;但是为什么你偏偏想谋这个缺呢?”
“薪水好,可以到九千而我的经济……”
“九千……”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重复说,皱了皱眉。这个薪水的高额数字使他想起了,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所提到的职位,在这方面违反他的总是趋向节约的计划里的主要思想。
“我认为,并且关于这个我在报告里写过,我们现在这些高额的薪水便是我们政府的错误的经济assiette(原书附注为政策。——译者)的证据。”
“但是你想怎么办呢?”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哦,我们假定,银行经理赚一万——他值得上这些,或者工程师赚两万。总之,这是有生气的事情!”
“我认为,薪水是对于所得到的价值的一种报酬,它应该遵从供求律。假若薪水的规定不遵从这个定律,例如,当我看见了两个工程师离开学校,两个人有同等的学识和能力,却一个赚四万,另一个以两千为满足,或者,当我看见了法律学的学生,骠骑兵,没有任何特殊的专门知识,做了有大薪水的银行经理,我就要认定薪水不是按照供求律规定的,而只是凭交情规定的。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过失,对国家的公务有坏影响。我认为……”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连忙打断了妹丈的话。
“是的,但是你要同意,这是开办一个新的确实有用的机关。总之,这是有生气的事情!他们特别看重的是事情要做得正直。”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强调着这个字音说。
“正直”这个字眼的莫斯科的意义,是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所不了解的。
“正直是消极的条件。”他说。
“但你还是帮我一个大大的忙吧,”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向波穆尔斯基说一声。就是在谈话的时候……”
“但是这件事好像更要靠保勒加锐诺夫。”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说。
“保勒加锐诺夫在他那方面完全同意了。”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红着脸说。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在提到保勒加锐诺夫时脸红,因为这天早晨他去看过犹太人保勒加锐诺夫,这个拜访在他心中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确实知道他想要服务的机关是一个新的、有生气的、正直的机关,但是那天早晨,当保勒加锐诺夫显然故意使他在接待室里和别的请愿者们一同等了两个钟头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不舒服了。
他觉得不舒服,不知道是因为他——柔锐克的后裔,奥不郎斯基公爵——在犹太人的接待室里等了两个钟头,还是因为他平生第一次没有遵循祖先的在政府服务的前例,而另寻新的出路,但总之,他是很不舒服。在保勒加锐诺夫家里两小时的等候中,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轻快地在接待室里走动着,捋着胡须,和别的请愿者们交谈着,思索着一个戏言,就是说到他如何在犹太人家里“久待”,他努力地对别人甚至对自己掩藏着他所感到的心情。
但是在这全部时间里他觉得不舒服,他恼怒,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什么:是由于“到犹太人家去办事,我倒久待了”这个戏言没有结果,还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当保勒加锐诺夫终于极恭敬地接见了他,显然因为他的屈辱而得意着,并且几乎拒绝了他的时候,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连忙要尽可能快快地忘记这个心情。而现在,只是一想到,他就脸红了。
十八
“现在我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关于安娜。”沉默了一会,摆脱了这个不愉快的回忆之后,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说。
奥不郎斯基一说出安娜的名字,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脸色就完全改变了:没有了先前的生气,它表现了疲倦和死气。
“究竟是什么事您要我办呢?”在靠臂椅上转动着,弹着pince-nez(夹鼻眼镜),他说。
“一个决定,随便一个什么决定,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我现在来找你(‘不是把你当作一个伤心的丈夫。’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本想这么说,但是怕因此破坏了这次的谈判,便换了说法),不是把你当作一个国家的官员(这不是顺口说出的),却是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基督教徒。你应该可怜她。”他说。
“那么,究竟要怎样可怜她呢?”卡列宁低声说。
“是的,可怜她。假若你看见了她,像我——我和她过了一整个冬天——你就要可怜她了。她的处境是可怕的,简直是可怕!”
“我似乎觉得,”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用较高的几乎是尖锐的声音回答,“安娜·阿尔卡即耶芙娜有了她自己所希望的一切了。”
“啊,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看上帝的情面,不要让我们去追究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她所希望的等待的是——离婚。”
“但是我当时认为,假若我要求把儿子留在我这里,安娜·阿尔卡即耶芙娜会拒绝离婚的。我这样地答复的,并且以为事情已经完结了。我认为这事情是完结了的。”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尖声说。
“但是,看上帝的情面,不要生气吧,”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摸着妹丈的膝盖说,“事情没有完结。假若你允许我讲几句话,事情是这样的:当你们分离的时候,你是伟大的,尽量宽大的;你给了她一切——自由,甚至离婚。她重视这个。不,你不要想了吧。她重视到那样的程度,以致在最初的时候,她觉得对你不起,她没有考虑也不能考虑一切。她把一切都放弃了。但是现实,时间,表示出她的处境是痛苦的,难受的。”
“安娜·阿尔卡即耶芙娜的生活不会使我发生兴趣的。”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抬起眉毛插言道。
“请让我不相信这话,”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温和地回辩着,“她的处境对于她是痛苦的,对于无论哪一个人是无益的。她应得的,你要这么说了。她知道这个,并不要求你什么;她坦白地说,她不敢要求你什么。但是我,我们全体亲戚们,所有的爱她的人,要求你,恳求你。她为什么要受苦呢?谁会因此得到更大的益处呢?”
“对不起,您似乎把我放在被告的地位上了。”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说。
“噢,不是,噢,不是,一点也不是,你要了解我。”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又摸着他的手说,好像他相信这摸触会和缓他的妹丈。“我只说这一点:她的处境是痛苦的,但它可以由你减轻痛苦,而你毫无损失。我来替你把一切布置得使你不觉得。你晓得,你答应过的。”
“从前是答应过。我那时以为儿子的问题决定了这种事情。此外,我希望安娜·阿尔卡即耶芙娜也有宽大……”脸色发白的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用颤抖的嘴唇困难地说。
“她把一切都听你的宽大去处理。她只要求、恳求一桩——把她从她所处的难受的处境里拔救出来。她已经不要儿子了。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你是好人。你在她地位上试去处片刻吧。在她的地位上,离婚问题是她的生死问题。假若你从前没有答应过,她便安于她的处境了,她便住在乡下了。但是你答应过,她写了信给你,搬到莫斯科去住。她在莫斯科每次会到人,就好像刀刺她的心,她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了,天天等着你的决定。这完全像是把一个判了死罪的人用绳索套在颈子上关了好多个月,约许他,也许是死,也许是释放。可怜她吧,我来把一切布置得……Vos scrupules(你的犹豫)……”
“我不是说这个,这个……”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憎恶地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也许,我答应了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