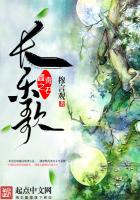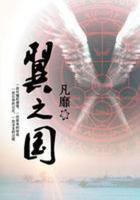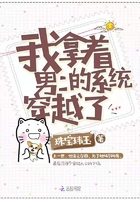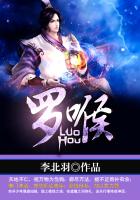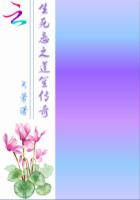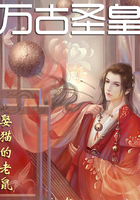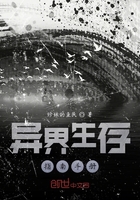林曦和林昭也各自寻了蒲团坐下。
林启整理了下思绪,缓缓开口道:“我林氏一族可谓是先祖一力开创的,先祖发迹于微末。本是大汉末年一落魄书生,却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林氏一族百年基业,真可谓是时代的弄潮儿。就算了同时代的大晋太祖,一代真龙也掩盖不住先祖的光辉。当初分封功臣之时,太祖本欲封我林氏为异姓王,共享天下。可先祖执意不受,故而改封一等国公。”
林昭听后激动道:“可惜不在一个时代,否则真想见识一下先祖风采,先祖当年曾经以弱胜强,不用奇袭,不用诡计。率一万步卒硬生生击溃装备精良,兵种齐全的五万精兵。真可谓是一代军神。”
林曦却冲林昭问道:“哥哥说的这些,族史里面也有记载。那一战,先祖令士兵结盾如墙,集矛如林。肩并肩,同进退。前者阵亡,后者补上,以保证阵式。以一万对五万未曾后退一步,硬生生将那五万精兵磨死与盾墙矛林之下。哥哥,若是你会怎么对付这种战阵?”
林昭深深的思索了一下,才郑重道:“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既然在绝对兵力的优势下,我会以强弓硬弩撕开缺口,而后骑兵掩杀,让其不能结成阵式,而后分而歼之。而不会去冲击先祖的方阵。”
林曦轻笑道:“敢问父亲有何见解,哥哥说的可是一种良策。”
林启笑斥道:“你已成竹在胸,却来为难为父。自己说吧。”
林曦缓缓开口道:“哥哥所言,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可是哥哥所言不去冲击方阵,可最后还是与方阵硬碰硬。眼光局限于战场之上。何不从别处入手?”
林启道:“哦,妹妹还有良策?”
林曦道:“兵法还有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族史记载当初先祖深入敌人腹地,有多是步卒,行进撤退的速度皆比不过强敌。而前有强敌,后有洛水。故而背水一战。故而此战正当围之,断其粮道。而等到先祖筋疲力尽,而后歼之。当初领兵之人,未曾见过这种方阵,不明就里,故而以优势兵力冲击方阵,反而成就了先祖,使之一战成名,而自己却贻笑大方。”
林启笑道:“不错,着眼全局,运筹帷幄。昭儿你得跟你妹妹多学学了。”
林昭摸了摸头:“不错妹妹博闻强记,就连族史的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孩儿受教了。”
林曦道:“哥哥的战术也是极好的。速战速决,毕其功于一役。可是这都不是重点。先祖未发迹之前可是一书生,从哪学得这兵法战阵,哥哥不觉的好奇嘛?不知父亲可否解惑?族中可有不记载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或者说历代族长口口相传的秘辛。”
林启沉思后道:“这个倒曾没有,不过皇室收藏的野史倒有记载。记载上写:林氏先祖林远,未发迹之前,泯然于众人。青年时曾大病一场,病愈后犹如神仙灌顶,而后一飞冲天。”
林曦轻蔑的一笑:“看来太祖当初也是调查过我林家的,帝王心术。果然如此。”
林启斥道:“素女,慎言。既知皇权无孔不入,小心祸从口出。”
林曦道:“女儿妄言,父亲且放宽心。素女知道分寸。但先祖奇异不止于此,先祖知兵事而不擅奇谋。擅诗词而短经义。而且还会许多奇门异术。比如说,精盐提纯,陶瓷烧制、冶金、器械的打造。更可怖的是先祖发明了连弩。这种神兵利器可是彻底使得大晋在战场上无往不利。而先祖发迹之前就连皇室也评价:泯然于众人,没有展现出丝毫奇异之处。这未免不合乎常理。”
林启道:“素女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林氏百年。六祖倒是给出了一个结论。”
林昭好奇道:“父亲,什么结论?”
林启淡然道:“仙人所授。”
林昭不禁愕然:“可这个结论也未免太过搪塞了吧。”
”林曦会心一笑道:“这个结论虽然搪塞,也给了天下好事之人一个交代,毕竟就连我林氏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外人又怎么清楚真假?估计是六祖不胜其烦,以堵天下众人之口。倒也给我林氏增添了几分神秘。这正是六祖高明之处。”
林曦又道:“关键是先祖留下的祖训也与世格格不入,比如说林氏子孙无男女嫡庶之分。林氏子孙婚姻父母均不能强加。凡嫁为林妇者,无**无后之大错不得随意休妻纳妾。这其后两条祖训也是我林氏子嗣艰难的原因之一吧。”
林启道:“不错,开国之初,各权臣贵族,无不想把女儿嫁入我林氏。就是因为先祖的这些祖训。”
林曦道:“可就算如此,我林氏繁衍百年,也不该子孙如此凋零,仅剩一十二支。”
林启沉重的道:“族史记载历代族长均浓墨重彩,唯独记载五祖却是十分模糊,而后六祖横空出世。你们可知为何?这是因为我林氏在此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差点令林氏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林曦紧张的看着林启问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林启反问道:“你想我林氏当时已经传承近百年,根基深厚。而且手握兵权,能有什么事能让我林氏毁于一旦?”
林曦震惊道:“难道是谋反?除此之外,女儿想不出任何事能使林氏族灭。”
林启道:“不错,正是谋反。当时掌权的五祖心有大志,身居高位,手握兵权。为让我林氏再上一步,却动了妄念,竟然私自从边关调回五千精锐,意图谋反。只可惜,竟然遇上了一代雄主孝宗皇帝。最后功亏一篑。五祖身死,全族被囚。孝宗皇帝正准备将我林氏满门抄斩,罪行公布天下之际。由于边关一直是我林氏掌兵,主帅无故身死,边关士兵人心惶惶。鞑靼见边关不稳,竟倾举国之兵。打破边关,一路南下。兵临晋阳城下。众臣劝孝宗皇帝迁都南巡,满朝动荡之际。六祖在天牢中手持太祖赐给先祖留下的一面金牌,要直面君王。在那奉天殿上,六祖披头散发,高举金牌。直面孝宗皇帝,孝宗皇帝怒斥道:你林氏位极人臣、享受百年富贵,却不思报答君恩,却欲谋反。致使边关不稳,鞑靼兵临城下,你还有何话说?。”
六祖把头都扣破了,只言:“林氏谋反,不知情者居多,陛下值此危难之际,当尽诛首恶。若陛下真的要杀,我林氏子孙宁愿战死沙场。只求陛下念我林氏先祖余荫,给我林氏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若我林氏击退鞑靼,请陛下念我林氏血战之功。为我林氏留下一条血脉。六祖当殿立誓:凡林氏子孙男丁身高超过车轮者,尽赴沙场,只求孝宗皇帝,留下襁褓中的婴儿,不辱我林氏女眷。”
那一战,我林氏凡是身高超过车轮的男丁尽皆发配沙场,一无坚甲,二无战马。布衣赤足便上了疆场,那一战我林氏父子相护,兄弟并肩。父亲替儿子挡住一箭,兄长替弟弟挨了一刀。打出了我林氏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百人去,一人还啊!活下来的只有六个孩童,以及六祖,当鞑靼退去,我林氏的尸体整整堆满了百辆大车,六位孩童以及妇孺肩拉人推将他们的父亲、兄长、夫君、儿子拉到了皇宫之外。六祖身中六箭,一十三刀。这还是在我林氏重重保护之下,六祖后来回忆其中就有他的亲侄子替他挡住了一枪,那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被鞑靼一枪贯膛,血溅在六祖脸上。林氏都知道谁都能死,唯独六祖不能死。只有六祖才有可能保住林氏,六祖也清楚这一点,可是眼看看一个个亲属、孩子为了保护自己死在面前。六祖往后的一生都活在愧疚之中。
就连六祖面君都是被抬着上殿的,金殿之上,六祖向孝宗皇帝复命道:“林氏子孙尽皆战死沙场,唯余罪臣苟且偷生。罪臣授首待戮。只求陛下,放过皇宫门口的那些孩子妇孺,罪臣代我战死的林氏子孙叩谢陛下天恩。”说罢吐血金殿,满朝大臣无不落泪。可叹一人之野心,竟连累的全族皆灭。若是没有六祖横空出世,林氏恐怕早就族灭。遗臭万年。五祖若非早死,看到这一幕不知会作何感想?
林曦道:“后来孝宗皇帝放过了我林氏?”
林启道:“不错,孝宗皇帝不愧是一代雄主。念我林氏子孙血战之功,不计功过,放了我林氏一马。自那以后我林氏交出兵权,爵位降为三等国公。林氏也在重重监视中度过了孝宗一朝,不敢有任何违制的举动。就连六祖如此大才也不敢表现,蹉跎半生。不过我林氏还是保存了下来,孝宗皇帝未免这场丑闻曝光,特意捏造消息说:五祖带兵不利,致使鞑靼南下,危及晋阳,只诛杀五祖,降林氏爵位为三等国公,也算保住了我林氏百年清誉。”
而后孝宗皇帝驾崩,新帝继位。感念当年林氏战功,又二十年忠心耿耿。又值鞑靼肆虐边关。重新启用六祖,六祖在五十岁那年再次领兵开赴边关。六祖卧薪尝胆二十载,国仇家恨终于有机会报了,而后十年间将鞑靼远逐漠北。六祖最后身死边关。临终前,告诫子孙:“一定要再复我林氏荣光,让我林氏成就千年世家。”自六祖之后我林氏奋发图强,屡建奇功终于在你们曾祖那一辈。哲宗皇帝复我林氏一等国公。颁下丹书铁券,以示恩宠。
而我林氏子孙多历沙场,子孙战死的多,常年征战,夫妇又聚少离多。子嗣艰难。故而我林氏纵然是百年世家至今依然子孙单薄。可我林氏的血性一直在传承。
林启说完,林昭和林曦不禁泪流满面,唏嘘道:“我林氏还有这般变故,竟因一人之妄念,差点举族皆灭。而我林氏子孙却在血与火中站了起来。我等定披荆斩棘,不负先祖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