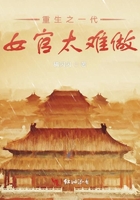自从那次听到莫叔且对侬兮表明心意后,白傲雪便非常不喜欢他接近侬兮。而今却不得不点头,他相信莫叔且的忧心不亚于自己,可是恰是这一点让他喉间似有异物,说不出话,半天只哽咽出一个字:“嗯。”
主仆二人各怀心事在走廊上伫立良久,终究还是有人打破了这样的静默。
扫视一眼楼下来来往往的人,云淡风轻地问了句:“你喜欢侬兮?”
当初说出那一番话的时候就料想到有这么一天,所以很是淡定,说:“王爷不该怀疑她。”
古朴的檐角,挑起暗月寥寥,似这廊头的愁人。他双手杵在栏杆上,沉默片刻后才说:“我不怀疑她,只是担心……”
“王爷也害怕?”身边的人丝毫没有畏惧,完全看不出是一位侍者。
“我不怕,因为他们是敌人,可你莫叔且不是敌人。所有人都可以不知道,唯独你不可以不理解我。你知道,那些伤害侬兮的事,我都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有谁见过,主子委曲求全的去请求属下?可是他白傲雪从不把自己当主子,也从未把莫叔且当属下。
不管他是真心相求还是假意示弱,莫叔且无所畏惧,与之相视,问:“王爷是不相信自己?还是不相信侬兮对王爷的心?”
“她的心我无从得知,但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的能力。你本就不是寻常人,也是我不愿面对的危机。”
无从得知?莫叔且心里冷笑。就算是瞎子也看出她易侬兮对你的情深意重,你是看不见还是假装看不见?莫叔且心有不快,说:“钟鼓玉帛非吾事,池台花鸟非吾春。只是王爷再这么伤她下去,她终究会离开的。属下去接人,先行退下。”
因为太子病重需要静养,所以东宫中的下人剩下不多。赵公公把侬兮领到太子专门会见人的屋子,为她推开门后就等在屋外。
心惊胆战地进屋,却见太子端坐在特制的太师椅上,太师椅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毛褥子,身形消瘦,面色枯黄。在看见侬兮到来后,对侬兮微微一笑,道:“易姑娘到了。”
夜间召见,这屋中又无他人,即便太子看上去平易近人,但这不足以消除侬兮的战战兢兢。微微瑟缩着下跪叩首:“民女易侬兮见过太子殿下。”
“免礼。”因为久病,本是温润的音色听上去也显得有气无力。
“谢太子殿下。”道谢后站起身,担忧使得她深深颔着头,而警觉又使得她对四周的一切都特别上心。
太子看出她的心思,不生气也不点破,柔声解释:“深夜叫易姑娘进宫来,多有不便,但这事还是尽早说的好,又不愿让易姑娘落了女乐的名声,便说与易姑娘探讨北城之舞。”
平淡的解释让侬兮微微愕然,同时也稍稍放下悬着的心,终于敢看向太子,恭敬地问:“太子殿下有何事与民女说?民女自当谨听。”
“我知道你是程文将军的孩子,后来得知你和鸿天隐匿在祥云庵,本想将你保护起来,却不想派去的人竟是常大成安排在我身边的探子。后来你跟随齐王进宫,想留你在宫中,便以护你周全,但你还是愿意跟着齐王去。有他护着,我也不是太担心。”
“太子殿下……”侬兮彻底呆住。很想问当事人,知不知道他一心庇佑的人曾经想过要取他性命?
难怪愧疚地向侬兮颔首,让侬兮手足无措。不等她说话,太子又从身后拿出一个锦盒,致歉说:“当年因我势力薄弱,眼看着程将军受难而无能为力,倍感愧疚。这是这些年我收集的证据,足以证明程将军的清白,如今一并交给易姑娘,也算是了了未完的心愿。”
颤颤巍巍地走过去,双手捧过锦盒,侬兮霎时红了眼眶。有了它,程家可沉冤得雪。程将军?多熟悉又多陌生的词,多少年不曾听人提过,而今再次听到,却是出自这储君之口。太子的诚意让侬兮备受感动,不言只字片语,扑通一声跪在太子面前,重重的就是三个响头。
“还有一事,也该给易姑娘说清楚。北城还有一股程家军旧部,他们也知道你还活着,表示愿意听命于你。虽说有齐王相护,但是我也得提醒你,他太看重权势,想必程家军旧部之事他也是知道的。你自己看得真切一些,莫让人担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