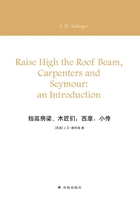见钱令梓出来,世子回头看了屋内一眼,迎了上去,问:“玉儿跟你说什么了?”
钱令梓看着世子,回想起赵玉儿说过的话,回想起她说话时的神情。
世子真的是我的良人吗?她在心底问自己。
隐下赵玉儿说要杀他的话,钱令梓回到:“她想离开。”
世子没有惊讶,看来赵玉儿之前已经给他说过了。
“你帮我劝劝她吧!如果现在出府,别人会怎么议论她?又能去哪里呢?”他对着自己新婚的妻子说。
钱令梓愕然,连桃儿也忍不了,想要说些什么,被李儿拦住了。
“世子莫不是忘了,我手上的伤。”
说道这个,世子有些尴尬,他摩擦着钱令梓手臂:“团团,赵玉儿不能走。”
“那就要看世子的本事了,恕妾身无能!”钱令梓拂身离去。
眼看钱令梓出了院门,世子又回看了一眼屋内,只能看到赵玉儿纤细的身形,看不清脸上有什么表情。
回到屋里,忍了一路的桃儿终是忍不住:“世子也欺人太甚了,小姐与他还是新婚,怎么能这样对小姐呢?如果被二少爷知道,气都要气死了。”
钱令梓没有说话,她木然的由李儿摆布。
这时门外传来通传,李玉儿来了。
通传的声音还未落,李玉儿已经进得屋来,她拉着钱令梓左看右看,看她面无表情,就知道又受人欺负了:“钱姐姐,那赵玉儿又欺负你了?还是世子哥哥?”
看着李玉儿关切的表情,钱令梓挤出一个微笑:“无事。”
“还说没事,我一听说世子哥哥过来就知道有问题,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前脚进你屋,后脚就又去了赵玉儿屋,太过分了!”
李玉儿气得在屋子里乱转,想找办法把世子和赵玉儿都教训一番。
“我让他去的。”
“什么?”李玉儿驻足,诧异的看着钱令梓:“钱姐姐,你是不是疯了,还嫌头顶的帽子不够绿吗?”
看她们谈论的内容有点偏了,桃儿和李儿便告退出去,守在门口。
钱令梓像慈母一般看着为她着急上火的李玉儿,伸手为她理了理耳发:“玉儿,很多事都不能只看表面,那赵姑娘,她不想留在王府的。”
“真的吗?”李玉儿听她这样说,托着腮帮子思考:“莫不是,她想以退为进?或者是觉得府里规矩太多,想当个外宅?那世子哥哥怎么说?”
世子!钱令梓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世子会想通的吧。”
“不说这些扫兴的事了。我想出钱给果儿开个铺子,你能不能把之前的计划写下来,给她做个参考。”
“开铺子?好啊!”李玉儿一听开铺子,眼珠子都亮了:“我能不能掺一股啊?卖什么的?瓷器吗?哎呀,铺子的位置要选好,怎么招人呢?能不能用府里的人?不行!不能让他们知道。”
看李玉儿一脸兴奋,钱令梓似乎已经不那么心烦了。
用过晚膳,送走李玉儿,钱令梓继续研究着计划书。
第一条:铺子选址
她陪嫁的院子在城南,直接隔出一间做铺子就行,第一条划掉。
第二条:经营事项
果儿刺绣做得很好,但如果只做刺绣的话太单一了,且富贵人家都有自己的绣娘,穷人家又没那么多钱买刺绣的用品。李玉儿的建议是做成衣铺子,高中低价格都卖,也行。
第三条:经营人选
……
钱令梓正一条一条的修改着计划书,放风的小丫头递消息给桃儿。
“小姐,世子过来了。”
钱令梓连忙把计划书收起来,拿出账本开始翻看。
过了一会,世子进屋。
还没来得及跟他请安,世子便挥挥手,有些疲惫的样子:“你们出去,我和世子妃有话说。”
侍女都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俩人,有些尴尬的沉默着。
“团团。”
听他的语气,似乎有点委屈。
“世子有事请讲。”钱令梓放下账本,看向世子。
他似乎很累,伸手搂住钱令梓,把头靠在她的头上,闷闷的说:“留下玉儿是有苦衷的知道吗?”
钱令梓已经不习惯他突然的亲昵,想挣扎,世子却搂得更紧了:“别动,让我靠一靠,我很累。”
世子突如其来的示弱让钱令梓有点不知所措,她只能伸手环住世子的腰,把眼眶的泪都浸在他的衣襟之上。
世子说:“我们不要再置气了好不好!”
有什么苦衷是我不能知道的呢?钱令梓心里这样想着,嘴里却口是心非的答道:“好。”
世子又说:“玉儿救了我,也救了王府,赵家有所求,只有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她了。”
钱令梓抬头看他,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
“明日,玉儿大伯父就到了,他是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
“我们的婚礼?”
“我和玉儿。”
“你和玉儿。”钱令梓的眼眶再也不争气,豆大的眼泪直直的滚落下来,他不但要纳了赵玉儿,还要给她婚礼。
钱令梓突然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收回抱着他的手,强颜欢笑道:“祝你们白头偕老。”说完,眼中又淌出泪。
“团团,我说过,有苦衷的,况且,李侧妃和翡翠你也没有在意啊!你就把玉儿当成翡翠她们一样不行吗?”世子也松开她,转而抓着她的肩膀。
对啊!我在在意什么呢?钱令梓自嘲的笑了笑:“世子,夜已深,我要歇下了。”
“团团!”世子很受伤的收回手,无可奈何的说到:“以后你会明白的。”
眼睁睁看着世子出门,看着他挺拔的身躯消失在院门,钱令梓再抑不住悲伤痛哭出声。
桃儿李儿闻声赶来,看她哭得如此悲伤,一时间吓到不知该如何是好:“小姐,小姐!”
“无事!”钱令梓强撑着说出两字,却还是泣不成声:“你们、先、出去,我想静静。”
桃儿她们见劝不了钱令梓,便连忙去请刘嬷嬷。
刘嬷嬷到的时候,她已经止住了哭声,正提笔写着什么东西。
见刘嬷嬷进来,钱令梓的笔顿了一顿,没来得急拭掉的眼泪滴在字上,化做了一个墨团。
本来听桃儿说钱令梓痛哭,刘嬷嬷是不太相信的,她看着钱令梓长大,从小到大哭过的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这才来王府几天就转了性?还是说被欺负得很了?
看钱令梓真哭得如此伤心,刘嬷嬷连忙上前:“我的小姐呀!你这是做什么?是不是世子又说了什么?”
“嬷嬷!”钱令梓难得失态扑在刘嬷嬷身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好好好,回家回家!”刘嬷嬷顺着她的话,安慰到。
半晌,钱令梓终于不再掉泪,她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刘嬷嬷:“让嬷嬷见笑了。”
“小姐这是什么话,老奴看着你长大的,人都有情绪,发泄出来就好了。”
听到里面没了哭声,李儿连忙打水进去。
钱令梓洁面之后又坐回桌前,看自己写到一半的家书,揉成团丢到水里,晕开再看不清写了些什么。
“今天晚上的事,不要传出去,我已经没事了。”钱令梓洗了脸就跟换了脸一样,看不出刚刚那个脆弱的模样:“嬷嬷先回去休息吧!我要休息了。”
躺在床上,钱令梓开始思考,赵玉儿明明说她不想嫁入王府,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做出死都要嫁进来的模样呢?
第一次是在二婶面前,把二婶气得半死;
第二次是在新婚第二天早上,这次做了什么不知道,但也没能得逞;
第三次直接刺杀我,虽然没有得逞,但这样做了之后不是更不能嫁入王府了吗?
第四次自杀,最后直接告诉我不想嫁入王府,难道说,她说的是真的,每一次看上去是在求嫁,实际上是在求不嫁,她为什么不能直说呢?
而世子又说他是有苦衷的,如果他们俩说的都是真的,既然两个人都不愿意,那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是一定要他们结合才行的呢?
钱令梓百思不得其解,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第二天,钱令梓展开信纸重新开始写信:
“父母亲大人膝下,谨禀者:儿成亲已月余,王爷王妃待儿不薄,现又有孕在身,事事顺心;四月花期已至,蔷薇香重,夜深好眠,勿挂念。
城南宅子空余,儿划于果儿做成衣营生,但恐无人照看,望母亲挑选合适人选。
闻刘嬷嬷道,李国公府有一嬷嬷与刘嬷嬷自幼相识,来自吴地,年事已高想返回家乡。因儿有孕,为孩子求善积德,已允此事,还望母亲相助。
虽时光如隙,午夜梦回间,仍以为幼时,儿无能承欢膝下,心中甚悲。双亲年齿渐高,儿在千里之外,有缺孺子之职。望双亲保重身体,以期来日。
专此谨禀,恭请福安。
另问哥哥嫂嫂、弟弟妹妹安好。”
写好信,按上火漆,看着桃儿递了出去,她的心情已舒解几分。侧院传来呼喝之声,钱令梓寻声而去,四个女子正在练习,她居然忘了公主姐姐给的门神,之后要用起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