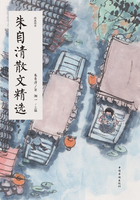时 间:清乾隆11年至18年
(公元1746~1753年)
地 点:山东
人 物:
郑板桥:潍县知县,54岁(初出场年龄,下同)
沈椒园:御史,后为知州,60多岁
王 凤:郑板桥老仆,65岁
砚 耕:郑板桥弟子,12岁,女
高先生:砚耕父,秀才,40多岁
郭先生:潍县乡绅,近50岁
县 丞:潍县县丞,后为州同,近50岁
樵 根:小和尚,20岁
桑 叶:小尼姑,17岁
田廷林:潍县豪富,50多岁
毛掌柜:潍县富户,近50岁
田廷烳:吏部侍郎,田廷林之弟,40多岁
五什子:田廷林家人,30多岁
一
暮春时节。原野。白云,青山。
三头毛驴,从白云青山深处悠悠而来。郑板桥身着布衣长衫,骑在驴背上,王凤走在头前。
他们越过山坡,趟过河流,穿过树林……
郑板桥或陶醉景色,或捋须赋诗,或即兴作画……
王凤不时与他说笑着……
片名徐徐升起:郑板桥(六分半书)。
职、演员表字幕……
远方显出一个城镇的轮廓,王凤指点着说着什么。
郑板桥面露喜色,遥遥望去。
一顶披彩官轿,径直迎上前来。
潍县城关,西门。披红挂彩。
一个小衙役在城门上翘首远望。县丞、田廷林等一班吏员乡绅,衣冠楚楚候在门外。几个乡绅在悄声议论着。
瘦子:“上任不坐大轿,这新任知县也真够体面的了。”
郭先生:“听说是个书画家哟。”
毛掌柜:“书画家!怪人!啐!”
小衙役:“知县大人来啦!”
大路上,披红官轿拥拥而来。鼓乐齐鸣,鞭炮作响,县丞、田廷林等人迎上前去。
官轿停住,众人躬身屏息。小衙役上前揭开轿帘,轿内无人,只有一箧书画、一包行囊。众人惊住。
野外田边。郑板桥神情忧郁地注视着:
干裂的地板;
枯黄的麦杆;
乱葬岗,横七竖八的饿殍;
路上,逃荒、乞食的人群……
他心情沉重地、默默地向前走着。
一棵巨型银杏树下。一个小和尚朝一丛柳林学起了鸟叫。
柳林中走出一个小尼姑。
小和尚和小尼姑坐到银杏树下。
银杏树后,突然走出几个和尚和尼姑。为首的老和尚一声喝,小和尚和小尼姑被捆了起来。
郑板桥看到树下的情景,走上前来。问道:“这是为何?”
老和尚打量着,道:“寺中小徒,违犯教规。”
郑板桥:“通奸?”
老和尚摇头。
郑板桥:“谋财害命?”
老尼姑摇头。
郑板桥:“那他二人如何违犯教规?”
老和尚:“……私自相会……”
郑板桥:“你二人为何私自相会呀?”
小和尚:“……她母亲病重,家中无粮,要我告她……”
郑板桥:“此情可真?”
小尼姑哭着,点了点头。
郑板桥:“你二人何时相识?”
小和尚:“我二人本是同村,父母将我与她许为……夫妻……只因天旱,父母饿死,我剃了发,她也……”
郑板桥默然。
北关外路上。县丞、田廷林等向这边寻来。
银杏树下。郑板桥走到小尼姑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桑叶”。
“你呢?”
“樵根。”
“桑叶……樵根……”郑板桥目视老和尚、老尼姑:“她二人说的可是假话?”
“不假,不假。”
县丞、田廷林等人来到面前,老和尚等慌忙欲走,郑板桥摆摆手迎上。
县丞:“潍县大小吏员恭迎知县郑大人。”
老和尚等注视郑板桥,大为惊异。
主簿:“县丞大人。”
田廷林:“潍县乡绅士民恭迎郑大人。”
主簿:“田廷林,田大人。”
乡绅们依次上前施礼。
主簿:“毛掌柜、郭先生、谭先生……”
郑板桥一一答礼,爽朗而亲切地:“郑燮奉调来潍,不胜荣耀,日后与各位朝夕相处,诚望各位多多相助。”
田廷林:“大人言重。我等惟大人之命是听。”
主簿:“各位已备下酒宴,为郑大人洗尘,请大人上轿入衙。”
郑板桥:“天干地旱民不聊生,洗尘就罢了。”一指小和尚和小尼姑道:“此二人旧有婚约,因家境贫寒削发为僧。方才二人相会,被老方丈等人擒住,各位以为该当如何处置?”
众人注视不语。县丞微微晃着脑袋:“全凭大人……”
田廷林:“小人等愿闻大人高见。”
郑板桥目视老和尚、老尼姑:“本县代你等处置如何?”
老和尚、老尼姑:“老爷吩咐……”
郑板桥:“二位小僧私自相会有违教规,理应严惩。”
众人点头。郑板桥又道:“但二人削发本属灾荒所逼,私自相会又为家中断粮、母亲病重,自当别论。”注视众人:“本县有意将他二人还俗,归乡成亲,侍奉老母,你等以为怎样?”
众人一齐惊住。樵根、桑叶惊疑地抬起头来。
郑板桥对老和尚、老尼姑:“你二人可允?”
老和尚、老尼姑不敢相信地点着头:“老爷吩咐……”
郑板桥对县丞、田廷林等人:“各位以为是否可以算是公断?”
众人低沉着脸,不置一词。县丞晃着脑袋:“全凭大人……”
郑板桥哈哈大笑,吩咐为樵根、桑叶解绑。
樵根、桑叶上前就要跪倒。郑板桥拉住二人,吟咏似地:“是谁了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田廷林冷眼旁观。道:“大人处置可谓公断,只怕日后对佛门诸人……”
郑板桥:“佛门以善为本,本县救民疾苦,岂非同出一辙?”
田廷林柔中带骨:“郑大人爱民之心,非比寻常。”
郑板桥:“为民父母自当为民作主。”扫视众人:“眼下百姓悲苦无状。本县拟布告开堂,广听民间疾苦,各位有何见教?”
田廷林等人愕然相视。
二
日。东关街头。
墙上赫然的布告。一群百姓围在布告前看着、议论着。砚耕拐着一只小篮子走来。
县署大堂。
郑板桥威严端坐。堂前空空,只有两行皂役颇为威风地侍立着。
日近正午,郑板桥来到院里。王凤迎上摇了摇脑袋。郑板桥眉头尖蹙,欲言又止。
东关街头。看布告的百姓们围着砚耕说着什么。
五什子和几个家丁从街口走来。百姓们慌忙散去。
太阳西斜。县署大堂外。
堂门大开,阶前一群麻雀在觅食。
夜。县署后院,书房。
正面墙上,挂着一幅镶金“清”字匾。两侧是李蝉、苏东坡的竹石图和金农、黄庭坚的笔墨真迹。
郑板桥身着长衫在喝着闷酒。他闭目哼了句昆曲,抬起头来。
“清”字匾赫然入目,熠熠生辉……
——乾隆六年。京师,沈椒园书房。
郑板桥身着崭新的文七品朝冠,坐于一侧。
沈椒园满面春风:“你攻读多年,中了进士,争得七品冠带,老夫也正为你高兴。”
郑板桥:“学生能有今日,全凭恩师……”
沈椒园:“嗯,往日之事休提。你今走马上任,老夫尚有一字相赠。”
郑板桥:“学生洗耳聆教。”
沈椒园轻一招手,家人摆过笔墨。
沈椒园大笔一挥,写下一个大字:“清”。
沈椒园;“我等大清臣僚,当以‘清’字为立身之本,报君为国留芳百世,断断不可弄奸耍滑,害国害民。”
郑板桥庄重地:“恩师教诲,学生刻骨铭心!”
县署后院,书房。
郑板桥把酒杯摔到地上,站起来。
三
街上。郑板桥、王凤走来。
一个临街的门里闪着火光,二人走近,透过门缝,见一位老翁正在灶前熬盐。
老翁刮起锅底上的盐沫放到嘴里,又连忙吐了出来。
郑板桥欲要敲门,王凤朝对街口的“毛记盐行”指了指。二人走去。
“毛记盐行”。门窗紧闭,门前一个牌子上写着盐价,郑板桥靠到牌前,辨认着:“粗盐……斤……三十五文……”吃惊地:“潍县地处海滨,盐价竟如此之贵!”又靠前看着。
晨光微露。一条石径小巷,郑板桥、王凤漫步而来。
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二人循声,来到一座木板房前。
木板房内,砚耕湿毛巾扎额,在背诵着《兰亭集序》。声音抑扬顿挫,清脆悦耳。
郑板桥站在窗前,点着头。
屋内,砚耕换水开门,见到有人连忙退后。
“打扰,打扰。”郑板桥上前,亲切地:“小公子读书,为何还不休歇?”
砚耕见是两名老者,略放了心,道:“爹爹教我,每日如此。”
“难得,难得。”郑板桥上前一步:“你爹爹可在?”
砚耕神情突变,转身回到屋里。
郑板桥、王凤随之走进。
屋内,墙上挂着一幅“新篁图”,图下题着一行字:“小女砚耕十二龄作”。
郑板桥打量砚耕,这才发现面前是一位女孩子。他看着“新篁图”,连连点头。
“新篁图”一侧是一幅“群雁图”,群雁凌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图上墨字:“小女砚耕存念,父字。”
郑板桥仔细端详“群雁图”,大为赞赏。
郑板桥:“你爹爹呢?为何不见?”
砚耕抽泣起来。
——木板房内。砚耕作完了画,要饭吃。高先生揭锅锅空,找米米无,只好找出两个铜板走出门去。
——“田记粮行”。高先生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掏出铜板买粮。铜板被丢了回来,卖粮人指指价格牌,示意钱太少,让他走。高先生无可奈何。
——潍北盐田。高先生挑起两筐重重的盐。
——街头。高先生卖盐,百姓争相购买。毛掌柜带着一伙人赶来,掀翻盐摊,抢走盐担。
——毛掌柜家厢房。高先生被打得皮开肉绽。砚耕大哭,被强行拖走……
县署大堂。
郑板桥拍案怒骂,喝令加刑。毛掌柜跪地求饶。
四
日上三竿。县署后院侧室。
郑板桥边喝着酒边恣悠悠地哼着昆曲:“俺笑着那戒酒除荤闲磕牙……”
小衙役入内,小心地:“大人……”
郑板桥不理,依然喝着哼着:“做尽了真话靶……”
小衙役:“大人,该上堂了,小的们都在等着。”
郑板桥眉眼一抬:“上堂,上的什么堂?”
小衙役:“每逢双日上堂,这是规矩。”
“散去,散去!”郑板桥晃着酒杯:“笔墨端来。”
小衙役不解其意,愣在那儿。
王凤入内,端过笔墨,放到案上。
郑板桥“嘿嘿”笑着,酒杯一放,提笔,神采飞扬地写起来。
王凤:“大人,高先生来了!”
郑板桥喜上眉梢:“快请,快请!”
高先生和砚耕走进。
高先生上前要拜:“大人……”
郑板桥摆手:“嗯,罢了,罢了。”
高先生:“我父女二人多蒙大人救助,不胜感激之至。”
郑板桥一笑,指着案上:“高先生看本县书法如何?”
高先生走过,仔细观赏,真诚地:“大人书法,真、草、隶、篆四体相参,又颇有作画之工,真是标新立异,独具一格!”
郑板桥哈哈大笑,又端起桌上酒壶:“高先生,熏上几蛊如何?”
高先生连忙摆手:“小人对酒,实在不能。”
“哦!”郑板桥笑道:“老夫平生只喜得喝上几杯黄汤。‘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高先生:“大人想是海量。”
郑板桥:“酒量倒也平常,只是嘴馋。”晃着酒壶,夸耀地:“宋朝钧窑彩釉,如何?”笑着,示意高先生落坐。
郑板桥:“高先生才学人品已有所闻,日后还望多多助我。”
高先生:“晚生不过一个穷秀才,大人如此看重自当效力。”
郑板桥:“依先生看,板桥治潍,当以何事为先?”
高先生思忖片刻,坦诚地:“民冤鼎沸,自当平诉,但潍县连年大旱,数十万饥民嗷嗷待哺,更需大人解救。”
郑板桥点头。王凤拿着一包银子走来,递给高先生。高先生慌忙推辞。
郑板桥:“这又何必。拿去作些生计,也免得与那些盐商们呕气。”
高先生只好接过,道:“我为了砚耕,才不得不去贩些私盐,哪想……只要这孩子能有所长进,我也就……”
郑板桥:“这孩子生性聪敏,又有你作指教,日后还怕没有长进?”
高先生:“大人哪里知道。我这一辈子专攻画雁,这孩子却偏偏喜爱画竹、画兰。无师指点,只怕要误了她的。”
“哦?”郑板桥一笑,“本县倒是画得几笔竹兰,高先生不弃,本县收她作个徒儿如何?”
高先生:“砚耕怎有这等福气!”
郑板桥:“如此说,这个徒儿我是收定了的。”
高先生喜形于色,连忙拉过砚耕给郑板桥磕头。郑板桥得意大笑。
小衙役送上茶,郑板桥呷了一口,问道:“本县张贴布告,广听民间疾苦,为民伸冤,不知为何百姓避而不来?”
高先生:“一是田家作祟。”
“哦?”
“田廷林,潍县豪富之首、万恶之源。”
“嗯……”
“二是百姓不敢轻信。”
“这是为何?”
“前任知县哪一个上任之初,也要喊上几句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到头来,一个个都成了田家的座上客、马前卒。”
“俗吏!”郑板桥愤愤而起:“这班俗吏!”他踱了几步,注视室内雕梁粉壁,忽然大喊:“来人!”
王凤和小衙役等跑过。
郑板桥:“吩咐下去,县署内外,即刻冲洗粉刷!越快越好!”
王凤奇怪地:“大人……”
郑板桥:“俗吏臭气污染多年,不一力扫除,怎能更换新气!”快步出门,环视院内,一指高耸森严的院墙:“打开!打开!都打开!”
县署内。
后院。一班衙役挥锤抡镐,将院墙砸开了几个大窟窿。砚耕和一群孩子们欢呼着。
大堂。一班工匠里里外外冲洗、清扫、粉刷。许多百姓聚拢围观,高先生给大家讲着什么,百姓们露出惊喜的神情。
大堂内。郑板桥在理案,告冤的百姓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
大堂外。许多百姓在递着状子,王凤、小衙役接收不暇。
五
县署后院,公事房。
郑板桥阅状,愤愤拍案:“恶绅!”
他感情冲动地踱着。县丞身着文八品朝冠双目微闭,微微晃着脑袋,如入梦境。主簿、王凤等关切地注视着。
郑板桥站定:“这等大富恶绅如不惩治,百姓何以安生!”断然地:“唤典隶,传田廷林到堂!”
小衙役欲去,主簿起身拦住:“大人……”
县丞睁眼看了看,又闭目晃起脑袋。
田府,客厅。
墙上挂着几幅“空山无人”“行云流水”的山水画和古体字匾。陈设豪华、雅致。田廷林在案前作画,几个豪绅围在一边。
毛掌柜:“这江南蛮子一来,就把我等踩在脚下,这还了得!”
瘦子:“田爷,你老得拿个主意才是。”
郭先生看看田廷林看看毛掌柜,欲言又止。田廷林还是作着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