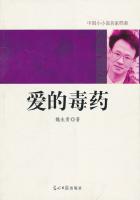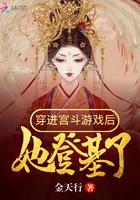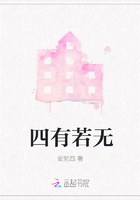“道旁苦李”这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讲述神童王戎的故事。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七岁时与一群孩子在路上玩耍,看见路旁有棵李子树,上面结满李子。孩子们一窝蜂跑过去摘李子。只有王戎视而不见,一动不动。大家问他怎么不去摘李子,王戎说:“李子树长在路边,却还结这么多李子,李子一定是苦的。”大家一尝,果然是苦的。
这个故事很有趣,小时候就记住了,佩服王戎的智慧。去年夏天到美国女儿家避暑。她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居民区。那里比北京凉快得多。这个居民区面积不大,周围还有几个与它类似的居民区。住房通常是平房,也有两层楼房,但没见过三层楼房。来到女儿这儿凉快是凉快了,但极不方便。没有交通工具,哪儿也去不了。我垂涎已久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离女儿住处仅两小时的车程,咫尺天涯,就是无法去。白天女儿女婿上班,我们留在家里,同蹲禁闭差不多。吃过晚饭我同内子便出去散步。我们不仅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散步,还走到邻近的小区。两个月来,我们把邻近小区都走遍了。
这里每家都有柠檬树和李子树,院子里有,门前也有,道旁也有。有的家还有杏树。每棵李子树都长满紫黑色的李子,熟透的落在地上。有的住户已迁走,大门紧锁,门前的李子树仍果实累累。我在树下地上捡了两个李子,回去女儿女婿一起说我:“你怎么摘街上的李子?”我说不是摘的,地上捡的。他们仍然责备我:“地上的也不要捡。”我只好说想检验王戎的话灵验不灵验。为此我还向他们简单地讲了竹林七贤和《世说新语》,但他们仍对我不满。我把李子洗过吃了一个,非常甜。老实说,我在国内还没吃过这么甜的李子。遍地李子树,棵棵长满李子,落了一地,却没人摘。美国人的脑子是怎么想的?我揣摩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是我的我一定要,不是我的我绝不要。”
今年夏天是在北京过的。溽暑天气实在难熬。开空调吧,就是开到二十八度也觉得皮肤发紧,不舒服,只能开小风扇。原来想重译《日瓦戈医生》,但脑子发胀,译不下去。一个半月只翻译了俄国女作家苔菲的十三篇短篇小说,加起来还不到两万字。
只要天不热得无法喘息,我傍晚都到明城墙遗址公园散步。我散步的路边有两棵树根连在一起的桑树。我看桑树发芽,抽叶,结出桑葚;桑葚由青变紫,熟透的落在地上。总有人在地上捡桑葚,大人比孩子多。一天我走过时看见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在树下捡桑葚。忽然一个孩子把一根短棍朝桑树扔去,打落的桑葚就不止是紫色的熟桑葚了。他快活地向妇女喊道:“妈,快点捡!”我对孩子说:“公园的桑葚不能打。”他说:“谁说的?”。母亲不说话,脸上露出凶相。我知道再说下去没有好结果,只得向前走了。没过几天,桑树紫的、青的桑葚都没有了,树上垂挂着打断的枝条。明城墙遗址公园原是居民区,北京人家里喜欢种枣树和香椿树。居民迁走,树留下了。春天香椿树如何遭抢劫,我没看到,因为香椿树都不在路边。但路边枣树被折磨的惨状我看见了。枣还没长熟,人手够得着的树枝都已光秃,只有几颗青色的小枣躲在树梢上。我揣摩我们的同胞的想法:“是我的我一定要,不是我的我也要。”我对那位母亲的态度深感忧虑。她怎么不管孩子打桑葚呢?孩子顶撞老人怎么不说孩子呢?能教育出好孩子吗?
我想起七十年前的往事。我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带我逛北海公园,走到五龙亭的时候,我采了路边的一朵喇叭花,准备给姐姐,她喜欢这种花。母亲看见立刻说我:“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你要记住。”她为了让我记住,还编了个神话。她说喇叭花有花神,你掐它的花,夜里它会来找你,把你缠得透不过气,我也不救你。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采花了。
时间过得飞快,我已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傍晚散步时,不时想起美国的甜李、中国孩子向桑树扔棍子,特别是那位母亲的凶相。时间是倒退还是前进了?中国人何时才能分清“公共的”和“自己的”?男孩子又如何教育自己未来的孩子?想着想着不觉走到桑树前,桑叶满枝,树下一个人也没有了。
附:写完这篇小文和内子到天坛散步,看见一个中年汉子在用竹竿打银杏树上的白果,神情自若,旁若无人。我走过去看,地上袋子里已装了半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