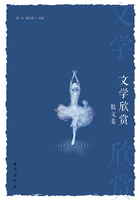流沙河先生是我敬重的作家,虽至今悭吝一面,但他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有,可我无法说清我与他的关系。说神交吧,应当彼此精神沟通,可我知道他而他并不知道我,说神交未免一厢情愿。说心仪已久吧,只能说我对他的仰慕,包括不了我受到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干脆就说我与流沙河吧,这等于我和他并列,平起平坐,也不敢当。只能就事论事了。
一九五六年我在北京俄语学院当助教。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我在新华书店买到流沙河先生的诗集《告别火星》(作家出版社出版)。读后觉得小诗清新可喜,与过去读过的反映阶级斗争或抗日战争的诗不同,诗人抒发了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如《表》《火柴》和《金鱼》等。
表
得滴——得滴——得滴……
为辛苦的人伴唱,
为偷懒的人叹息。
红色的秒针,
光阴的鞭子,
追赶主人,一点也不留情。
火柴
你烧毁自己,
把火给人类,
短促的一生只不过几秒钟,
却比虚度百年的人更可贵。
金鱼
一只金鱼,
摇着轻飘飘的大尾,
披着红艳艳的花衣,
吻着绿茵茵的水草,
沿着亮晶晶的玻璃,
游来游去,
自言自语:
“哦,原来大海这样美丽!”
这三首诗现在看都没有问题,当时也没有问题。但由于《草木篇》的缘故流沙河被划为****分子,他所写的诗就都有问题了。我不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四川文联便开始批判他了,仍向平时接近的人推荐《告别火星》。同屋老刁专心钻研俄语语法,从不读文艺方面的书。我向他推荐《告别火星》。没想到他不仅读了,对其中的几首还很喜欢,竟把上面引的三首抄寄给他弟弟小刁。小刁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学生,系团总支书记。小刁必定也喜欢,不然不会在一次团员大会上朗诵了。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一栏里转载了《草木篇》,并加了批判流沙河的编者按。我这“吹捧流沙河”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系里的批判对象。批判我并不冤枉,我的确向人推荐过《告别火星》,但却没有“到处宣扬《草木篇》”,因为《告别火星》没收入《草木篇》,我没读过。让我深感内疚的是老刁也受到批判,小刁因在团员大会上朗诵过流沙河的诗竟被划为****分子。如果不是我,他们兄弟两人都安然无恙。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草木篇》我是在《人民日报》的“什么话”里读到的,《人民日报》转载的目的是供大家批判,却没想到我不但不批判反而非常喜欢这组诗,并且背下来。一九五八年十月我戴着大红花光荣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在田地里把这组诗背给一同下放的老郑听。老郑就是当今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军人物郑佩欣教授。他也很喜欢,很快也背下来了。我们还背给其他下放的人听。如果这时候批判我,倒真是“到处宣扬《草木篇》”了。我们还把周围的人分别戏称为“白杨”“藤”“仙人掌”和“梅”等。如果领导知道,我们肯定要挨批判的。可当时不知为何却没人汇报。“****”期间,还有人给老刁贴大字报,揭发他在反右运动中,和“****分子”蓝某某一起宣扬《草木篇》,但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影响,只能算“流沙河诗歌事件”的余波罢了。况且我沾先君的光,侥幸漏网,只被调离北京。
如梦如烟的岁月过去了。此后流沙河先生出的书我遇到的都买了。他的《锯齿啮痕录》读过几遍。他的文字凝练,蕴藉棘刺,令我倾倒。通过他的作品,不知为何使我更加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这时可以用我对他“心仪已久”了。听燕祥兄说,流沙河伉俪到过北京,并曾同燕祥夫妇一起到承德旅游。可那时我正在俄罗斯教汉语。
后来收到四川作协黄先生来信,向我要拙著《寻墓者说》,并替流沙河先生要一本。我知道流沙河先生喜爱俄苏作家,“****”期间抄家的时候他写过一首短诗《焚书》:“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可见他对俄国作家契诃夫难割难舍之情。话说回来,我们这代人有谁不热爱俄国和苏联文学呢?
我把送给黄先生和流沙河先生的书寄给黄先生,并在信中希望得到流沙河先生的《Y先生语录》。黄先生回信说《Y先生语录》已经没有了。我本未抱多大希望,所以也未十分失望。一星期后忽然收到黄先生寄来的流沙河先生的书和一幅字,黄先生说:“沙河先生说书没有了,可今天早上他夫人送来《Y先生语录》和一幅字,现寄上。”我知道流沙河的字很难求,不存非分之想。如今收到书和字,大喜过望。书上写道:“英年先生一笑,流沙河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字是一首七绝:
野外小河红莓花,梨花天涯喀秋莎。
转眼兴亡悲往事,白发人听后庭花。
左上方写的是“欣闻将赠《寻墓者说》一册,流沙河”。下面是两枚印章。
遗憾的是至今没能见到流沙河先生,我想总会有见面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