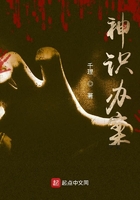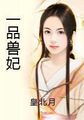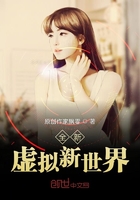蒋路同志逝世已经九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他大概因为耳朵背,同人说话的时候,右耳总靠近说话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很响,特别是打电话的时候,声音格外浑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看到出版社出书越来越从经济效益出发,一些有文学和历史价值的书出不来,而满足读者不健康趣味的书却成泛滥之势。我给蒋路打电话,发牢骚,说现在没法译书了,想译的书没人出版。他显然与我有同感,但还是为出版社辩解了几句,送我两句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是他治学的格言,他的《俄国文史漫笔》和《俄国文史采微》就是他这条格言的实践。当然,还得付出辛勤的劳动。他多次穿越半个北京城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凌芝夫人写道:“晚年他将历年积累的治学心得加以爬梳归纳、字斟句酌写成《俄国文史漫笔》。这本书倾注了他近十年的精力,被他视为最爱。无论从史学、构思或文笔角度看,篇篇都闪烁着作者的智慧。有时为了补充或核实一些资料,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不管酷暑还是严冬,他和我乘坐公交车去国家图书馆,一去就是一天。”
一九九七年收到他寄来的《俄国文史漫笔》,他打电话说,这些文章都是离休后写的,请我读后提意见。“请提意见”这类话现在不过是客套话,不能当真。但我知道蒋路却不是随便说的,他真诚地希望我对他的文章提出意见。我认真阅读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博览群书》上。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这本书是难得的好书,涉及俄国文史方面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往往又是正统文学史略而不提的;如民粹派、哥萨克和民意党女侠索菲亚等,书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读者未必多,因为书中讲的都是留里克和罗曼诺夫两个王朝的事,没有一定俄国文史知识的人,不一定读得下去。如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自己也未必读得明白。那时我对俄国历史很不熟悉,连罗曼诺夫王朝的朝代也排不下来。一九八九年到苏联教汉语后才拼命补课,即所谓“恶补”。我说把《博览群书》给他寄去。他一定不让我寄,说他儿子可以买到。他在任何一点小事上都不愿给人添麻烦。我说去看他,他回答住得太远,天气热,不要来了。我看他并没有什么事,知道他不喜欢无事拜访,便没有去。二〇〇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一进会场就看见蒋路。他从前排走过来同我热情握手。他瘦得厉害,但精神很好。我还以为这是通常说的老来瘦呢,说明他身体不错。吃饭的时候他招呼我到他那里去,他旁边坐着绿原,前面是梅志。记得他告诉我,社里一位他赏识的女编辑准备搬入老年公寓,他觉得住老年公寓未必合适,但又不知如何劝阻。这是我与蒋路最后的一次见面。
蒋路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一九四七年我所在的中学转移到阜平县陈南庄,在山坡上开设了一间简陋的图书室。我借了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以为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传记。读了才知道不是,而是另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大剧作家。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忘了,却记住译者蒋路的名字。上世纪五十年代读过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对前者的兴趣大于后者,特别是屠格涅夫对果戈理的回忆。那时我正迷恋果戈理。我不喜欢备受赞许的《怎么办》,结构杂乱,作者不过借形象和情节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已,但蒋路对两本书的注释非常详尽,令我佩服。我那时天真幼稚,也动了翻译念头,很想向蒋路请教,但连他在哪儿工作都不知道。
光阴荏苒,一九七七年春天福建师范大学组织“鲁迅序跋研讨会”,我和蒋路都参加了。在那次会上我才见到心仪已久的蒋路。一九七七年是万物复苏的年代,搁笔已久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为文化事业做一番贡献,所以来自出版社的人备受青睐。蒋路是著名的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国家出版社的代表,身边自然围绕着很多人,我无法同他接近。我倒拜访过住在二楼两端的林辰先生和戈宝权先生,他们是以鲁迅博物馆顾问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戈宝权先生告诉我他有《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原文版,回北京后我从他那里借来,并把它译成中文,并于一九八〇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蒋路住在几层楼、哪间房间我都不知道。研讨会散会后,不知谁组织部分与会者顺路访问浙江大学,游览西湖,其中有我和蒋路。在杭州我们同住一室,有了接触的机会。傍晚我们沿里西湖湖畔散步,谈起俄国文学。我说爱读作家回忆录,比如老阿克萨克夫写的《我与果戈理相识始末》,让我了解果戈理所处的时代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蒋路对回忆录也很感兴趣,他说也想读这篇回忆录,不知收在哪本书里。我告诉他收在一九五二年为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而出版的《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一书中。我有这本书,他要看我可以借给他。我们谈得很投机。回北京后没再联系,我没有到出版社找过他。一次看内部电影《悲惨世界》,在电影院门口与他相遇,他请我翻译库普林的中短篇小说。他说南京大学有意翻译库普林的作品,并寄来选目,但他觉得我更适合翻译库普林,说到这里电影开演了,我们一同进去看电影。我有点惊讶,因为他不了解我的水平就约我译古典作家的作品有点冒险。我那时对他还不了解,觉得电影院门口说的话未必可信。几天后他把库普林作品三卷集和一本库普林评传送到我家。他那时住在苏州街,我住在南池子,没有顺便的公交车,他是走来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拎着四本洋装书走路是很吃力的。他说:“你先译《冈布里努斯》,我准备收入《俄国短篇小说选》,然后再译其他小说。《摩洛》要译,其余由你选。‘冈布里努斯’是音译,没查出什么意思。”我译好《冈布里努斯》交给他。他看后叫我到出版社去,把稿子还给我。我发现稿子改动得很少,只用铅笔改了几个地方,并指出“跳舞”的“舞”并未简化为“午”。他说稿子可用,后面的译稿他不看了,译好后交给责编姚民有即可。字体娟秀清晰,凡见过蒋路字的人都知道。他问我还译了哪几篇,我说译了《阿列霞》。他要我把《阿列霞》交给他,这篇小说收入文学小丛书,一九八〇年出版,一次就印了十万册。这是我与蒋路接触的开始,以后接触多了,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蒋路的职务是编辑,有人说他是学者型的编辑。这种评价并不全面,学者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蒋路是深邃的思想家、眼光远大的出版家、知识渊博的学者、卓越的翻译家和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为人谦和,埋头工作,不喜欢出头露面,很少参加俄苏文学界的活动,所以同他接触不深的人,未必了解他真正的价值,以及他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并深受他影响的艾珉女士写到她同蒋路的一次对话: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更大?”艾珉问蒋路。
蒋路回答道:“按说,这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不可否认,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舆论作先导。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扫除观念上的障碍,这一点,欧洲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他接着说:“欧洲近代文学中有许多东西会对我们的传统观念形成冲击,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中国历来是帝王崇拜、祖宗崇拜,很容易产生迷信和盲从;不像近代欧洲的价值观,把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创造精神、开拓精神看得很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把尊重人、爱护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类思想精华被当成垃圾抛弃了。”
蒋路想把欧洲文化精华引入中国,像五四时期的先行者们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引入中国一样。他把出版事业看成实现理想的手段。立足点就高出大多数编辑。他翻译《怎么办?》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并积极参加《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蒋路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到。艾珉说:“有一天,我遇上一个有关俄国历史的细节问题,在饭桌上请教了蒋路,他的回答明确清晰,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捧出一部大书,专门把我找去做了一番详细的讲解,态度之认真令我大受感动,这才明白老编辑们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一年春节前,我得了四头漳州水仙,我知道蒋路夫人凌芝喜欢水仙,便给他们送去两头。那时我刚读完他们夫妻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发现他们把抹大拉的马利亚译成马格大林纳了。我对蒋路说了。蒋路顿足道:“这是编辑改错的。自己不懂,又不肯查工具书,连郑易里的英汉词典里都收入了。”他翻开郑易里的词典给我看。接着他强调从事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圣经和希腊神话知识,没有要学,起码遇到问题知道到哪里去查。蒋路是《欧洲文学史》的责任编辑,艾珉说:“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工作的罗经国老师告诉我,看了蒋路加工的《欧洲文学史》稿,他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或细节,他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处已重新调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写或重写。在他们看来,蒋路远不止是编辑,而应是重要作者之一。可是他们请他参与署名时,蒋路却坚决谢绝了。”蒋路对《欧洲文学史》的校订已经充分说明他的欧洲文学史知识何等丰富。但他还担任过《瑞典文学史》和《捷克文学史》的编辑。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学史》,判若天渊,质量上有极大的提高,致使编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当然又谢绝了。熟悉欧洲大国的文学史已属不易,而对瑞典和捷克这样小国的文学史同样如此熟悉,我想象不出第二人。蒋路编辑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充分表现出他甘愿为人作嫁衣裳的可贵精神。凌芝在《蒋路文存》编后记中写道:“《生活与美学》译者周扬主动提出请蒋路将他这本由英文转译的旧译本根据俄文校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被人视为畏途,如同改造一幢旧房屋,即要用新材料表现现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风貌,这实际意味着比重译一遍还难!可是蒋路做到了。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事人的离去,许多细节已渐渐暗淡起来,责编蒋路究竟为这本书的再版付出了多少心血也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获得了新生。成稿时,连俄文版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恢复了它的原貌。周扬看了改文,十分满意,主动把蒋路校三个字写在他名字后面,却被蒋路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后来周扬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结果照样被勾掉了。此书出版后周扬接见蒋路,问他有什么要求可以帮他解决,蒋路什么要求也没提。”这件事蒋路也跟我谈过,我再补充几句。他说几乎每个句子都要重译,可为了照顾周扬的面子,不得不保留周扬的某些词句,这是最费劲的地方。为此他绞尽脑汁。蒋路认为周扬译文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先行者的错误。周扬表示不要稿费,稿费归蒋路,但蒋路还是把稿费退回去了。周扬不知如何表示感谢,请蒋路吃了一顿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普希金文集》和《高尔基文集》等世界文豪的文集或全集。编辑程文说:“这都堪称是人民文学外文部乃至全社的支柱工程。蒋路同志是这些工程的总设计师和主任工程师之一。”而这些文集和全集都是在蒋路离休前完成的。他分秒必争,组织人力,制订编译体例,在离休前了却自己的心愿。蒋路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这几句概括的话,还不足以表示蒋路做了多少工作。
我没有找到蒋路对《托尔斯泰文集》等全集或文集制定的选目和编译体例,只找到他对《屠格涅夫选集》中“文论”部分写的意见,建议撤销六篇文章。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只引用两条:
①《侄女》:作者图尔及其小说在俄国文学中不占重要地位,我国读者对她更是十分陌生,而屠格涅夫的论文又太冗长;
④《关于“现代人”杂志决裂的原因》太简略,未能说明决裂的真相。该文自一八六二年在刊物上发表后,作者生前从未重印,可见他自己也不满意。
他建议撤销的六篇文章我一篇也没读过,想来一般读者也未必熟悉。蒋路用几句话就把撤销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概括能力之强,文字之凝练,非等闲编辑能做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知识何等渊博。
谁担任责编是成败攸关的问题。蒋路独具慧眼,善于识别人才,不问资历,大胆使用他所信任的编辑。艾珉一九七五年调入出版社,不能算老编辑。蒋路让她担任《巴尔扎克全集》的编辑。陈馥女士八十年代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个新编辑,蒋路委任她编辑《托尔斯泰文集》。这两套丛书就出自两位令人尊敬的女编辑之手。蒋路不仅敢于使用新人,而且热情帮助。艾珉写道:“记得我接受《巴尔扎克全集》的任务时,颇有些思想负担,这么大的项目,做砸了这么办?于是我坚持要蒋路复审。蒋路为我复审了《全集》的前三卷。期间对我的指点和启发,让我终身受益无穷……对于译稿,只要有一丝费解之处,他都要求重新核查原文,以避免理解上的错误;对于编辑加工,他要求顺应译者的文风,与原译完全融为一体;至于注释,他要求务必处处为读者着想,不但要使读者通过注释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还要尽可能帮助读者扩大知识面,了解西方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蒋路对译文的要求,对译者的尊重,恐怕没有人持疑义,但今天恐怕也没有人能做到。我与蒋路讨论过做“注释”的问题。我说有些译本,读不懂的地方译者不注,读得懂的地方反而注,令人啼笑皆非。他说注释应当像辞书的条目,概括地阐明事件或人物的主要特征。如注人物,绝不能仅注生卒年月,而要点出这个人最主要的方面。但字数又不能多,所以做注绝非易事。那时我们打算办个培训班,我请蒋路去讲如何做注释的问题,他勉强答应了。后因经费不足没有办成。我到他家表示歉意,看见他桌上摆着用工整的字体写好的讲课提纲。
今天有多少外文编辑像蒋路那样对待编辑工作呢?说绝对没有未免主观,但说少而又少是不争的事实。不少编辑不懂外语却担任外文编辑。有的编辑找他认为外语很好而实际上很差的人审阅。不但不能提高译稿质量反而糟蹋译稿。有的编辑不看就发排,制造出大量劣质译文。我们过多批评译者,却放过编辑和出版体制,因此刹不住劣质译文潮水般的涌现。不从源头整治,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蒋路非常重视培养出版事业合格的接班人。他用人只看才能和工作态度,不看政治身份。他所看中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蒋路非常赏识陈馥,她文学修养深厚,中俄文水平很高,但她像我们通常说的,属于“政治上不开展”的那类人,在新华社的时候还被错划为右派,到出版社以前没做过编辑。到出版社不久蒋路就让她担任《托尔斯泰文集》的编辑,对她十分信任,约稿、校改和退稿都由她全权负责。只有她遇到困难,才帮她解决。《托尔斯泰文集》出版后,蒋路满意地笑着对她说:“没想到托尔斯泰文集竟出在你手里。”艾珉和陈馥虽进入出版社的时间都不算长,但都是中外文造诣很深的人,与刚出大学校园的人完全不同,蒋路对后者的要求严格得多。对他们主要是培养,先干一年校对,再到编辑部见习。
我渐渐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熟了,有时路过出版社便上去坐坐,喝杯茶。一天我到编辑部,冯南江先生正在谈论《日瓦戈医生》,一口咬定没有俄文版,各国的译本都是根据意大利文转译的。大家都不说话,因为没人知道有没有原文版。我说有原文版。冯南江说:“你见过?”我说:“何止见过,我有原文版《日瓦戈医生》。”蒋路听了吃惊地问:“你真有?”我说明天拿来给大家看。
我真有《日瓦戈医生》的原文本。一九五八年我下放到青岛郊区李村镇劳动锻炼。在山坡上休息的时候,公社通讯员送来人民日报。打开一看,一则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新闻引起我的注意。说来惭愧,我这个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毕业生竟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何许人。苏联专家讲文学史的时候只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不讲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更加好奇。我给远在美国的叔叔写信,请他寄一本《日瓦戈医生》来。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日瓦戈医生》已经寄到北京。书是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封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被烈火焚烧。“文革”时期我被打成牛鬼蛇神,随时都有被抄家的危险。这本书被抄出来还得了,烧了又实在舍不得。我把它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夹在马恩列斯俄文版的著作当中。红卫兵再无知也不敢抄马恩列斯的著作。果实下的烈火可以解释为世界革命的熊熊大火。《日瓦戈医生》就这样逃过“文革”一劫。
我把书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们见了都很惊讶。蒋路当场拍板翻译,并指定由我翻译。当时不订合同,口头同意就行了。我说一个人翻译不了,蒋路说那你就再请一个人吧。我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秉衡老先生合译,老先生欣然同意。我们便干起来。帕斯捷尔纳克是诗人,诗人写的小说很难翻译。我们埋头翻译,不理会社会上发生的事。这时一场轰轰烈烈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了。蒋路不管当代作品,由另一位副总编辑主管外文部。我找他,他不说停译也不说继续译,态度模棱两可。我找蒋路,他说还是继续翻译,运动迟早会过去。我们松懈了,时译时停。运动很快过去了,出版社又积极起来。每天打电话问进度。我们像上了弦的发条,拼命翻译。出版社还嫌我们进度慢。孙绳武先生带着三个编辑到我家来,在日历上划了一道,说这天必须交稿,译好一部分就派人来取。我们按期交稿,责编程文先生干脆住在印刷厂,边看边发排。从交稿到出书只用了一个月时间。这样赶译当然无法保证译文质量。以后这本书一再印刷,我做过小的文字修改,但无法重新校订。我决定终止合同,重新翻译,也是受蒋路的影响。蒋路翻译的《怎么办》一九五三年出版,以后又出版过两次。我向他要过,他说已通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不再印刷,手头没有了。他请陈馥重新校改,并对她说不要有顾虑,就像她通常校改译稿那样校改。陈馥是极认真的人,把《怎么办》从头到尾校改了一遍,蒋路非常满意。当然,不会有高人替我校改《日瓦戈医生》,只好自己重译了。可我早已过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能做得到吗?
一九八九年我到苏联教汉语,课余时间到高尔基图书馆看书。看感兴趣的书,做札记,没有“收获”的想法。回国后在董乐山先生的“催逼”下,根据札记写的随笔陆续在《读书》、《博览群书》和《随笔》等杂志上发表,后以《寻墓者说》为书名结集出版。我寄给蒋路一本。他很高兴,打电话说:“你从翻译家变成作家了。”这句话是他随便说的,但我想起三年前他对我加入作协的冷淡态度。有人介绍我加入作协,需要两个人签名,我兴冲冲找蒋路。没想到他态度非常冷淡,他说:“加入作协没什么意思,你要加入,我可以签名。”我很扫兴,便找了戈宝权先生。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觉得蒋路的话太对了。
蒋路为人极其低调,谦虚和蔼,但他身上有股鼓舞人向上的力量,与他接触较多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蒋路培养过多少人,帮助过多少人,我说不清楚,但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