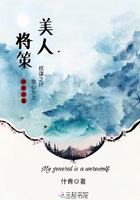慎芮回到南院,一推院门,见院门竟然已经闩上了。她上下比量了一下院墙的高低,发觉翻过去很费劲。于是返回园子里,折起柳条来。
“你怎么又回来了?”
“啊——”慎芮没提防,耳朵骤然听到这句话,魂都吓掉了,“我这肚子里可有弓家的骨血,四爷就不怕他有个好歹?”
“跟我有关系吗?弓家的骨血多了去了,难道都要我负责?”
“说得也是。”慎芮说完,就不再理弓柏了,专心折下柳条,辫在一起。
“你在干什么?”“四爷跟你说话呢。”“嗨——这丫头还上劲了,你信不信我敢打你?”
慎芮歪头看看暗影里的高大身影,哼了一声道:“我跟四爷有关系吗?你凭什么打我?我是弓家‘二’奶奶买来做‘二’爷的通房丫头。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跟‘四’爷半点关系都没有哇。”
“呵呵呵——这死丫头应答得倒快。你折柳条干什么?”
慎芮继续不理他,感觉柳条够用后,提在手里就走。
弓柏跟在她后边,想看看她干什么。
“四爷的妾室通房们都等着四爷呢,您怎么能晃荡着不回去?五个人轮流来,有四个晚上得守空房呢。您再这么懈怠,更不得了,您的女人们不定干渴成啥样了。”
弓柏噗哧一下喷笑出来,“你真是乡下来的?不会是媒婆为了凑数,随便从青楼拉来的吧?这种话都能说出口。再说,深更半夜,我们孤男寡女的,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呀?二哥可是经常不着家啊。”
慎芮站住,转头看着弓柏:“四爷这种小白脸型的,我不喜欢。就算暗示也不会找你的。所以四爷放心,我再干渴,也找不到四爷身上。”
“你——”弓柏抬手就想打下去。可是慎芮已经扭头继续走了,完全不把他当回事。
弓柏放下手,摸摸鼻子,不明白自己怎么没打下去。
慎芮走到南院的院门处,搬了个石头垫脚,把柳条辫成的藤条扔到院内的一棵树干上,打了个死结,抓住垂下来的一头,就开始往墙上爬。
“你还有这本事?”弓柏抱着胳膊站在她身后,看她笨拙的样子,估计爬不上去。
“四爷是不是怕了你院里的女人?这么晚了都不敢回去,怕她们给你吃****?”
“我院里的女人有这胆子就好了。等你生下二哥的儿子,二嫂估计又会把你卖掉。到时候我把你买了吧?”
“那敢情好。伺候完哥哥,又去伺候弟弟,细水长流,这生意真是不赖。”
弓柏没说话,见慎芮还真的爬上了墙头,然后从树干上解下柳条,‘咚’一声蹦下去,接着脚步声远去、消失。
“这是个什么女人?”弓柏咕哝一声,望望天上的星星,朝弓杉的院子走去。他院子里的女人晚饭时闹了别扭,哭哭啼啼的,让他头疼,不想回去。
慎芮走到西厢房,见房门还开着,正是自己离开前的样子,挡着半边门的凳子仍在原位挡着。她松了口气,还以为房门也给锁上了呢。
第二天一大早,慎芮刚从听荷院请安回来,就见南院里挤了好几个人,热闹得像菜市场。
“三姑娘,你终于回来啦?三房的孙姨娘说自己的翠玉簪子丢了,想到你房里看看,我们说等你回来再说。”蔡嫂子的大嗓门吼得孙姨娘直皱眉头。
“哦?翠玉簪子丢到了我的房里?那这件事得好好说道说道。我听说怀了孩子的人,最沾不得那些晦气物件。有些人专门拿了妇人们用过的饰物,涂上一些腌臜物,送给有了身孕的人,然后怀的小子变成了姑娘,又或者生下死胎的。”
“你说什么?!”孙姨娘一下跳起来,怒气冲冲地冲到慎芮面前,还没做什么动作呢,慎芮一叉腰,把肚子挺得老高。孙姨娘顿时想到面前之人是二奶奶买来生儿子的,刚扬起的手又生生放了下去,“我的翠玉簪子被人偷了!我是来看看是哪个不要脸的贱蹄子偷拿的!”
“我不关心孙姨娘的簪子是谁拿的,我只关心会不会有秽物进了我的屋子。所以,我现在可不敢进屋了。万一有什么秽物在里边,冲撞了二爷的骨肉就麻烦了。蔡嫂子、滕嫂子,麻烦两位去请一下二奶奶和三奶奶,这件事一定得查个清楚。二爷二奶奶盼个儿子容易吗?这才有点动静,就有人上门闹了,以后还得了?”
孙姨娘气得浑身发颤。闹半天,自己丢了东西还成害人精了。从她屋子里搜不出簪子就罢了,搜出了簪子还难洗自己的清白了。她一大早看到自己的簪子不见了,顿时就想到了慎芮头上,气得没吃饭就冲了过来找簪子,结果蔡嫂子等人不让自己进屋搜,非得等慎芮回来再说。
滕嫂子和蔡嫂子互相看了一眼,急忙使个眼色让身边的小丫鬟去叫人。孙姨娘来弓府两年了,平时鼻孔朝天,很不得人心。现在看她被慎芮气得不顾形象、怒气冲天,俱都笑着指指点点。一个别房的妾室,谁会把她当回事?
孙姨娘几时受过这个阵仗?在娘家时也算是个娇小姐,来了弓府,三奶奶见三爷爱护,明面上对她也算客气。被下人围着奚落还是头一次,孙姨娘气得大哭起来,好像慎芮把她欺负了似的。慎芮暗哼一声,转身出了院门,站在院子外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