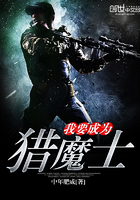刑午听言,立即起身,朝公孙稷一礼,公孙稷相扶,笑道,“如今孙周四处收寻王子下落,但我的府邸王子竟管放心住下,等王子伤愈,再商议归楚之事。“
刑午点点头,又道,“不知郤珲在何处,某可否一见?”
公孙稷道,“郤珲伤势颇重,正在疗伤,过两日,自会相见。”
……
公孙稷别刑午而出,穿过几个回廊,回到书房,郤珲侯在此。
“主子。”
郤珲行礼,躬着身子,公孙稷一个耳光扇去,郤珲嘴角流出鲜血,仍一动不动。
公孙稷沉下脸来,“你的胆子越发大了,私下与刑午联系,若不是我急时赶到,你的身份,你的性命,你大仇未报,便对得起你的家族?我辛苦救你,不惜威胁长桑君教你本事,便又对得起我?“
“奴知错了。“
“知错?“公孙稷提高声音,“你何时知错?你告诉我,你要手刃栾书,我便同意你去回城,原不知,你计划让刑午带你阿姐离去,还让她知道了真像,坏了我的大事,这次又是因这事。”顿了顿,自是一股恼怒。
“知道便也罢了,原以为你的阿姐会杀了孙周,想不到,她却贪婪孙周之宠,郤珲,她真是你郤氏之后?或者,她还不够恨孙周,若她的孩子因孙周而失,你说,她会怎样?”
郤珲听言,吓了一跳,“咚”的跪了下来,“主子不可。”他移到公孙稷面前,“若那孩子没了,阿姐的命也会没了,阿姐曾说,等她诞下孩子,她会助我一臂之力,阿姐自是憎恨孙周,怎会贪婪他的宠爱?否则也不会被罚于永巷。“
“如此,她为何还不下手?“
郤珲想了想,“阿姐未曾言明,奴认为,阿姐或是想利用孩子……而奴与刑午相约,是因为知道刑午真心喜欢阿姐,等奴与阿姐报了仇,奴恐凶多吉少,便让刑午带她离开,照顾阿姐。“郤珲心急,恳切道,“望主子成全,若阿姐没了,珲又岂能苟活于世?”
“你在威胁我?”公孙稷眉目一挑。
“奴不敢,奴自从找到阿姐,便与阿姐性命惜惜相关,奴只有她这么一个亲人,奴不想失去。”说着磕了一个头。
“如此……”公孙稷沉思不语,郤珲紧张的看着他,没人比他清楚,此人有多狠。
公孙稷坐在几侧,目光深邃,关于杀孙周,如今他并不着急,时机还未成熟,至少姬夫人那侧,他还没有把握,得到她的支持,对于君位,他不着急,他要等到最佳时侯,孙周掌握晋国,势力正盛,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他懂得,即然错失了第一步,他便等下去,犹如农人等候秋收,猎人等候猎物壮大,便可收获,此刻孙周丧命,对他是弊大于利,适才,他只是试探而己。
但要把辛夷送走,他是万万不会同意。
公孙稷看了看他,复尔勾起一股子笑容,“你且起身。“顿了顿,“你与你阿姐复仇之事,我己说过,暂不着急,你可让她安心呆在孙周身边,等侯时机,我会保她安全,你也可放心,至于刑午,我会送他归楚,你的阿姐,还是留下好。”
“主子……”
郤珲还想说什么,但见公孙稷神色,立即噤声,片刻道,“奴知道了。“
公孙稷瞟他一眼,“此番你若再善自行动,可别怪我不客气。“
“喏。”
*
再言辛夷居于永巷全然不知外间事,她静静的等侯孩子出生。
一场秋雨一场凉,树上叶子己枯黄,整日冷风阵阵。
在舜华殿,因君夫人照料,还有医者前来,来到这里,果真是被遗忘了一般,虽他们未至,然,公女时常偷偷送些东西来,被褥厚衣,樱也让公女带来她未完成的小衣,夜间,她便挑灯赶制。
生产所用之物,她不懂,便由亘妇开单子,让公女想法准备着。
而她白日仍旧去织室织布,都说初产会特别紧张害怕,甚至会有危险,然而,她一点也不惧,这孩子在肚子里,是如此有活力,特别近日,闹腾得厉害,像是呆不住,要急于出来,且,自怀孕以来,她遭受了太多,几经生死,她挺了过来,孩子也挺了过来,如此顽强的小东西,怎会在最后关头有事?
她盼着那天,孩子获生,她得到解放。
然而,后宫之人,也期盼着,却因为孩子出生,便是她的死期。
己有不少人暗地打听着,便是姬夫人也时刻注意消息,这日,第一次派了医者。
医者回来复命时,被孙周宣了去。
孙周忙于追查刑午,数日无眠,一无所获,神色难看,在朝堂之上,更是一脸严肃,前朝一片乌云压顶,人人自危,原是与宦者令交好者,不在少数,纷纷受到牵联入狱,不少人便得了个通敌之罪。
医者见国君之色,战战栗栗。
“孩子还有多久出生?”
“快了。”
孙周皱眉,“快了是何时?难道不能有准确时日?”
“这……”这可难到医者,他踌躇了半晌,“据臣观测,辛美人……”辛夷己除去封号,医者一慌,误口,惧君上责备,但见君上并未在意,又改口道,“其肚大而圆,有下垂之征兆。”
“那是何意?”
医者道,“据臣经验,往往产者半月前便会如此。“
“你是说还有半月?如今月中,孩子出生便在月未?“孙周诧异,如此说来……他算了算在回城的时日,突然一惊。
但听医者又道,“然,有时早产也会如此。“
“早产?”
医者解释道,“未到时日,孩子便降生。”
“为何如此?”
“这……”医者有些好奇,君上为何问这些问题,但他深知,辛美人这一胎,有诸多争议,自己不敢妄加猜测,便一一详细讲了妇人生产之事。
荚侯在孙周身后,不时瞟瞟主子,他又怎能不明主子之意,孩子若这月降生,不是早产便是……他也希望是真的。
然,但见孙周越来越苍白的脸,原是医者又谈起,产者多有血崩而亡,立即制止了医者的话,暗暗把他骂了一通。
又凑到孙周面前,“主子可放心,女子产子,如瓜熟蒂落,不会有事,不会有事。“
言毕,狠狠瞪了医者一眼。
医者也会看脸色,连连附合荚的话。
这时,孙周才挥挥手,医者退下,然其神色一直没有恢复。
再说姬夫人也得了辛夷半月之期,轻轻一笑,便向妕吩附道,
“到日子得提醒我,我要去提醒君上,该准备鸩酒了。”
这话被一旁的师玉闻得,不作声色,脑中自有一番打算。
鲁姬栾姬等几位姬妾,往长乐殿去的次数,也越发勤起来,言语之间,有意无意提到辛夷产子,己不到一月时间,君夫人听言,果真脸色难看,鲁姬便朝边上美姬使了眼色,这美姬便说来。
“那人凭什么为君上生孩子?幸得孩子出生,便是她伏罪之时,也算为夫人之子报得一仇。”
“就怕若是一位公子,君上见了,又不忍心。”另一姬又道。
“君上之言,怎能返悔?难不成夫人之子白白被人害死?”
“自是不能,若君上真有此意,我等一定拼死进言,还那孩子一个公道。”
众姬皆称喏。
至始至终,栾姬都未说一言,但观君夫人神色沉重,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明显对辛夷产子有着深深的怨气,她垂下眸子,暗松一口气。
次日是栾姬母亲祭日,便向孙周请示,出宫吊念。
栾氏祖坟之地,栾姬跪在墓前,诚心祈祷。
“阿母,若在天有灵,便护佑女儿,让那人与她的孩子……”她暗自腓腹,目光是一片清冷,心中仍旧有些忐忑。
片刻,蘋扶起她,见主子面有忧色,有些担忧,“近日主子为何心神不宁?“
对于这个不走心的小奴,栾姬淡淡一笑,并不言语,一旁的赵传见了,嘴角扯出丝讥笑,上前两步,凑近道,“美人放心,有夫人在天护着,美人必心想事成。“
栾姬听言,长吐一口气,瞟了赵传一眼,对他的话甚是满意。
赵传回头,朝蘋挑了挑眉,意在“示威“。蘋瞪他一眼,咬着唇闷闷不乐。
自宦者令出事,赵传便一直跟在栾姬身旁,这令蘋十分不悦,就不明白了,自己从小便侍候主子,怎么主子对她越发不亲了?连一个阉人也不如。
栾姬自不管小奴的小心思,蹬上马车回城,经过栾府,便令驾者停车,进了府。
栾黡出怔,栾府便由她说了算,一家子人全看她的眼色,栾姬在这里可谓扬眉吐气,更是少不了对那些人扬威。
发了一通“脾气”,众人不敢言,包括栾夫人,庶夫人个个低声下气,栾锜己被秘密处决,庶夫人至今不知情。
栾姬看她一眼,冷哼一声,便进了以前居住的小院,在那里,会让她想起以前的日子,虽然心痛,却能坚定她的心。
屏退众人,她独自走在小径上,有感叹,有悲伤,有回忆。
“妍到此处,可有想起与我初见之时的情景?”
突然窜入耳边的话,让栾姬吓了一跳,她立即倒退数步,险些摔倒,被一只手臂紧紧扶住。
待回过神来,但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你……你……”
“是我。好久不见。”
刑午紧紧的看着她,“你若想见我被孙周擒得,身首异处,可大声呼唤,我不会为难你。”
“什么?”
栾姬一惊,涨红着一张脸,“你这是何意?”
见她生怒,刑午扶好她,离她两步之远站定,瞟了瞟远外的小奴,并未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于是又把她拉到一树下。
“无意,恐你也知我的处境,猜你会如何?”言毕,望进她的眸子,要窥探她的想法。
同时,数月之后,再一次相见,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复杂之情。
这几月来,他的心思一直放在辛夷身上,几乎忘了她,他即将归楚,知今日是她母亲祭日,必会前住吊念,便扮着小厮,混进了栾府,只为一见,也想证实一些事。
栾姬嚅嚅唇,心中有愧疚,目光微闪。
“你认为我会如何?当真唤人来捉你?”说着,又觉一股子委屈,流下泪来。
“你怎会是楚人?你为何要做楚国奸细?你可知,这是灭族之罪?”此言带着责备,又是深深的痛惜。
她从未想过伤他,只是,他伤了孙周,又与辛夷不清不楚,她心中有恨,有不甘。
于是抬起头,怒视着他。
刑午扯出一丝笑,“你这番情景,可会让我误会,你对我有情。“
栾姬愣了愣,冷笑道,“我只当你友人,你知我心中是谁,而你?“她语气突然酸楚,“与大多男子一般,口是心非,见异思迁而己,你口口声声对她无意,如今,人人都传,你与她有情。“
栾姬以为他会如往常一样否认,却未听见他反驳,但见他低垂着头,一幅心思重重,好像思考什么重大之事。
“你……“
“然。“刑午打断道,“与她数次经历生死,如今才明白,是我错了。”
“你说什么?”
栾姬惊鄂不己,张着嘴,一幅不可思议的表情,只听刑午又道,
“****之事,我一直未看清,是我负了她。”
栾姬听言,只觉好笑,心中的怒火一拱一拱,“如此,你今日来寻我,就是告诉我,你喜欢她,来向我炫耀?”
刑午看着她,摇了摇头,“我来是为屡行承诺。“
“承诺?你对我有何承诺?“栾姬极力克制自己的怒意,指甲深深掐着掌心,怕控制不住会朝他抓去。
“我入晋宫,你当知什么原因,我不否认,为了楚,但也是因为你。“顿了顿,”我曾说过,会带你离开。“
“如此?”栾姬挑眉看着他,”充满讽刺,“你告诉我喜欢了别的女子,又说要带我离开,刑午,你是来羞辱我,你欲把我置于何地?”
刑午道,“我虽喜她,但对你放心不下,孙周身边永远不缺女子,你又是栾氏之女,便是如今栾氏没落,他仍会忌惮栾氏,以防栾氏再起,他怎会宠爱于你?你何须孤独于宫中?便是宠你,只会招来别人妒忌,而你的身后只有一个栾黡,凭他,何以给你支持?“
他句句实情,但听到栾姬耳里,只觉刺耳。
他说的这些道理,说了这么多,她怎能不懂,但,她宁愿他只说“因为我爱你,所以要带你离开。“
便是一句,就可顶数言,可是,他的关心却未带丝丝情意,或许他自认为对她还有爱,可她知道,那己不是爱。
是什么让他变了,当初的誓言,“刑午娶妻,必娶栾妍。“早己烟消云散。
是她?是那人,阴魂不散,勾搭了孙周,又勾搭了刑午,栾姬恨得咬牙切齿,这样的女子,怎配得到他们的爱?
然,虽对她恨之入骨,却面不作色,短暂的惊鄂之后,却是深深的失落。
栾姬低下头,“你都知道?你知道我的苦。”喃喃道,“可是,你要如何带我走?“
“我自有法子,你还有辛夷,我们都会离开晋国,然,你得先带她出宫。“
“什么?“栾姬猛的抬起头,目光充满怨恨,“原来,你来寻我,说什么为我着想,说什么带我离去,却都是为了她?”
似被说中心事,刑午目光闪烁,又定了定神,抚上她的双肩,“她与你一样,只是个可怜的女子,她怀有身孕孙周却弃之不顾,你曾与她姐妹相称,难道不愿助她?便是为了我。”刑午急道,“妍,我喜欢你,是因你心地善良,与别的贵女不一样,你不屑富贵,不屑权势,我带你离开,也是不想让你变得如那些后宫女子一般。”
顿了顿,“等回到楚国,若你愿意,我便娶你。“
栾姬心中一跳,瞪大着双眼,“你喜欢她,还会娶我?”
“你与她不分大小。“
栾姬又低声一笑,“不分大小?妻便是妻,妾便是妾。“
“此事,容以后再议,我自会对你们一视同仁。“
“我心里只有孙周。”
“若你不愿意,我会为你别寻良人,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你好好想想,孙周对辛夷如此,他日难保也会如此对你。“
栾姬果真陷入沉思,有一想法从脑中急闪而过,片刻,她抬起头,看着他,“你要我如何做?我怎能带出她?”
刑午听她答应,显得高兴而兴奋,又似松了口气,把她搂了搂,“我知你会答应。“
“不,我没有答应你。“
“妍?“
栾姬轻轻推开他,“我不会离开孙周,然,我也不想你有事,正如你说,我曾与她姐妹相称,我会助你。”
“妍!”刑午一阵感动,目光有些湿润,“可是,若被孙周得知,你如何应付?”
栾姬道,“我对孙周有救命之恩,他便欠我恩情,总之,你不用担心,我会处理。“
刑午还有些踌躇,栾姬催促道,“你快告诉我,要如何做?“言毕,又看了看远外,“他们不见我,定会寻来。”
刑午眉头一皱,似是做了最大决定,“宦者令之事,孙周当真以为我走投无路?“言毕,冷哼一声,又道,“后宫里,岂只有宦者令一人。”
“你是说,晋宫还有奸……楚人?”
刑午摇摇头,“他并非楚人,此人身份孙周永远也想不到,与孙周有不共戴天之仇,那日,便是宦者令带我与他联系,被孙周发现。“
栾姬眨眨眼,有些云里雾里。
刑午不愿多说,“你放心,他会安排让你带辛夷出宫。”然后,又从身上取下一物,交到她手里,“你拿给她,她便会跟你走。”
那是一块玉,是刑午贴身之物。
栾姬心口堵得慌,突然有些嫉妒,又道,“他如何做?你可知,晋宫如今守卫森然,辛夷怀有身子,太过明显,便是永巷,她的身边也是不离人,如何逃过眼线?恐她消失半刻,便会立即被发现。“
刑午听言,嘴角露出笑意,缓缓道,“偷梁换柱。”
栾姬不解,刑午又道,“到时你便知道,记住,十日后,巳时,我便在城门第一间酒肆相侯,至于如何出城,我早有计划。”
栾姬还想问清详情,突听有脚步声传来,刑午再次抓着她的双肩,“你当真不和我一起?”
栾姬也是一惊,推着他,“你快走。“
刑午深深看她一眼,“你再想想,十日后,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言毕,很快消失在树林之中。
瞧着他的背影,栾姬紧紧握着那块玉佩,心跳如鼓,矛盾,纠结,但很快,做了决定,目光从来没有过的狠绝。
待栾姬的车马急急出了栾府,大街上,小厮打扮的刑午,看着那马车身影,目光也是一片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