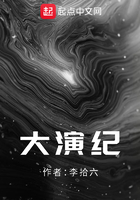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一个梦都没做。醒来后发现她正站在床边对我笑,笑得特别好看。看见我睁开眼,她一下子拿起了刀,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在自己脸上划了两刀,一横一竖,每一刀都划得特别深,皮肉翻卷,血哗哗地流。我夺下刀,她还是在那里笑,笑得特别灿烂,血哗哗地流进嘴里,染红了她的嘴唇,染红了她的下巴,滴滴嗒嗒地落在我的手上。她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间啊,让我欠了这么多……”
“她当天就走了,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我找过她,找了几个月。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找了。我拿那一百万运了几次货,一次香烟,一次汽车总成,一次化妆品,接着去海南买了一张红线图,红线图出手后盖了几栋楼,再以后……”
“我当上了议员,当上了慈善家协会主席,企业家理事会理事长,我到处投资,房地产、金融业、服装、家电、赌场……跟十几个国家的元首吃过饭。也找过很多女人,中国的,外国的,还有黑人。我做那件事情,可就是不能留她们过夜,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行了,那天陪我的是当年的亚姐,就在丽晶酒店的总统套房。把亚姐赶走之后,我做了一个梦,那是十七年来我第一次梦到她,梦里的她还带着那两道伤口,血慢慢地流下来,她对我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间啊。”
“我知道,她肯定是死了。她走之前说过:不死不相见。现在她终于肯来见我了。她就是这么残忍。那天晚上我再也没睡过,一直在想: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她小时候那么好看,现在四十四岁了,四十四岁的她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生过得多么快啊,转眼之间人就老了。十七年来我从没想过她,偶尔回忆起来,我就使劲摇摇头,我有杀人之心,做什么都能做得到,包括忘了她。不过那天夜里,我还是想了她几分钟,从六岁到十一岁,从十三岁到十七岁,再到二十七岁……她一直都那么好看,又是那么残忍。我还记起了她的生日:四月二十四日,很多年以前的这天下过一场雨,我从她的课桌里偷了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在床头放了四年,最后缩水干枯,硬得像个核桃……”
“我又开始找她,在十七年之后。你还记得我送你的那支笔吧?就是在那前一天,我找到了。她那时已经死了十二天,我赶去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没有镜子,没有电视,床下放了一碗粥,已经长满了绿毛,枕头上有四根银白色的头发,原来,她的头都白了。”
“她给我留了一封信,她知道我会来找她。”他看着我,轻轻地眨了眨眼,我终于发现是什么让我如此不安了——从进这间屋子开始,他的眼睛就没有眨过!
他掀开枕巾,下面是一个紫黑色的盒子,方方正正的,隐约有一点树木的清香。他来来回回地摩挲着,忽然笑了起来,“你看,这就是她,”说着抽开盒盖,露出了满满一盒黑粗的砂,他伸手抓了一把,然后手掌平摊,骨灰从指缝中瑟瑟地漏下来,最后只剩下一块一角硬币大小的骨片,他说:“烧得太粗糙了,是不是?这么多硬块。你猜这块是哪个部位的?头?胳膊?腿?”我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把那块骨头放在鼻子下闻着,笑得无限幸福,“我这辈子没什么朋友,只能跟她说说话,我每天枕着她,可是,一次都没梦到过她。唉,操纵这世界多么简单,可梦见一个人,多么难啊。”
报仇雪耻
骨灰盒下压着一封信,他拿起来递给我,那是两张最普通的十六开信纸,纸都发黄了,边角皱折,看得出已经被读过了无数次,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在心里默念:
……
现在我们可以见面了,十七年前订的约会,我知道你不会失约。这十七年来我天天都在诅咒你,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你不欠我什么,而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你打过我一次,我打过你二十几次,还欠你二十几次;我为你留下了两个疤,你为我留下了无数个,还欠你无数个;你跟我的时候没有过女人,我跟你的时候有过四个,还欠你四个;你没打过胎,我打过三次,还欠你三次。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间啊,凭什么这么少,又这么多。你欠我的,只有一个苹果,咬过一口的苹果,核桃一样的苹果……
有时候一闭眼就能看见你,六岁那年,你穿着大人穿旧的中山装,鞋带没系好,拖拖拉拉的,你小时候又丑又脏,你一路跟着我哭,你说:不卖,不卖,不卖,不卖……你是嫌钱太少吧?坏蛋,再过二十年,给你一百万,你就把我卖了。
九岁那年,你当上了三好生,第一次为我打架,就因为别人拉我的辫子,你太矮了,打也打不过,坐在地上一脸是泥。你小时候是个讨厌的鼻涕虫,但你不哭,一次次站起来跟人打,我当时想:坏蛋,打死你才好呢,他们都说我是你老婆,可我从来都不是。
十岁,你肯定不记得了,你把六块橡皮偷偷放进我桌里,我把它摔在地上,红色的小猪跳起来,绿色的小鸡跳起来,你不要脸,不要脸,坏蛋,你小时候总那么不要脸,可那种橡皮已经买不到了,百货商店的售货员说:这是哪辈子的事啊,带香味的橡皮?早就停产了停产了。
十二岁那年,你掉进了水里,我推的,你不喊救命,一个劲儿地瞎扑腾,你快淹死了还会咳嗽,看着真可笑,坏蛋,你小时候总那么可笑。那天被我妈骂了两个小时,她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死了你就得给他偿命。我想:杀死一个坏蛋还得偿命,还讲不讲理。
我一直恨你,连做梦都想杀了你,你不知道吧,也许你知道,你总说我残忍,坏蛋,可你的三棱刮刀至今还在王飚手里,你捅了他十几刀。女伴们都说:女人啊,如果有人肯为你杀人,那你就是天下最幸福的。我是女人,我恨你,你这个杀人犯,可直到头发全白我才明白:原来这一生啊,只有恨你的时候最幸福。
十六岁,你瘦得像根竹竿,你一身是血,被打倒了九次,打倒九次还能站起来,我说得没错,你活该,你以为我会感动,可你知道我有多恨你?我说:我宁可被人轮奸,也不想看你一眼。再过几年,你为我坐牢去了,那个恶棍说要把你弄死在里面,那时候我想:坏蛋,现在不一样了,我宁可被人轮奸,也想再看你一眼。
出狱那年你二十二岁,你说你学会了烫衣服,还会按摩,你带回来两百块钱,给我买了一双鞋,小了一号,夹得脚生疼。你一身伤疤,腿上有两道,腰上有两道,后背是被烟头烫的吧,九个圆圈,我想叫你和尚来着,却怎么也叫不出来,眼泪落在你的背上,我笑起来,说天太热了,这么多汗。坏蛋,你从来不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你总是说:别看了好不好,我怕吓着你。
……
你太瘦了,所以我叫你竹竿;你睡觉时磨牙,所以我叫你耗子;你脑袋是方的,所以我叫你砖头,还有傻子、葫芦、蒜瓣儿……沙沙毛是个少儿不宜的词,你这辈子也不会知道了。可是,我叫过你亲爱的没有?亲爱的坏蛋,亲爱的坏蛋,亲爱的坏蛋,坏蛋,坏蛋,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间呵,凭什么这么少,又这么多,每一天都像这十七年……
……
还没看完,他一把夺了过去,放在手里揉得稀烂。我愣愣地看着,他满面通红,额头青筋暴起,在屋里来回踱了两步,突然一把将我拖了起来,“走!”他咬着牙说,“跟我走!我带你看我是怎么报仇的!”
夜风呼啸,满院落叶纷飞,四只蓝喙天鹅振翅而起,在月光下啪啪地拍击水面,就像飞天的幽灵。那座叫“红灯区”的教堂四门大开,两只价值连城的猫静静踱步,在黑暗中睁着绿莹莹的眼睛。他走到耶稣神像前,耶稣凄凉地微笑,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把耶稣的眼睛直抠了出来。我冷冷地抖了一下,接着灯光大亮,墙上吱嘎作响,一扇门慢慢地显露出来。
我们走进长长的、潮湿的地下巷道,他一言不发,只是脸色越来越青,像是千淬百煅的硬铁。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烤胶皮味,越往前走,这味道就越浓。不知道走了多久,连鞋袜都湿透了,终于来到了一扇门前。他掏出钥匙,哐哐啷啷地开了锁,我探头看了一眼,立刻感觉两腿酥麻,站也站不稳,趔趔趄趄地靠到了门上。
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啊,到处都是火炉,四壁烤得焦黑,一条条的沟纵横交错,沟里流动着血红粘稠的汁液,冒着蒸汽,咕嘟嘟地翻腾着,带着呛人欲呕的臭气。屋子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笼子,边框烧得通红,笼子下的铁池里血水蒸腾,热浪滚滚,离着五米远,我还是感觉皮肤像撕裂了一样地疼。笼子里有一张大铁床,床上坐着一个——天哪,我也不知道那还能不能算是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耳朵,没有鼻子,眼窝里是两团破棉絮一样的皱肉,全身上下乌紫赤红,活像一头剥了皮的猪。一听见声音,这个“人”立刻张开了没有舌头的大嘴,像猪一样尖厉地号叫起来。
“有时候我实在很佩服我的这位老同学,”他尖声笑着说,“他到这里两年了,居然一直没死,你说是不是很神奇?”他拿起一把锋利的铁叉,伸到笼子里戳了戳那堆肉,那堆肉上下乱蹦,嘶声长嚎,一声比一声凄厉,一声比一声瘆人,两只残臂哐哐地砸击着身下的铁床,“你看,他多么活泼,多么有劲,有时候还会哭,哈哈……”我顺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满身淋漓的汗。
他收回铁叉,从屋角的铁架上叉一大块生牛肉,又一次伸了进去,笼里的那堆肉蹦得越发激烈,如果不是隔着铁笼,估计连屋顶都能撞破。他啧啧叹息:“真可惜,他今天不饿,否则你就能欣赏到他表演吃肉了,哈哈,他吃肉的样子简直是精彩绝伦,精彩绝伦!哈哈。”
然后放下铁叉,半跳半走地来到我面前:“我找到他时,他说他想做一个六根清净的人,哈哈,一个多么有理想的人啊,一个……所以我剁掉了他的双手双脚,剜掉了他的眼睛,割掉了他的鼻子、耳朵、舌头,还有下身,哈哈,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哈哈……”我几乎要昏过去了,笼里的那堆肉一直冲着我啊呜啊呜地大叫,叫得我毛发倒竖,他仰天狂笑:“听懂了吗?他让你去报警呢,哈哈,把警察局长叫来吧,哈哈,把法院院长叫来吧,哈哈,把全世界都叫来吧,哈哈,哈哈……”
斯坦威:Steinway,名贵钢琴的典范,一八五三年创始于美国纽约,是肖邦国际钢琴大赛、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的指定用琴,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著名钢琴家的首选用琴。明星中,猫王、约翰·列侬等都是该品牌的忠实顾客。
索斯比拍卖行一九八〇年拍卖过一架斯坦威大钢琴,成交价三十九万美元。约翰·列侬生前用过的一架斯坦威黑檀木竖式钢琴,拍卖估价在九十万至一百一十万英镑之间,合人民币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三百万。在中国大陆的钢琴名店中,一架斯坦威九尺琴售价一百三十五万元,这笔钱可以买普通钢琴一百多架,买组装电脑五百余台,如果买成打折机票,可以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行三千四百次,每天往返一次,可以飞上将近五年。
二〇〇四年春运期间,有个买不到火车票的四川民工流落北京街头,经过民航售票处门口时,他站了很久,然后发誓道:老子这辈子一定要坐一趟飞机,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