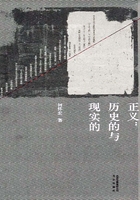你们当然不会希望我在短短的一个钟头里,详尽论述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这一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因此,我限制了自己的任务:我将要谈的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是如何理解原罪或者论述思辨和启示的真理,因为这是同样的问题。不过,应当预先说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连他们对人的堕落的观点和议论,也未必会得到满意的充分阐明,至多只能是概述而且是粗线条的:为什么原罪吸引了这两位十九世纪超群绝伦的思想家的注意力?顺便说一下,通常以为,尼采很少谈论《圣经》;但陷于罪孽的课题是他全部哲学理论的轴心或者枢纽。尼采主要的基本议题是苏格拉底;他认为,苏格拉底是颓废派,也就是说,主要为堕落的人。并且他也认为,苏格拉底的堕落在于历史——尤其是哲学史——总被视为并且开导我们将历史视为他的最伟大功绩:他对理性和为理性所获得的知识具有一种无限信任。当你看到尼采关于苏格拉底的沉思时,你就会经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圣经》关于禁树的传说和引诱者令人神往的话:你将知道善恶。克尔凯郭尔对我们谈论苏格拉底比尼采谈论得更多、更坚决。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异,那就是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苏格拉底是直到所谓“圣书”即《圣经》这部神秘莫测的书出现在欧洲地平线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最卓越出众的人。
陷于罪孽从极为遥远的年代起就开始烦扰人类思维。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尘世间并非一切都尽如人意,甚至极不如意: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来说,“在丹麦王国里有些肮脏”。人们作出了巨大而紧张的努力,以便阐明这种不幸是来自何处。现在就应当说明,希腊哲学正如其他民族的哲学一样(包括远东民族的哲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我们在“创世纪”的叙述里看到的答案截然相反。最早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之一——阿那克西曼德在他身后保存下来的残简中说:“根据必然性,单个生物的生是从哪里来,他们的死也就从那里来。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受到惩罚,并且由于自己的渎神行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报复。”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一思想贯穿了全部古代哲学:单个事物,当然主要是活的生物并且大多是人的降生算作是渎神的敢作敢为,他们的死亡和毁灭就是对此的公正报复。生与死的观念是古代哲学的出发点(我重复一遍,它纠缠不休地在宗教创始人和远东哲学面前萦回)。在各个时代和不同的民族里,人的唯一思想似乎在决定命运的必然性面前着魔而徘徊不前;而必然性给世界带来的是与人的诞生紧密相联的可怕的死亡法则,并力图毁灭已经产生与正在产生的一切法则。在人的存在本身里,思想启开了某种不应当、恶习、疾病、罪孽;与此相应的是,智慧要求根除那种罪孽,也就是弃绝具有开端并注定拥有不可避免的终结的存在。希腊“卡塔西斯”(即净化)的根据是认为,意识和证实生者必死的直接材料给我们启示了亘古永恒、始终不变和永远不可战胜的真理。现实而真正的存在应当不是在我们这儿,也用不着我们去寻找,而是在那生死规律的权力的终结处,也就是在那没有生因而也就没有死的地方。思辨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好像觉得,聪慧的视觉所看到的一切产生和受造的东西必然死亡的规律,永远是存在本身固有的:对于这一点,希腊哲学竞同印度教徒的智慧一样不可动摇地确信不疑,而与古希腊人和印度教徒相距有几千年之久的我们,也同样不能从这种最自明的真理的支配下挣脱出来,好像最初发现和证明了它的人们一样。
在这方面,只有“圣书”才成为神秘莫测的例外。书中讲述的东西与人们用自己聪慧的视觉所发现的东西直接对立。我们在“创世纪”的一开首就看到,一切都是造物主创造的,一切都有开端;然而,这不仅不是存在的残缺性,不足性、缺陷性和罪孽性的条件,而相反,却是宇宙里一切可能的善美的保证。换言之,上帝的创造行为是一切善美的唯一源泉。在创造的每天傍晚,主一边瞧着被创造物,一边说“至善”。在最后的一天,上帝回顾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明白一切都是至善。无论世界还是人类(上帝赐福于他们)都受造于造物主。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完美无缺并且毫无瑕疵: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既不存在恶,也不存在恶之源——罪孽。恶和罪孽是后来出现的。它们来自何处?《圣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一定的答案。上帝在伊甸园里的各种树之间,种植了生命之树和善恶知识之树。他对第一个人说:一切树上的果子都能吃,但是知识之树的果子不能接触,因为一旦你接触它们,你马上就会死去。然而,诱惑者在《圣经》里名为蛇,它比上帝创造的一切动物更狡猾。它说:“不,不会死的,而且会使你们睁开双眼,还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人接受了诱惑,尝了禁果,于是他的眼睛睁开了,并且懂得了善恶。他看到了什么?他又懂得了什么?他看到的正是希腊哲人和印度贤明所看到的:上帝的“至善”不能自圆其说——在被创造的世界里,并非一切都是善;在被创造的世界里,也正因为它是被创造的,不能不存在恶,而且是难以计数的恶和难以忍受的恶。我们周围的一切——意识的直接材料——都以不容争议的明晰性证明了这一点;只要“睁开双眼”,看看世界,只要“知道善恶”,就不会作出相反的判断。从人“知道善恶”的时刻起,罪孽就与“知识”一起进入了世界,而恶是紧随在罪孽之后的。《圣经》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像古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罪孽从何而来?与罪孽联在一起的生活恐惧又是从何而来?存在中有否罪恶?存在作为被创造物,尽管由上帝创造,具有开端,在亘古永恒、不受任何制约的法则支配下,必然为许多不完善之处所困扰,它们将导致存在的灭亡,或导致“知识”、“睁开的双眼”以及“聪慧的视觉”里的罪孽和恶,也就是来自禁树之果的罪和恶。过了数百年,上个世纪集欧洲二十五个世纪思想之大成者、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毫不动摇地深信:蛇没有欺骗人,知识之树的果实是一切未来哲学的源泉。应当立刻说明:黑格尔的说法在历史上是对的。知识之树的果实确实成了哲学之源,一切未来时代的思想之源。不仅是同《圣经》相异的多神教的哲学家,而且承认《圣经》是受上帝启示之书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哲学家,都想要成为知道善恶的人,并且都不赞同弃绝禁树之果。对于(亚力山大的)克雷芒(三世纪初)来说,希腊哲学是第二本《旧约》。他断言说,假若能够把THO3HIc(也就是知识)与永恒的拯救分开的话,假如让他去选择的话,他选择的将不是永恒的拯救,而是THO3Hlc(知识)。全部中世纪哲学就是朝这一方面发展的。在这方面就连神秘主义也不例外。著名的《德意志神学》的佚名作者断言,亚当就是吃了二十个苹果,也不会有任何不幸。罪孽不是从知识之树的果实中而来;因为知识不可能带来任何丑恶的东西。《德意志神学》的作者对知识不可能带来恶的信念从何而来?他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显而易见,他没有想到可以在《圣经》里去寻找真理和发现真理。只应在理性本身中寻求真理,只有理性承认为真理的才是真理。蛇没有欺骗人。
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出生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只是克尔凯郭尔死于四十三岁,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十岁,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开始创作时,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文学活动),并且都生活在黑格尔主宰着欧洲思想界的时代里,当然,也就不能不感受到自己完全处于黑格尔哲学的支配之下。确实应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也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任何一本书——这正与谙熟黑格尔理论的克尔凯郭尔相反——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思想有一种异常的敏感,别林斯基的朋友们从德国带来的东西足以使他对黑格尔哲学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就是“辍学的大学生”别林斯基本人——当然,他在哲学上远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高瞻远瞩——也正确地感受到,并且不只是感受而且还词语恰当地表达了他在黑格尔的学说里不能接受的一切,也就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能接受的一切。援引别林斯基一封著名的信的片断:“假若我能达到梯形发展的顶层——我在那儿也会恳求您对生活和历史条件的一切牺牲,对偶然性、迷信,菲立普二世的严刑拷问等等的一切牺牲作出解释,否则,我会从顶层倒栽葱似地跳下来。我不想要幸运和天才,假若不是心平气和地涉及到我们血缘兄弟中的每一个的话。”……不必说,假如黑格尔有可能来看别林斯基这寥寥数语,那他也只会轻蔑地耸耸肩称别林斯基为野蛮人、野人、不学无术之人。虽然他没有领略知识之树的果实,因此也不会想到存在着确定无疑的法则,它规定了一切,即他狂热辩护的人都有开端,也应当有终结,没有必要要求任何人对生物作解释,它们是有限的,不应当有任何保护和防卫。不仅第一对堕落的偶然牺牲品不应当去保护和防卫;就连像苏格拉底、乔尔丹诺·希鲁诺和许多其他这样伟大、最伟大的人,德行贤明、端正的人,也被历史进程的车轮无情地辗碎了。仿佛他们是无生命物体一样不屑一顾。精神哲学之所以是精神哲学,正因为它善于高居于一切有限和暂时的东西之上。而且相反,一切有限和暂时的东西只有不再操心自己的毫无价值,因而也不值得任何关注的利益时,才参与精神哲学。黑格尔也许会这样说——他也许会借助《哲学史》一章解释道:苏格拉底应该饮鸩而死,这不会有任何灾难:一个老态龙钟的希腊人一命呜呼——值得为这件区区小事大声喧嚷吗?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它只能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哲学家,也就不能以聪慧的视觉去谙识事物之本质。甚至,谁要对此视而不见,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他就无权认为自己是笃信宗教之人。因为一切宗教尤其是绝对宗教——黑格尔就是这样称呼基督教——用圣像给人启示的东西,不比思维的精神自己看到的存在本质更完善。他在《宗教哲学》里说道:“因此。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内容不是由历史,而是由哲学来证明的”(也就是由《圣经》的故事来证明)。这就意味着,只有当思维的精神承认《圣经》与那些它自己发掘到的,或如黑格尔所说,从自己汲取到的真理相吻合时,《圣经》才可能被接受。其他的一切都应当摈弃。我们已经知道,与《圣经》不同,黑格尔的思维的精神从自身中得出蛇没有欺骗人,禁树之果也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知识。同样,思维的精神还摈弃《圣经》里叙述的不可能和奇迹。通过下面的话,可以看出黑格尔多么蔑视《圣经》。他说:“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婚礼上,来宾们得到了多少酒,这完全无关紧要,谁的瘫痪的手痊愈了,也同样纯属偶然:数以百万人的手仍瘫痪着,肢体仍残缺不全,任何人也不能治愈他们。可《旧约》里说,在出埃及时,犹太人门口标上了红色的记号,以便让主的天使识别。这种信仰对精神没有任何意义。伏尔泰最尖刻的讽刺就是针对这种信仰的。他说,上帝没有很好地教会以色列人不朽的灵魂,反而教诲他们怎样去打发自然需求(aller a la s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