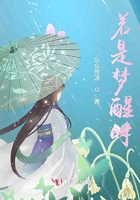落日五湖游,烟波处处愁。
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
鲁班湖,这座人造湖泊,竞使无数英雄望湖心叹,秋日湖水明净,少了夏天碧绿,多了冬天的通透,更透显出秋的宁静和豁达。阳光照在湖面上,奇怪的是惟有在这个季节你才有机会看到一两只嬉戏的小鸭,清脆的叫声回响在秋天透亮的空气里,一旁的青山依旧静静的伫立。
问世间,恩怨情仇为何物?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金秋九月,天地黄灿灿,丰收的日子给这苦难的岁月增加了一份少有的喜悦,微风阵阵,杨柳依依,唱完最后一曲的蝉簇们也渐渐停止了它的颤动。
张无英静静的立在鲁班湖畔,微风轻轻地吹着她长长的发丝,一波又一波的水浪拍打着附有青丝的石岸堤,一条从肩绕过胸前的带子深深地陷入衣服之中,她用右手提了提,沉重的背包在它的身后晃了一下,有几缕发丝卡在里面,干燥得发光。
累了吗?不,这点累算得什么,怎么我这不睁气的眼皮,你在眨几下似似?哎,我的头怎么了,居然嗡嗡地响过不停,肚子,还有这肚子,象一只小鸽子咕咕地叫。
我这鞋子更可怜了,脚丫上大母指早己伸出头在外面望风,几条红色的细丝线在它后面散开,象一堆榨干的枯草,被那风儿吹得忽上忽上。
鸭儿啊鸭儿,你咱这样扑腾飞鸣,难道我这倒映在湖水里鬼魅般的影子让你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
哪是什么?水底龙宫?红色的俏檐,往来愰动游走的灯笼,横梁下几个流金的大字,奇怪怎么是倒的啊?
张无英用两个指尖狠狠刺了一下眼皮,波光闪闪,满湖的碎银在那屋子周围跳动。
不,我不能发晕,难到这是幻觉?
她猛地一抬头,眼前突然一亮。
“曹家大院!”
三十几级的台阶上,那高高耸立,拔地而起的建筑正是曹家大院。
张无英理了理披头的散发,挪了挪那软而无力的腿,在湖边拾起一根粗硬的柳条,支撑着身子,左右在地面的青石板上轻敲了几下,弯着腰向上爬去。
一步,二步,三步……
十步,二十步,三十步……
你说过,我会跪到你门前,你还说过,只要我心诚志坚,你就会答应我的祈求。
我来了,你还好吗?
曹家大院屋外,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就这样跪着,不住地向房内嗑头,细声地呼唤,这声音几乎是哀求,在这闷热的天气里,听了也让人感到一丝寒意。
只见这人虽然穿着朴素,但还是显得相当整洁,那长长的身影倒映在石阶上,腿细细的,娇美嫩白。
“元芳,元芳……”
“我来了,开门啊!开门……”她的声音不时通过门缝向里面传去。
也许这低声哀求的声音能够感天动地,但是乎没有感化屋内那颗冰冷的心。
悠扬而又略带亢奋的歌声在里房响起,还不时传来阵阵欢笑。
一阵风远处吹来,门“吱呀”一声裂开了一条缝隙,一束强烈的夜晚之光从屋里斜射出来。
风中裹着汗味向里屋飘去,那哀求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元芳!元芳!我来了,我来了!开门啊!开门!”
这声音象风又象雾,融入空中很快就消失,没有任何回应!除了那悠扬的歌声外,难道她们没听见?还是……
“是我,是我啊,听到了吗?”
屋内任然没有任何回音,偶尔那淡淡的菜香从那里飘来之外,几乎无任何动静。
风越来越紧,扯动衣服呼啦啦的响,那门缝也愈来愈大,顺着细孔向里望去,张无英眼神不觉为之一震,似乎扑灭的希望又在心里重新燃起。
“汪……”
“唔……汪!唔汪汪……”
一只长长的黑影向她迎面扑来,几颗尖尖的牙齿露在那血盆大口之中,长长的舌头吐着沾液,来势凶猛,象一只饥饿之极的猛兽从躺开的门缝中冲了出来。
不好,出来的不是人!是一只狼狗,一只黑黑的狼狗它吞噬着,嘶咬着……
张无英左右躲闪,本能地用手挡住自己的脸,跪着的上身差点倾倒她不知所措,疲倦的双眼充满了恐惧。
“咔嚓……”
断金碎骨之声,那只咆哮的狼狗咬住了她几根指头,在她周围扑腾跳跃。
血,鲜红的血随掌流淌,还没断根的肉皮成了它的血槽。
屋檐下的一群飞鸽被惊飞,扑愣着翅膀,几欲先走,几乎怕飞慢了逃不掉这活阎王的追杀,甚至有一只鸽子滴落在她头上。
她强忍着痛苦,那大大的眼晴迷成了一条缝,狠狠地的向里屋看着。
那束殷红的鲜血是从右手十指的断裂出冒出来的,渐渐地变成一条线,往下绵延不断地流,可她手依然麻木地向里屋指着。
“你……”
“黑虎……”
张无英的声音好象从地底下冒出一般,显得那样低沉,充满无赖。
尖利的牙齿在灯光的照射下再一次露出来,白光闪闪,阴森恐怖的声音又一次在耳边回响,它象一只野狼,一只失去爱子的野母狼,发出“嗥嗥”长鸣!
一种原始的动物噬血的本能在它体内涌动,可她面临的只是一个微弱的女子,没有同情,没有怜敏,它再一次向她发出了攻击。
“妈妈,妈妈……”飞飞那欢快的声音在她耳伴回荡,可扯动发丝的手并不象她平时那样的温柔。
猛烈,急如闪电,这畜牲的利爪。
“飞飞,是你吗?妈妈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难道这是梦?一场沉睡了千年的梦?
发丝带着少量头皮飘落,那黑犬大而长的身影从她头顶闪过。
黑虎是一个典型的食肉动物,几次扑闪,招招见血,而它面对的却是一个柔弱女子。
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在这里悲剧上演,她几乎失去了任何反抗力,肉体的痛苦和她心灵的创伤相比,这只是沧海的一滴水,她有一种怅然而去的解脱之感。
不,她不能就这样离去,为了她的飞飞,还为了她将来的前途,她在心里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自己。
仅管她的飞飞一无所知。
血浸染了她的脸,衣襟也在漫漫的浸湿,她终于有勇气跪在了这屋前,十多年了,十多年啊!
“黑虎……”一个甜甜的声音从里面飘来,她是乎带有某种狰狞的微笑。
灯光下,一个年轻女人一手摇着扇子,另一手做成凉逢搭在前额上向屋外张望着。
“喂!这不是张二姐吗?你怎么了?”这个看似丫环的女人嘴角挂着微笑,不过她说的那句冰冷的话让她的形象大打折扣:“我们大少奶奶这几天心情不好,她不想见你,还不滚,你这贱货!”
“滚,滚,滚,快滚……”这声音象巨雷一次又一次在她耳旁炸响。
可那黑虎象似对这跪着的妇人情有独钟,它摇了摇尾巴,掉过头,扬起前爪,准备再一次攻击,嘴里的一些长发掉落在地上,那长长的舌头从它嘴边露出来,滴着血,不断地掉落。
“黑虎,不得对客人无礼,闭住你的嘴,污染了这地毯,大少奶奶怪罪下来,让你一阵好饿!”
“呜……”
“呜……呜……”
那叫做黑虎的恶犬是乎心犹不甘,舌头一伸一缩地拌着鬼脸,让人觉得非常恶心和不安。
它摇着尾,摆着头,望着那侍女不停的愰动,长长的舌头吻着那纤纤细手,丝毫没有后悔之感。
“黑虎,你真讨厌!”侍女娇慎地嘟着嘴,头抬得老高,望着天空。
天空繁星点点,偶有几颗胆怯之星眨着睡眼,不忍目视这惨景,悄悄地躲入云层,风吹得疾了,似乎加快了脚步,为她哀鸣和抱不平。
侍女是乎对此情此景早已私空见惯,另一只手掏出沙巾,抚了抚那殷红的血斑,然后捂着鼻。
“活该,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大少奶奶是何等人物,岂能你想见就见的!”
张无英并没有答话,前额那变得稀疏的头发随风吹起,露出那张俊俏的脸,两道弯弯的柳月眉象一缕玉带嵌在两眼之上,眼眶里黑葡萄般的珠子微动,深遂而充满智慧。
“怎么?我说得不对,有种你就滚过那铁钹!我和大少奶奶在西厢房候你!”侍**冷着脸,准备拂袖而去。
张无英弯着腰,跪过那门槛,一张亮愰愰的足有两米长两米宽的异物摆在了去西厢房的路上。
“别走……”张无英沉沉地回答着。
“哼!怕了?”侍女用手指了指那一排排竖有足够五寸长的铁钉说道。
整个这个厢房,活脱脱变成了一个屠杀场。
“你需要的就在那铁钹对面!快过去拿啊!何去何从,你自己决定!”侍女更加得意,那阴冷般的嘲笑充满无尽的邪气!
路灯悄悄地照射着这整个西厢院,嗜血如命的飞蚊嗡嗡地飞绕着她周围,有一两只竞大胆地爬上了那冒血的头皮。
侍女摇了摇那白而带血般的沙巾,仿佛这柔弱的沙巾变成了一只利剑向那铁钹飘去,只一瞬间,那沙巾起了红光,冒起一股白烟,着火燃了起来,空中立即弥漫了一种烧焦的羽毛之气。
热浪不停地从那一排排尖尖的铁钉上冒了出来。
“厢妹,你这火焰铁黎阵比我那黑虎迅猛多了!”先前的侍女甲满含嫉妒地嬉笑。
“哈哈,你这尖牙利齿的狗姐,还不是大少奶奶的智慧!”
随着那一声阴阳怪气的嘲笑声过后,灯光下一身着黑的侍女乙出现在不远处屋檐下,黑色的衣服佩着高挑的身材,与张无英眼前的白衣侍女形成鲜明的对照。
两个黑白无常牢牢地把守着这入门关。
不知这入门关坑害了多少人!
但这种坑害又大多是自愿的!
因为他们都有事求于曹家大少奶奶!
张无英忍着剧痛,勉强站直了身子,那纤细倩丽的身影印照在铁钹上,披头散发,显得异常鬼魅。
只见她缓缓地用随身携带的毛巾擦去脸上的污血,狠狠地咬了咬牙,看着那一根根耸立的尖钉,双脚不免为之一抖。
就这细微的动作,仍然没有躲过侍女乙的眼睛,她很狎意地笑了笑。
侍女甲看着眼前的妇人,心中升起一种无名的敬意。同为女人,为什么这妇人既有如此的精神原动力,她不知道在她背后有什么在支撑她。
“张二姐,你还是何必呢?你回吧!”言语中充满同情,决无半点假意,也许是张无英的恒心和契而不舍的精神感化了她。
张无英没有回答,甚至在她眼里充满不屑。她侧目斜视了她一眼。
天哪!这岂是一个弱妇人之眼,被她一秒杀,兴许三冬的严寒也会变得温暖。
“张二姐,你这样做值吗?”
是的,这样做值吗?这一句直刺心扉的话语让她不寒而立,曾几何时,她反复在揣摩,这在外人看来仅仅为是与非的问题,而对于一个痛苦了几十年的弱女子来说好象自我套上了一条无形的枷锁,让她欲罢不能。
她迟疑地看着那铁钹,又回头望了望那侍女甲,不禁仰天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