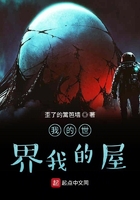宁远城的整个冬日未曾再下雪。燕枝远远望向神岭雪山之上,颜色已由先前的白色积雪变为春日的枯黄。山腰之中有一片蔓延的红色宫殿,便是她日后的公主府。
神岭雪山的北风颇大,加之入冬严寒,故而工部的官吏勘察选址之后,选取了南境最为常见的红棕色砂岩为建造材料。砂岩既不受风雨侵蚀,也不生青苔,且吸潮抗损。
南下的两个月以来,燕枝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便是推窗向外望去,只见胭脂色的石头府邸比前一日又雄壮了许多。即便是百里之外,也看得见落日余晖般的红色。
燕枝也并未闲着,连日来命吴垠于各城之间游走,与诸位官吏探讨兴办学堂之事。她原以为夷人难以管束,哪知筑城城主蒙峰一道令下,强制要求十岁以上贵胄子弟尽数去念书。
学堂开课当日,素来只顾着玩耍和狩猎的小夷人们哭闹着不肯念书。蒙峰便搬了长凳,手持长棍,在门口坐了三天,吓得一堆孩子连哭也不敢哭。
筑城原是南夷国都,读书之风既然兴起,便由南至北,吹便了诸城。
天子减免南境赋税三年,百姓并无苛捐杂税之苦,加之南境冬日漫长,缩在家中也是无所事事,外出读书实乃消遣的好去处。
神岭雪山以北,本是南楚国土,自去年战乱平息以来,也安定了许多。燕枝打算从明年开始,逐年推举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去明城参加春试。今年的春试了是赶不上了,也不知临玉此番参加御试高中了没有。
明城之中已经春暖花开,礼部将本届学子的文章誊抄之后,便呈予太傅和天子过目。今年乃是女子参加御试的第一年,故而试卷之中倒是有些另辟蹊径的文章。
虽然同为学子,但是男子与女子的言论、见解皆不相同。男子渴望建功立业,文字之间锋芒毕露。女子追求平稳,故而文章内敛含蓄。
燕榕与陆景岫读了这样多的试卷,已累得双目昏花,只觉这个也好,那个也不错,偏偏要评选出个一二三名来,当真困难。
天子见二人面露疲惫之色,心道林馥当日一人主管试题、科考、评阅,也未曾累成这般模样。所谓为政之才,还需多多历练。
既是难以抉择,天子便又命内侍传唤丞相入宫。
林馥原本于七八日前便开始在府上待产,哪知过了三日毫无动静,索性又同往常一般上朝。
她登上马车之时,听得葛慧叹息道:“肚子这般大了,怎就没有动静?”
“许是腹中温暖舒适,不肯出来。”林馥说罢却下了马车,道:“此处距离宫门颇近,我走去便可。”
自她升官以来,不论是上朝下朝,皆久坐不动,女医前几日还劝她多走动些。
葛慧觉着也成,便陪着主子沿着御街前行。哪知还没走几步,林馥便开始觉着肚子痛,再走几步之后,连同腰腹至后脚跟都在痛。
她只得扶着葛慧道:“回府,传女医。”
沈通通报庆安王之时,燕榕还在阅览试卷,沈通那一嗓子惊得树上的鸟儿振翅高飞。
“殿下,王妃要生了!”
燕榕愣了半天,只听皇兄道:“今日就到此处,你即刻出宫。”
“殿下快去,我一人在此便好。”陆景岫道。
“陆大人也回去罢。”天子说罢,又命内侍接了皇后与凰儿一同出宫。
燕榕嫌马车太慢,便兀自策马先行。御街之上行人熙熙攘攘,但见一人御马疾驰,也不知这般急切赶往何处。
燕榕记得小皇嫂生产之时颇为痛苦,叫唤了整整一天,丢了小半条命才平安产下凰儿。他忘不了皇兄那一日脸色煞白,双目赤红如饮血的狼狈模样。
而后每每提起生子这件事,皇兄便抱着皇嫂道:“只要凰儿便好,我再也不要阿吾生孩子。”
他每日都同林馥在一处,只有今日御试阅卷,不曾陪伴着她左右……燕榕想到此处,心上愈发急切,也不知往日短短的御街,今日怎么这样长、这样远。
诸位官员原本还在应卯,宫中便突然传来消息,明城官员从明日开始,三日不必上朝。遥想皇后诞下公主之时,天子三日不曾临朝,不知庆安王妃诞生下的究竟是男是女。
岳临江心道景岫还在宫中,便顺路接她回府。谁能知晓她方才还在乾明宫与庆安王一同议论春试录用,突然便听闻王妃要生产了。
岳临江见她这般欣喜,却是将她揽于怀中道:“你南下之时吃了许多苦,我怕你身子受不住,如今可是愿意同我生儿育女了?”
陆景岫只道二人公务繁忙,着实没有时间讨论这般大事,只是低着头道:“我知晓你一直想……我也不曾说过不愿意。”
先前他入了夜倒是努力,可是她白日里繁忙,晚上困乏得厉害,久而久之便教岳临江觉着,她许是对此并不上心。
今日听她这般回答,岳临江只觉马车外的景致也明朗了几分,不由望向僻静小巷的街景。所谓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便是此情此景。
岳临江的住所本就僻静,平日里罕有人至。可今日却有一双男女手牵着手,旁若无人地沿着街巷漫步。
他只道此处安静,方便了这一双年轻的小爱侣,可是待他看清了二人的背影,脸色便阴沉了下来。
陆景岫又岂能分辨不出,那身形挺拔的年轻男子,恰是刑部的杨云帆,与他十指相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今日上午参加御试的岳临玉。二人有说有笑,直至入了杨云帆的府邸……陆景岫觉着,夫君此刻的脸色难看极了。
她连忙牵住他的衣袖道:“杨大人与你我是同僚,临玉也不是孩子,夫君切莫动怒!”
岳临玉刚一进门,不由拍着脑袋道:“哎呀,御试都已结束,我怎么还跟着你来温习功课!”
杨云帆笑道:“御试虽已结束,你日后也可常来。”
“常来做什么?”岳临玉便也笑着看他,“我同你非亲非故。”
“我……”杨云帆一时语塞,他不止一次同她说起过,想对那夜之事负起责任。哪知岳临玉听罢一个劲笑,终于有一回,她良心发现说了实话,才承认那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就是喜欢看他焦躁难安的模样。
这女子当真胡闹!
杨云帆想了想道:“那一夜之事虽是假,这些日子你同我想处却是真。若是你愿意,我将那夜之事落实了也可。”
岳临玉笑道:“你这坏人!”
岳临江在门外站了一会,忽然听到院落中没了声响。他一脚踹开大门,只见二人若惊弓之鸟般各自后退几步。
小妹吓得面色惨白,匆忙低头不敢看他。杨云帆亦是好不到哪里去,只是苍白的嘴唇颇为明媚,竟是多了女子口唇之上的胭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