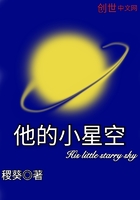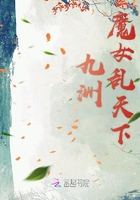林馥上下打量着这位南夷小王子,他的相貌与夷人大相径庭,也不似夷人蒙峰那般浑身杀气、眼神狠厉。他时常目露胆怯,便是有些小心思,也尽数写在脸上。
“既是王子不想说,写下来也可。”林馥循循善诱。
“我……我不会写字。”禾仓抱歉一笑。他的母亲是楚女,可王兄的母亲是乌羽族的美人,乌羽族的后代才有资格读书写字,成为高贵王位的继承人。
林馥见他的模样不像撒谎,却又道:“依王子所说,贵国国师对南夷将帅了若指掌,不知从前是不是南楚京官?”
禾仓不明白她所说,只是问道:“你既是说过要放我走,何时才肯放了我?”
林馥不假思索道:“待攻下筑城。”
“什么!”禾仓当即涨红了脸,“筑城是我南夷国都,你竟要灭我家国,你这恶毒的女人!”说罢竟是十指如钩,蓄力向她抓挠而来。
林馥不知这状如虎豹的拳法从哪里学来,却是站在原地不动,待他笨拙地扑向她,她稍稍倾身,而后一脚猛踹他膝盖后的腿弯。
禾仓“砰”地一声跪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若非你们主动挑起事端,又怎会引得楚军压境?”林馥质问。
禾仓酝酿了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反驳她,只觉得自己堂堂一国王子,被一个女人一招击倒在地,堪称脸面尽失,无颜再见父王。
林馥看出他眼中稍纵即逝的绝望,却是嗤笑道:“南天大王派你来送死,我留你性命,你竟然不知感激?”
“胡说八道!”禾仓争执道。
林馥见禾仓不过是个十七、八的少年,想来不过比沈荆年长几岁而已,觉着他这般面红耳赤的模样既可笑,又可怜。
“宗诏乃是南楚反臣,你与他一道率几千人偷袭阴丘城,不过是在赌运气而已。”林馥道:“还好你赌赢了。”
“这……这都是国师的计谋,国师所言没有一句假话。”禾仓不认为自己全然靠赌。
“何以见得?”林馥问。
“国师可预言天狗食日。”禾仓又道。
“日月轮转,昼夜交替。莫说天狗食日,天狗食月亦不稀罕。”林馥并不觉着这是什么本事。
“国师最擅识人。”禾仓极力维护国师的声誉,“他曾对蒙峰将军说,偷袭宁仓府粮草之时,若遇林馥则退,不退必败。”
林馥饶有兴致地盯着他,“他为何这样说?”
“他说你擅军政又多诡计,蒙峰不及你。”禾仓眨了眨眼。
若非林馥知晓眼前这半大的孩子不会撒谎,当真以为他是在恭维她。她又问:“可还有其他?”
“他还说……辅国将军乃是羊刃格,生来的将军之命。可他命带羊刃,煞气过重,姻缘不顺。”禾仓说罢,但见林馥一脸严肃,不知在想何事。
林馥沉吟一会,却是笑道:“国师是不是擅长看相、识人,合八字、言命理?”
禾仓不由想起,国师在父王面前自荐之时,便替父王的诸位姬妾看过相,而后指着长王兄的母亲道:“这位夫人宽额丰腮,下颌圆润,乃是大贵之相。”
父王听罢哈哈大笑,却是将他揪了出来,“你再看看他。”
彼时禾仓不过十二岁,不明所以地抬头望向那人,但见此人绕他一周,而后道:“这位王子……乃是早夭不寿之相。”
禾仓听罢默默无语,只听父王笑得愈发放肆,“先生真乃神人也!”
禾仓自幼知晓他与兄长们不同,不论是狩猎捕鱼、还是骑马射箭,但凡动作剧烈些,便会觉得胸口疼痛难耐,宛若锥心。乌羽族的巫医说,他心上有个窟窿,缺了心眼的人当然与其他王子不同。
年龄越长,禾仓越想早早死掉,而后转世投胎,和兄长们长得一般健壮、健全。因而此次国师定下了弃阴丘而逃,引楚人入瘴气林的计谋,他便主动请缨,冒死完成偷袭阴丘的任务。
其实他也曾怀疑过国师,他以为自己会死,没想到还能活到现在。他再过半年便满十八岁,也不知能否活到那时。
待到禾仓用了饭,便又被关入了囚车之中。但见不远处的宗诏衣不蔽体地趴在车里,只能勉强饮上几口稀粥。
禾仓心想,若他如宗诏这般在众人面前被扒了衣裤丢尽脸面,他宁愿一死,可他依旧活着。
林馥忙碌了一整天,入了夜又在城内、城外巡查。中了瘴气之毒的军士饮了小柴胡汤之后,症状果真减轻了许多。城中见手青中毒的士卒数以千计,在当地百姓的建议之下饮了许多糖水,勉强缓解了些许。
解毒、休整、布防,南下,待到下次出征恐怕最少半月。依夷人所讲,南夷多山岭密林,许多无人之境瘴气蔓延,士卒若是贸然而入,大都有去无回。然而如今已是入夏时节,只需在每日未时至酉时入林,便可避免瘴气中毒。林馥当即决定闭城半月,每日仅派斥候出城打探虚实。
待到诸事安顿完毕,林馥才想起沈荆一早摔落了半颗牙齿,又因食了见手青虚弱乏力,也不知好些了没有。她刚来到沈荆门外,便见他“哗”的一声推开了门,欢喜地唤了一声“姐姐”,而后直往她怀里扑。
林馥低头捏着他的脸蛋道:“教我瞧瞧你的牙齿。”
原本笑嘻嘻的沈荆立即闭了嘴,紧紧抿着嘴唇惶恐地摇头。
“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可害羞的?”她笑问。
沈荆仰面看了她许久,却是道:“姐姐,你生得真好看。”
林馥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但见他的两排牙齿中间露出一个黑黢黢洞,说话之时甚至能听到“嘘嘘”的风声。
他跟随她的这几个月,身高一点也不曾增长,还是一副又矮又瘦的模样。她不由摸着他的头道:“我未曾照顾好你。”
沈荆却羞赧道:“医者说牙齿虽然断了,却可以寻了颜色相同之物填补。我从前见过镶嵌金牙的,若是我也镶一副,日后是否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
“日后自然无人再敢欺负你。”林馥刮了刮他的鼻子,见他脸色蜡黄,眼底乌黑,连忙早些劝他上床睡觉。
沈荆不肯,非缠着林馥给他讲故事。想起沈氏因她灭族,林馥一时心上伤感,便任由他缩进被子里,抓着她的手恳求道:“姐姐,你再讲个故事给我听。”
林馥困得睁不开眼,却是半伏在榻上道:“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还有不曾告诉我的!”沈荆连忙道:“姐姐有喜欢的男人吗?”
“小孩子不准过问。”她不肯答他。
“可我早已不是孩子。”沈荆对她的敷衍十分不满。
林馥哄着哄着,便见沈荆缩在被子里睡着了。她以右手支着下巴打了个盹,近旁仿佛有一个声音在问,“姐姐喜欢的,究竟是迟琰之还是燕榕?”
林馥骤然从梦中惊醒,但见沈荆早已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