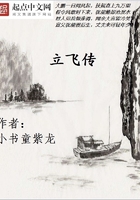房小虎家成了孤岛,地地道道的钉子户。
拆迁现场基本被清理完毕,四周已经砌上了灰墙,把房小虎的两间小平房包围其中,这个据点眼看就要被拔掉了。但房小虎依然高高兴兴地活着,因为他的脚下埋着上百万,为此在梦里不知笑醒过多少回。
浪三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房小虎了,眼前的这个比自己还小一岁的男人,见到浪三时,脸上纵然布满了微笑,但也无法掩盖生活的艰辛。拆迁,让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已经无力再去享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看看房屋四周拉的电线,安装的摄像头,铁门上已经多了好几道锁,还有被利器划过的痕迹。开发商还算仁意,没有断水,也没有断电。房小虎不敢让自己的老婆和儿子住在这里,他下定决心要守住这个发财暴富的最后机会。
晚上的时间最难熬,房屋的四周会出现各种奇怪而恐怖的声音,砖头瓦块也会不定时扔进院子,吓得野猫野狗乱吼乱叫。房小虎也如一只机灵的夜猫子,他不敢脱衣,不敢脱鞋,一把亮铮铮的匕首永远躺在他的枕边,这还不够保险。房小虎在大门后还蔵了一把斧子,院子里的煤堆上还放着一把小铁揪。这些都是以防万一,随手可以抄到的家伙。防小虎除了要与开发商斗声斗勇,还要承受着孤寂带来的威胁。与他一起并肩战斗的钉子户相继覆灭,有的被打伤,有的被胁迫,有的耐不住这种非人的生活,只有房小虎挺到了现在。每到晚上,他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电视机的音量足以传到不远处的小马路上。他坐在院子里,眼睛在月亮、斧子、铁揪之间移来移去,手里的匕首已经被他擦得照见了人影。陪伴他的只有墙头上的野猫和门外来回溜达的野狗。房小虎想找人说话,他会打手机,找自己的姐姐、同学、朋友,通话时总是以“哈哈”大笑开头,以“嘿嘿”傻笑结尾,他的语言功能开始减退,词汇仅能围着“拆迁”这两个字来延伸。
房小虎的卧室里放着父母的遗像,两位老人在这两间小屋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养育了四个孩子,辛苦一生,早早离世。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两间小平房居然成了子女发家致富的手段,两位老人安祥地看着房小虎把家变成了战斗的堡垒,屋里充满了血腥和铜臭。唯一的儿子像一条丧家之犬,蹲守在一片废墟烂瓦之中。小虎可不这么想,这个家里除了父母的像片以外,在他眼里都是钱,大把大把的钱,为了这笔钱,他用青春去赌,用家庭去搏,这种挣钱的方法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太容易了,简直太容易了,这是远在天堂的老人给自己留下的一棵摇钱树。
房小虎好长时间不去照镜子了,他感觉不出自己的变化,在浪三看来,这是一张与实际年龄完全不符的脸,皱纹横七竖八地排列在黑黑的额头上,两眼被深深地挤在眼窝里,鼻头上长了包,还不止一个,就像枪口上的瞄准镜。身体开始臃肿,尽管他每天像卫兵一样巡逻,但不规律的生活严重打击着男人的健康,头顶上的灰白加重了沧桑。
浪三和女人低头走进了房小虎的碉堡,虽然房门并不低,但浪三还是吓意识地低了一下头。迎接浪三的还是房小虎标致性的“哈哈”大笑,哥哥朗天明也在屋里坐着,他的脸上也带着微笑,故作镇静。
“浪三,进来坐,自己倒水喝,我给你做饭去,想吃什么?我这什么都有。”
“别忙了,随便吃点就行了。”浪三说着坐在哥哥的对面,而女人知趣地躲了出去,故意把空间留给了哥俩。
“你没找到地方?”哥哥问。
“我不想再租房子了,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房小虎这来住,行吗?”哥哥试探着问。
“什么?”浪三一愣,他没想到哥哥会出这么一招,“我搬人家来干什么?再说这是什么地方,是…..住的地方吗?”浪三把关键字隐去了,他怕房小虎听见引起误会。
浪三今天没有让步,也无法让步,就算房小虎家不拆迁,他也不可能住在这个地方。这地方还不如地下室呢,连卫生间都没有,更别说洗澡了。
“你先忍一段时间,我再想想办法。”哥哥在做最后的努力,“我上班太远了。”
“你远,你想过我吗?”浪三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外屋的女人吓了一跳。
浪三的嘴像一挺机关枪,把多年压在心里的怨气和不满全部倾倒了出来,声音把这间快要坍塌的小屋震得嗡嗡直响。
女人害怕了,她走进来说:“浪三,有话好好说。”
房小虎拦着女人:“让他说说吧,再不说他该得病了。”
浪三的情绪平复了一些,他一直扭着头,不敢去看哥哥的脸,直到现在,他才正眼去看哥哥。哥哥像雕塑一样坐在那里,没有反驳,也没有任何表情,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来了一个大倒个。以前理直气壮骂人的是哥哥,浪三只能有听的份。哥哥被浪三彻底震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也有压力。”
“我明天搬吧,我把房子给你腾出来。”哥哥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浪三听得很不舒服,他心中的酸楚达到了极点,也开始慢慢理解房小虎的初衷。如果我和房小虎换一个位置,说不定也一样为了最后的安宁去坚守,为了今后不再为房子打架去坚守,为了今后不再亲兄弟反目,为了今后不再妻离子散而坚守,为了今后老有所养而坚守。房子,都是因为房子,浪三想用世上最难听的话去骂房子,操房子他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