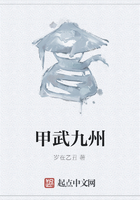深秋,黄昏,天气诡谲多变,远山虽清烟裊绕,漫天霞光却红彤如血。
连日滂沱大雨已然停歇,然道路尽是泥泞坑洞,荆轲一行人更是平添阻挠。
马车已不知陷入坑洞几回,隨行侍从早已一身泥巴,还没喘过气又见车轮深陷泥坑之中。
秦舞阳叹了一口气,正想吆喝大伙使劲拉动马车之际,道旁闪出数个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
为首的老者弯下腰咳嗽着道:「这位小哥——咳~咳~您别费力,各位都歇着,咳,让咱们替各位爷~咳咳~拉起马车,可好?」
另一老妇上前搭腔道:「各位大爷,咱们只求给些吃的——行吗?」
荆轲掀开布帘一看,只见眼前的老者面黄肌瘦,身后的妇婦哆嗦着身子,显是已捱锇多日。
「舞阳,取些干粮分予老人家。」荆轲心情沉重嘱咐后,又取出酒葫芦交予老者道:「老人家,天冷了,留着暖身子吧。」
那老者红着眼眶忙跪下拜谢,身后一众妇孺亦纷纷随着下跪。荆轲忙将老者搀扶起身道:「各位快快起来,都回去吧。」
老者抬起头,双眼茫然哽咽道:「回哪啊?咱家大郎,二郎征战不归,良田荒芜,盗匪猖獗,天下——无家可归呀!」
霎时啼哭四起,众妇孺皆抱成一团痛哭涕流,闻者无不心酸。
荆轲无语仰望苍天,也许狼烟四起的天下,烽火已无情遮蔽了老天双眼,于是无视苍生流离失所,伦常残缺。
目送老者搀扶着老妇与一众妇孺蹒跚离去,荆轲双拳紧握,内心却是一片迷惘。
夜暮低垂,荆轲等人终于抵达驿馆,安顿盥洗后,秦舞阳颇有微言道:「荆大哥,这一路往西去,流民何其多呐,你每回见着便分粮食,这也不是办法呀!」
荆轲看了看秦舞阳,笑道:「舞阳啊,我等少吃一口,少饮一囗並不礙事,可那些都是饥民吶...唉,你就别计较了。」
秦舞阳恨恨道:「这都得怨秦国,嬴政那狗东西挑起的战禍!只要杀了嬴政,天下当可太平!」
荆轲盯着秦舞阳严肃道:「舞阳!不可胡言!谨防隔墙有耳!」
秦舞阳犹自嘟哝几句方住口离去,荆轲搖头苦笑自语:「七国之战禍,又豈是杀了一个嬴政可制止...舞阳啊——你还看不清这天下之大势吗?」
「呵呵,那——荆卿可看清了这天下之大势呐?」窗外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荆轲一愣:「田光先生?!」急忙推开窗戶飞身而出。
淡黄色的月光下,一青衫老者捋须微笑而立,却不是田光还有谁。
荆轲半晌回不过神,田光笑吟吟道:「荆卿勿虑,老夫确实健在。」
「田光先生——您——哈哈!原来先生不过诈死,妙啊!」荆轲瞬间恍然大悟,忍不住大笑不已。
田光反而一愣:「荆卿不怨老夫使计将你牽扯替代?」
荆轲摆手慨然道:「如今看见先生安好,荆轲只有欣慰,怨又从何来?呵呵,一切自有天意安排啊!」
田光欣然笑道:「荆卿乃大度之人呀,此处不宜多言,荆卿且随老夫来。」说罢与荆轲翻身越墻而去。
驿馆不远处,一个黑衣人隐身在墻角,一双凌厉的眼珠盯着二人离去的方向,冷笑道:「哼!太傅大人果然神机妙算,田光这老匹夫还真的诈死。」
黑衣人手一挥:「都随我来!」随即几个起落跃过墻头。
「诺!」暗处数个黑衣人一声回应紧随而去。
离开驿馆半里,月影疏落的小树林内,一间简陋的小茅棚。田光取出一坛酒与荆轲对饮。
田光指了指茅棚道:「老夫特意在此久候荆卿到来,只为劝荆卿就此离去呐。」
荆轲搁下酒碗,恭敬道:「荆轲愿闻其详。」
田光叹息道:「老夫算是明白了,太子丹此人並无大智,且心胸狹隘,而燕王熹昏庸无能,只知苟且度日,环伺其余诸国,不外如是啊。」
「哈哈!天命!天命不过是人定啊!燕国也曾强盛,而天下诸国——谁不曾强盛?今,不是天欲亡燕国,亦不是欲亡韩,赵诸国,皆是自取灭亡呀!」
田光颇有些悲愤怨怼,无限感慨道:「如今的秦国已非昔日蛮夷,这都得归功于卫国商鞅变法图强吶...天下,终归一统,荆卿可曾想过——谁有资格令天下归一?」
荆轲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恐怕谁也没有资格,唯有法矣!」
田光黯然点头道:「是啊——荆卿所言正是老夫所以为,而今,唯有秦国之法不可破,嬴政没了,可法还在,继承之人不过依法而行呀!」
田光正色道:「大丈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当知晓有所为,有所不为!故,老夫劝荆卿不做徒劳之事,不知荆卿以为如何?」
荆轲淡然一笑:「呵呵,当初荆轲为了先生而答应了太子,如今喜见先生无恙,然而樊将军为了荆轲此行而自刎,荆轲实在没有理由辜负了朋友之义啊!」
田光叹息道:「不瞞荆卿,你可知明月之死另有隐情?」
荆轲心头一震,颤声道:「月儿?难道不是自尽而亡?」
田光搖了搖头道:「非也,致命那一剑乃是由背部刺入,可见明月绝非自尽。」
荆轲心口一阵刺痛:「月儿若真是遭人暗算而死,太子丹却无声张缉凶,原因只能是太子丹便是元凶!」荆轲只能如此理解。
田光续道:「老夫当初若不是诈死,恐怕便得真死了,而荆卿入了太子府之后,老夫遣人混入府中,那一夜收殓之时,是以得知此事。」
荆轲强忍由悲生愤之情,连饮三大碗酒道:「多谢先生相告,荆轲明白了。」
田光叹了一口气:「这当中的原委,老夫並不知情,然,由此可见太子丹此人其实並非仁义之辈,荆卿无谓枉自送命啊!」
荆轲心头一凛,暗忖:「月儿並非自刎,樊大哥呢?是否——」
荆轲回想当天秦舞阳前来求教剑法,然而却不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难道——樊大哥之死另有隐情?」
田光见荆轲若有所思,逐劝慰道:「此去咸阳尚有月余路程,荆卿不妨再三思量。」
荆轲端起酒碗敬田光道:「先生之意,荆轲明白了,大丈夫但求无愧于心,就此別过。」
田光见荆轲一脸坦然,不免心生愧疚,喃喃自语道:「无愧于心——唉,老夫若劝不得荆卿作罢,有愧于心呐!」
「先生言重了,荆轲自有打算,请!」说罢仰头一饮而尽。
田光目送荆轲离去,长叹一声:「老夫有负荆卿啊——」
「嘿嘿——既然有负,田光先生理应自刎谢罪才是!」随着一阵阴恻恻的冷笑声,七个黑衣蒙面人已闯入芧棚将田光团团包围。
田光冷静盯着领头的蒙面人道:「老夫若没猜错,阁下可是奉了太子之命?」
那蒙面人阴笑着一剑刺向田光:「上!」一声令下,七剑齐出。
田光一个旋身而起,凌空翻身落在领头人后方,一掌横劈其颈项。那人倏地斜身避过,反手一剑逼退田光。
其余六人一个转身,双足一蹬即直扑而来,田光左闪右避,趁隙窜出芧棚外。
「追!」七道黑影自芧棚急速冲出,瞬间又将田光围困。
「哈哈——左右是死,先生又何必徒劳挣扎!」领头人剑指田光得意狂笑。
田光一声冷笑已右足踏出,虚晃向前忽又向左一个箭步疾冲而去,包围左方那人不料田光声东击西,稍一迟缓已遭田光长袖捲去兵刃。
田光一剑在手,精神为之大振,身子一矮横削那人双足,那人往后一个跟斗避开。
不待田光追击,其余黒衣人已提剑刺向后背,噹啷一声,田光挥剑格开,随即将剑舞动成圈横扫而去。
七人见田光来势汹汹,倒也不硬碰,或退或绕,时而刺出一剑,意在消耗其体力。
田光毕竟已是迟暮之年,而七人乃太子府精挑细选之侍卫,武艺自是不弱,片刻功夫已见田光气喘吁吁。
领头之人见状一声呼喝,七剑齐攻,田光更是叫苦不迭。
田光喑自叹了口气:「不想今日终究难逃一死——」
月色朦胧中,一道人影迅速掩至,黑衣人惊觉回身一剑,那人身子一侧,右手已扣住黑衣人手腕。
黑衣人猝不及防,右手一麻,那人夺过利剑反手斜刺,已然穿心而过。田光趁乱反击,瞬间又刺毙一人。
「荆卿,你来得可真及时呐!」田光惊喜之余一轮急攻逼其余五人。
原来荆轲离去之时心神不宁,走了半里路方才彻底冷静下来,这才发觉佈满泥宁的小道旁留下杂乱的足迹,荆柯深恐田光遭人喑算忙折返芧棚。
领头之人见荆轲去而复返,慌忙挥手喝道:「撤!」
荆轲凌空翻身落在领头人之前,一剑挑开黑布:「是你?」蒙面人正是太子丹之侍卫统领——陈忠!
陈忠此刻只能叫苦连天,他不能伤着为太子丹赴秦国的荆轲,而荆轲明白了真相会否就此返回燕国寻太子丹复仇?
荆轲冷冷直视陈忠:「我只问一次,樊将军真是自刎而死吗!」
陈忠往后连退数步,嗫嚅道:「荆卿——你可别忘了太子是如何厚待予你...」
「明白!」荆轲话音刚落,一剑直取陈忠咽喉,噹的一声,陈忠虎囗宛如裂开,长剑脱手落下。
「上!」陈忠已顾不及荆轲有何打算,更不及细想如何向太子丹复命。
荆轲一腔悲愤贯注于一剑,如风起云涌,似江流水滔,陈忠等人惊骇之下奋力挥剑自保。
田光大喝一声,提剑与荆轲併肩直奔而去,陈忠早已乱了阵脚,连声惨叫响起,剑尖已直抵陈忠咽喉。
陈忠扑通一声跪下凄然道:「荆卿!陈忠不敢奢求你不杀我,然——懇求荆卿念及太子之难,燕国百姓之福祉,务求完成使命!」
陈忠说罢挺胸直撞剑尖:「陈忠——不过尽忠——于主子——」一口鲜血吐出,缓缓倒下而亡。
荆轲愣了好一会,陈忠何罪?不过各为其主,尽忠职守,乱世之中,早已分不清是非黑白。
剑兀自插在陈忠胸口,而荆轲心囗又何尝不是插着一柄无形之剑?
荆轲转身狂笑而去,田光茫然望着消失在迷濛月色下的背影,笑声之中却是无尽的沧桑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