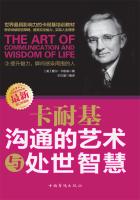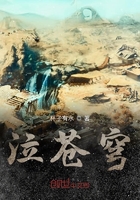生命,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珍惜的。我们之所以那样畏惧死亡,并不是由于生命的终结,而是因为有机体的破灭。因为,实际上有机体就是以身体作为意志的表现,但我们只有在病痛和衰老的灾祸中,才能感觉到这种破灭;反之,对主观而言,死亡仅是脑髓停止活动,意识消失的一刹那而已,随之而来的所有波及有机体诸器官停止活动的情形,其实不过是死后附带的现象。因此说,不管死亡如何令人恐惧,其实它本身并不是灾祸。当生存中或自己的努力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或为不治之症和难以消解的忧愁所烦恼时,大自然就是现成的最后避难所,它早已为我们敞开,让我们回归自然的怀抱中。生存,就像是大自然颁予的“财产委任状”,造化在适当的时机引诱我们从自然的怀抱投向生存状态,但仍随时欢迎我们回去。当然,那也是经过肉体或道德方面的一番战斗之后,才有这种行动。大凡人就是这样轻率而欢天喜地的来到这烦恼多、乐趣少的生存中,然后,又拼命挣扎着想回到原来的场所。
无可否认,生死的决定应是最令人紧张、关心、恐惧的一场豪赌,因为在我们眼中看来,它关乎一切的一切。但永远坦率正直,绝不虚伪的自然,以及“圣婆伽梵歌”中的毗瑟驽,却向我们表示:个体的生死根本无足轻重,不管动物或人类,它只把他们的生命委之于极锁细的偶然,毫无介入之意。——看罢,只要我们的脚步在无意识中稍不留意,就可决定昆虫的生死;自然之对待人类与动物相同,在人类身上,个人的生死对于自然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我们本身亦等于自然。仔细想想,我们真应该同意自然的话,同样不必以生死为念。
诚然,人类由“生殖”凭空而来,基于此义,“死亡”也不妨说是归于乌有。但若能真正体会这种“虚无”,也算颇饶兴味了。因为这种经验性的“无”,绝不是绝对性的“无”。换句话说,只须具备一般的洞察力,便足可理解:“这种‘无’不论在任何意义下,都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或者,只从经验也可看出,那是双亲的所有性质再出于子女身上,也就是击败了死亡”。
尽管永无休止的时间洪流攫夺了它的全部内容。存在于现实的却始终是确定不动而永远相同的东西,就此而言,我们倘若能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生命的直接进行,将可很清楚地看出:在所谓时间的车轮中心,有个“永远的现在。”——若是有人能同天地同寿,他便能观察到人类的全盘经过,他将看到,出生和死亡只是一种不间断的摆动,两者轮流交替,而不是陆续从“无”产生新个体,然后归之于“无”。种族永远是实在的东西,它正如我们眼中所看到的火花在轮中的迅速旋转,弹簧在三角形中的迅速摆动一般,出生和死亡只是它的摆动而已。
佛陀常言:“解开心灵之结,则一切疑惑俱除,其“业”亦失。死亡是从褊狭的个体性解脱出来的瞬间,而使真正根源性的自由得以再度显现。基于此文义,这一瞬间也许可以视之为“回复原状”。很多死者之颜面呈现安详、平和之态,其故或即在此,看破此中玄机的人更可欣然、自发地迎接死亡,舍弃或否定求生意志。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肉身只是一具皮囊而已,在他们眼中看来,我们的生存即是“空”。佛教信仰将此境界称之为“涅”,或称“寂灭”。
超越生命
按语:
生命只是一种存在,而死亡也仅是一种非存在,这两者对人来说无关紧要,因而也无需惧怕死亡。
在生活中,倘使有人问你有关死后继续存在的问题,而问你问题的这个人又属于那种希望知道一切事物却不学习任何东西的人,那么,最适当而又正确的回答便是:“在你死后,你将是自己未出生时的东西。”为何要这样回答呢?因为这个答案含有以下几种意思:倘使你要求一种存在,有起始而没有终结的话,那是荒谬而不合理的;此外,还含有一种暗示,即世界上可能有两种存在,相应的也有两种空无和它对应。不过,你也可以这样回答:“不管你死后成为什么——即使化为虚无——也会像现在个人有机体的情形一样的自然而恰当。于是,你最担心的是转变的时刻。的确,如果我们对这一个问题加以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存在,宁可不存在。因此,我们不再存在的这个观念,不再存在于其中某一时间的观念,从合理的观点看来,就像所谓从未出生这个观念一样,对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困扰。现在,由于这存在本质上是个人的存在,因此,人格的终结不能视为损失。”
生命因意志而在
按语:
意志是物自体,是内在内容,是世界的本质。生命,可见的世界现象,只是意志的反映。所以,生命因意志而起,如影随形一样地与意志分不开;如果意志存在,生命、世界便也存在。
表象世界完全是意志的反映,在表象世界中,意志的自觉一步一步地趋向明显和完整,其最高阶段则是人类,不过,人类的本性只有透过一套相互关联的行动才能获得彻底的表现。理性可以使这些行动达到自觉的境地,可使人类不断以抽象方式纵观全体。
从意志本身来看,意志是不自觉的,只是一种不断的盲目冲动,正如我们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中所看到的一样,此种盲目冲动的意志,透过表象世界的附加物而获得有关本身意欲活动及其所意欲者的知识。这就是表象世界,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说现象世界是意志的反映,是意志的客观表现。由于意志所意欲的往往是生活,而生活又不是别的,只是那意欲观念的表现,所以,如果我们不说“意志”而说“生活意志”的话,那是多余的赘言。
意志是物自体,是内在内容,是世界的本质。生命,可见的世界现象,只是意志的反映。所以,生命因意志而起,如影随形一样地与意志分不开;如果意志存在,生命,世界便也存在。所以,生命就是确保生活意志,只要我们充满着生活意志,就不必恐惧自己的生存,即使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生命,我们将发现,意志,一切现象中的物自体,知觉这些现象的认知主体等,根本不受生死的影响。生死只属于意志的现象,因此,也只属于生命;意志现象定表现于生生灭灭的个体上,当作时间形成中出现的无常现象——此种现象背后的东西,本身根本不知道时间的存在,但须以我们所说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便使它的特性客观化。生死皆属于生命,是两个彼此相互平稳的现象,也可说,生死是生命现象的两极。
我们要特别认清,意志现象的形式,生命或实在的形式,只是存在于现在,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后者只存在于概念中,如果遵循充足理由原则的话,只存在于知识的关联中。没有人曾生活于过去,也没有人会生活于未来;“现在”是生命的惟一形式,也是永远不可能从生命中拿走的可靠财富。“现在”永远和它的内容同时存在,两者永远固定而不动摇,好像瀑布上空的虹一样。因为,生命固定于意志之中,而现在则固定于生命之中。“现在”是意志现象的根本形式,“现在”和意志是无法分开的。只有“现在”是永远存在的和永远固定的。从经验上看,把一切短暂事物中最短暂的事物看成惟一持久的东西,其内容的根源和支持者是生活意志或物自体——人类本身就是生活意志。凡是不断变化和消灭的事物,凡是过去或现在存在的事物,由此种种产生生灭现象形式的缘故,都属于现象界。因此,我们应该想:过去是什么?是现在的玩意儿,将来是什么?是过去那玩意儿。对意志来说,生命是确定的,对生命来说,“现在”是确定的。每个人都不可以说,“最后,我是‘现在’的主人,它会像我的影子一样永远随着我,所以,它从那里来,为什么正是现在,对于这些,我并不感到惊奇。”我们可拿时间和不断旋转的球面相比:永远下沉的一半代表过去,而永远上升的一半则代表未来,但切线所接触的顶端不可分的点则代表没有广度的现在。切线不随球面旋转,“现在”也是如此,客体和主体相接之点,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属于可知现象,而是一切可知现象的条件。或者说,时间像永不止息的河流,而“现在”则是河水流过的石块,但河水没有把石块卷走。作为物自体的意志,和知识主体同样不受充足理由原则的支配,从某方面看,知识主体最后就是意志本身或意志的表现。对意志来说,生命是确定的,生命的现象是确定的,同样,“现在”也是如此,这真实生命的惟一形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无须探讨出生之前的过去,也无须探讨死亡之后的未来;我们要认识现在,要认识这表现意志的形式。现在不会摆开意志,意志也不会摆开现在。所以,倘若生命真能令人满足,那么,凡是以各种方式肯定生命的人,都可以认为生命是无限的,除去对死亡的恐惧,把死亡当作幻象,原来幻象使他变得愚笨地畏惧那可能永远剥夺他的现在而预示没有现在的时间;这是时间方面的幻象,与空间方面的幻象相似,由于空间的幻象,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地球上所占的位置在上,而其他所有地点则在下。同样,每个人都把现在和自己的个体性连在一起,以为整个现在完全在此,以为过去和未来是没有“现在”的。但是,正如地球表面每一个地方都是连上的一样,整个生命的形式也都是现在,因死亡夺去我们的现在而恐惧死亡,正如恐惧自己可能从地球表面滑倒一样的愚笨。“现在”是意志客观化最重要的形式。“现在”把时间分割,从两个方面向无限地延伸,好像数学上的点一样,并且固定不动。像没有凄冷夜晚而永远日正当中一样,太阳好像要沉入黑夜的怀抱,实际上它是在不断地燃烧。因此,倘若一个人惧怕死亡,以为死亡是自己末日的话,他便会背负着生命的重压,他无法从死亡中期求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