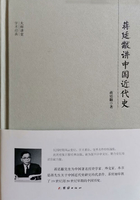七公公象失了魂,走进了云里雾里似的,心里简直没有了一点把握了。他想不到他经年渴慕着的满地黄金的上海,竟会这样地难于生活。梦儿全破碎了。要是年轻,他还可以帮着儿子想方法赚钱。或者是出卖他自己的气力;现在是老了,一切都力不从心了,眼巴巴地只能依靠着儿子来养活他。况且,这一次到上海来,又是他自己出的主意。
大家都沉默着。福生补好了顶上的漏洞处,也走进来了,他瞧了瞧六根爷爷,又把爹望了一望,焦急地,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
停了一会儿,六根爷爷才开口说:“福生!光急也是没得用的啊,明早我替你找找小五子看看,要是他能够替你找到一担菜箩的话,我再带你去设法赊几斤小菜来卖卖,也是好的。七公公你也不必着急,只要福生卖小菜能够赚到一点钱,你也好去学着贩贩香瓜子。大嫂子没事过桥去寻着巡捕老爷,学生子,补补衣袜,一天几十个铜板也是好捞的!”
“那么谢谢六根爷爷!”七公公说,“明天就请你老带福生去找找小五子看!”
福生仍旧没有作声。他把六根爷爷送走之后,便横身倒在中舱里,瞪着眼珠子,望着篷子顶上那个刚刚补好的漏洞处出神:“爹爹太老了!孩子们太小了!吃的穿的……自己又找不到地方出卖气力!”
一会儿,七公公又夹着叹了一声气:“要是明朝找不到小五子,借不到菜箩,乖乖!不得了啊!”
福生的力气大,挑得多,而且又跑得快,他每天卖小菜,竟能卖到三四千钱,除去血本,足足有一千钱好落,七公公便乐起来了。
他自己又用稻草编好了一个小篮儿。他告诉着福生,只要能够替他积上三百四百文钱,他可以独自儿去贩卖香瓜子,赚些钱儿来帮帮家用。只要天气不下雪,他的身体总还可以支持的。
福生没有什么异议。四五天之后,七公公便做起香瓜子生意来了。福生嫂原来也是非常能干的,每天招呼过丈夫和公公出去之后,便独自儿把船头船尾用篷子罩起来,带着四喜子,小玲儿,跑过打浦桥的北面,找着了些安南巡捕老爷,穷学生子,便替他们补补鞋袜,或者是破旧的衣裳。
这样的一家的五口生活,便非常轻便地维持下来了,七公公是如何地安了心啊!
每天早晨,当太阳还没有露面的时候,七公公就跟着儿子爬了起来,提着满篮了香瓜子,欢天喜地的,向着人烟比较稠密的马路跑去。
“谁说的上海没有生路呢?”他骄傲地想,“一个人,只要安本份,无论跑到什么地方都是有办法的啊。这就是天,天啊!”
七公公的勇气,便一天比一天大将起来。他再也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饿死人的地方了。他每天从大的马路穿到小的弄堂,又由小的弄堂穿到大的马路。只要可以避着巡捕的眼睛的地方,便快乐地,高声地叫着“卖香瓜子!”装着鬼验儿逗引着孩子似的欢笑,永远地象一尊和蔼的神抵似的。一直到瓜子卖完,夕阳西下,寒风削痛了他的肤骨,才象一匹老牛似地拖着两条疲倦的腿子,带着几颗给孩子们吃的橘子糖,跑将回来。同儿媳孙子们吃着粗糙的晚饭以后,一睡,便什么都不去想它了。
天气毕竟是加上了几重寒气,听说是快要到洋鬼子过年的日子了。小菜和香瓜子的生意都渐渐地紧张起来。福生和七公公也更加地小心着,小心那些贪婪的象毒蛇一般的巡捕和警察们的凶恶的眼睛。
“早些回啊!福生。”
“早些回啊!爹!”
互相地关照着。这一天,象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的压力,紧紧地压迫着父子们的心。在桥边,儿子福生又特别在站着,多瞧了那老迈的爹爹的背影一眼,一直看到那个拐过了一个弯,不再看见了,他才放开着大步,朝高昌庙铁路边的菜园跑去。
也许是因为过于耽心了吧,七公公刚刚才转过一个弯,心儿便跳起来了。手中的草篮子轻轻地抖战着,香瓜子统统斜倾在一边。他用着仓猝的眼光,向马路的四围不住地打望着:可没有看见什么,大半的店门,都还紧紧地关闭着没有开开呢。
自家把心儿镇静了一下。于是,便开始向大小的弄堂里穿钻起来,口里喊着:“香瓜子啊!”
最初的主顾,照例是上学去的孩子们。用着白嫩的小手夹着一个铜元轻轻地向草篮中一放,便在七公公的一个鬼脸儿之下,捧着百十粒香瓜子儿笑嘻嘻地走开了。接着便是讨厌的,争多争少,罗罗苏苏的娘姨和老太婆们!
工厂的汽笛告诉着人们已经到了午餐的时候。七公公便悄悄地从弄堂里钻出来,急忙穿过了一条大的马路,准备着回家去吃午饭,可是,猛不提防在马路的三岔口边,突然地发出一声:“跑来!卖香瓜子的老头子!”
七公公一看,一个荷着枪的安南巡捕,迎面地向他走了过来,他吓得掉转头来就跑。
“哪里去?猪猡!”
安南巡捕连忙赶了上来,用三只指头把七公公的衣领子轻轻地抓住着向后面一拖!
“猪猡依的香瓜子阿是弗卖?娘个操屄!娘个操屄!”
“卖,卖的!”七公公的腿子不住地发抖。
于是,那个安南巡捕便毫不客气地抓去了一大把香瓜子。接着,又跑拢来了四五个:“来呀!吃香瓜子呀!”
一会儿香瓜子去了一大半!七公公挨在地下跪着不肯爬起来,口里便尽量地哀求着:“老爷!钱!做做好事啊!”
“钱?猪猡!”安南巡捕用力的一脚,恰好踢在七公公的草篮子上。
篮子飞起一丈多高!香瓜子,铜板……接着又是一阵扫地的旋风!
“天哪!”七公公伤心地大哭着。他爬起来到处找寻着他的草篮子!草篮子抵剩了一个边儿;香瓜子?香瓜子倒下来全给大风吹散了;铜板?铜板满马路滚的不知去向!
七公公象发疯了似的。他瞧着那几个凶恶的安南巡捕的背影,他恨不得也跑上去踢他几脚,出出气!要不是他们荷着有一支枪的话。
还有什么办法呢?祗好痛苦地拾起马路上的零碎的铜板,提着半个草篮儿,走一步咬一下牙门地骂几句;象一匹带了重伤的野狗似的,踉跄地走回到自己的船屋子里来。七公公的心儿,差不多快要痛得裂开了。
儿子还没有回来,他一面吃饭一面流泪的向媳妇诉述着他这一次被劫的经过。媳妇垂头叹着气,说着一些宽慰的活儿,小玲儿和四喜子便围着他亲热地呼叫起来;可是,这一回,公公的怀中,再也没有橘子糖拿出来了。
午饭过后,太阳眼看得又偏了西了,福生还没有看见回来,七公公可真有点儿急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入他妈妈的!”
媳妇又带着两个孙儿走过桥去寻活去了。七公公独自儿坐在船屋子里,焦急地等待着儿子回来诉述他心中的苦痛。用着气愤的羡慕的眼光,凝视着对面的高大的洋房和汽车的飞驶;仰望着天上惨白的浮云,低叹着自家六七十年来的悲伤的命运!
“入他妈妈的,还不回来!”
非常不耐烦地低声地骂了一句。忽然,老远地有一个警察向这里跑来了。七公公吃了一惊!
“你的儿子呢?”
“七公公定神地一看,马上就认识了:这是上一次打儿子的耳光,要码头费的那个人。他连忙陪笑地说:“先生!早上出去的,还没有回来。”
“你们为什么把船架在此地呢?上一回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了吗?妈妈个入肉的!”
“是!是!先生……”
“马上撤开!”警察顺手用捧棍一击,拍的一声,船篷子上立刻穿了一个碗大的窟窿!“还有,那个坪上的一堆草,也得赶快弄去!上面有过命令的,这是叫做“妨害卫生,有得(碍)观胆(瞻)”!”
“是!是!”七公公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去告诉你的儿子吧!要是明朝还没有撤去,哼!妈妈个入肉的!”
警察先生耀武扬威地走了上去,回头还丢下一个凶恶的狡狠的眼光来!
七公公的心儿乱得一塌糊涂了,象卡着有一件什么东西急待吐出来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儿子还不回来,天色巴巴地快要黑下来了。
媳妇孙子们都回来了,马路上早已经燃上了路灯。胡乱地弄吃了一点东西之后,公媳们便都把心儿吊了起来,静静地等候着儿子、丈夫的消息。
“天哪!保佑保佑我的儿子吧!他再不能象我今天早晨一样呀!”
一夜的光阴,在严厉的恐怖中度过。
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儿子福生才赤手空拳,气愤得咬牙切齿地跑回来,一屁股坐在船头上,半晌还说不出来一句话。
“怎,怎么回来吗?”七公公战战兢兢地问。
“入,入他妈妈的!”福生忍气地说:“没得照会,昨天晚上在公安局关了一夜!
“菜箩呢?钱呢?”
“……”福生的眼睛瞪得酒杯那么大,摇摇头,没有作声。
“天哪!我们都活不成了哪!”
一家人都焦急着。晚上,那个讨码头钱的警察又跑了来,福生气愤的祗和他斗了几句嘴,便又吃了他几个耳光。结果,钱没有给逼出一文来,警察先生也知道没有了办法,才恼怒地跑到那块空坪上,轻轻地擦着一根火柴,把福生的草堆子燃烧了。
等福生知道了急忙赶上去扑救的时候,已经迟了,祗剩得一堆火灰了。
七公公便更加伤心地哭叫起来:“天哪!同强盗一样哪!我们活不成了哪!”
四
儿子没有本钱再卖小菜了;自家的香瓜子卖不成了;仅仅祗有媳妇过桥去补补破衣破袜,一家人的生活,便立刻感到艰难起来了。
福生整天地躲在船舱里面发脾气。他象着了疯似的。一天到晚,骂骂这个,又骂骂那个;从故乡的灭绝了天良的田主起,一直骂到打他耳光,关禁他,放火烧他的草堆子的丧天良的警察为止。骂得不耐烦了就把眼睛睁得酒杯那样大,仰卧在船头上,牢牢地钉住那惨白的天空,象在深深地想着一桩什么事件一样。有时候,还紧紧地捏住他那粗大的拳头,向空中乱击乱舞;或者是寻着犯了过错的孩子们捶打一顿!这样,一天,两天……他那一颗中年人的创痛的心儿,便更加迅速地变化得令人不可捉摸了。
七公公焦急得时时刻刻想哭。尤其是看不惯福生的那种失神失态的样子,真正是使他心烦,连一点儿忍耐性也没有。他几回都想开口责骂福生几句,可是,一想到这家伙平日拼死拼活地为生活挣扎的神气,心儿便不知不觉地软了下来。
“多可怜啊!他,他……天老爷为什么没有眼睛呢?”
习惯地一想到天老爷有眼睛,七公公的心儿便马上壮了许多。无论怎么样,他想,好人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到了要紧关头就会有贵人来扶助。譬如说:就拿这次到上海来的事情来讲吧,一到岸,没有办法,就找到了六根爷爷!
于是,七公公便比较地安心些了。他从从容容地跑到茶棚子里去找六根爷爷,六根爷爷表示没有办法,他不急;又跑去找小五子,小五子对他摇了摇头,他不急!不到要紧关头,是决没有贵人肯来扶助的,他想。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起来,除了整天地吃不到饱饭以外,每个人身上的破衣破服,都已经着实地感到单薄起来了。这,特别是七公公和那个稚幼的孩子,孩子们冷起来便往破被里面钻,特别是小玲儿,他差不多连小小的脑袋儿都盖了起来。七公公终天地坐在船舱中发抖,骨子里象有一把冰冷的小刀子在那里一阵阵地刮削他的筋肉。媳妇的生意,虽然比平常好了许多了,但是,天冷,手僵,一天拼命也做不了多少钱,生活,仍旧是毫无办法的哟!
“贵人为什么还不来呢?现在是时候了呀!”于是,七公公又渐渐地开始着起急来。他又跑去找六根爷爷,又跑去找小五子,六根爷爷和小五子仍旧没有替他想到办法。
孩子们,最初是闹着,叫着,要吃;随后,便躺在舱板上抱着干瘪的肚皮哇啦哇啦地哭起来。福生仍旧是一样的倔强,发脾气,寻着过错儿打孩子。福生嫂拼命地赶着做着生活!
“天啊!难道真的要饿死我们吗?”七公公这在挨不下去了,身上,肚皮……终于,他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明天,要是仍旧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就决定带着两个孙子,跑到热闹的马路边去讨铜板去。
单为了冬防的紧急,穷人的行动,便一天甚似一天地被拘束起来;尤其是沿日晖港一直到徐家汇一带的贫民窟,一到夜晚十时左右,就差不多不准行人往来了。
老北风,一连刮了三个整日。就在这刮北风的第三天的下午,天上忽然布满了灰黑色的寒云,象一块硕大无比的铝铁。当那寒云一层层地不住地加厚的时候,差不多把整个贫民窟的人们的心儿,都吊起来了。
“天哪!大风大雪,这儿实在来不得哪!”
入夜,暴风雪吹着唿哨似地加紧地狂叫着!随即,便是倾盆大雨夹着豆大的雪花。
“天哪!”人们都发出了苦痛不堪的哀叫。
突然:……一阵巨大的旋涡风,把一大半数贫民窟的草棚和船屋子的篷盖,统统都刮得无影无踪了!船屋子里面的人们,便都毫无抵抗地在暴雨和雪花中颠扑!
“不得了呀!福生快来呀!”七公公拼命地扭住着一片被暴风揭断了的船篷子,在大雨和泥泞中滚着,打着磨旋。福生连忙跑过来将他扶住了!
三四片船篷子都飞起来了,雨雪统统扑进了舱中!孩子,福生嫂,一个个都象落汤鸡似的,简直没有地方可以站得住脚;渐渐地都倒将下来了,满身尽沾着泥泞,腿子不住地发抖,牙门磕得可可地叫!
福生又连忙跑过来将他们扶起,拼命地把四五片吹断了的篷子塞在船舱中,用一根棕绳扎好。然后,扶着父亲、老婆,背着小玲儿和四喜子,跑到了马路上来。
两个小东西的脸色都变成了死灰,七公公已经冻得不能开口了,福生急急地想把他们护过桥去,送到一个什么弄堂里去暂时地躲一躲。可是,刚刚才跑到桥口上,就看见了一群同样的被难的人们,挤在大风雨中,和警察巡捕在那里争论着:“为什么不许我们到租界上去躲一躲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