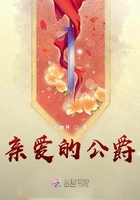话说红姑同了那婆子,历尽艰难,到得中央那座高楼上,正站在一间屋子的门前,侧耳倾听着,只闻得那哭道人和一个妇人在屋内吵着嘴。一会儿,忽闻到那妇人要冲出屋子来。这一来,倒把他们二人大大的骇上了一跳。因为这妇人一冲出屋子来,逆料这恶道也要追出来的,这不是糟糕么?不过,二人的心思也各有各的不同。在红姑呢,只想悄悄的就把继志盗了回来,不必惊动得这个恶道。在那婆子呢,也只想把这里的机关探听得一个明白,并不想和这恶道动得手。如今这恶道倘然一追了出来,当然要把他们发见,不免把他们预定的计划全行打破,你就是不愿惊动他,不愿和他动得手,也是不可得的了。但是“人急智生”这句话,真是不错的。就在这十分吃紧的当儿,他们忽瞥见离开这房门口不远,有一个凹了进去的暗陬,很可躲藏得几个人,便各人受了本能的驱使,肘与肘互触了一下,即不待屋中人冲出来,相率向这暗陬中奔了去。谁知这一下,可大大的上了当了。也不知是否那恶道所弄的一种狡狯,故意布成了这种疑兵,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向这暗陬中奔了去的。当下,只闻得豁啷啷的一阵响,他们所置足的那块地板,立刻活动起来,他们的身子,即如弓箭离弦一般的快,向着下面直坠,看去是要把他们坠向千丈深坑中去的了。幸而他们都是练过不少年的工夫的,早运起一股罡气,以保护着身体,免得着地时跌伤了筋骨。好容易方似停止了下坠之势,又像在下面什么地方碰击了一下,起了一个很剧烈的反震,便把他们翻落在地了。照理讲,他们早已有上一个预防,运起罡气保护着身体,这一跌不见得就会把他们弄成怎么一个样子。但是,很使他们觉得难堪的,他们并不是跌在什么平地上,却好像是跌落在一个水池之中,而且有一股秽恶之气和血腥之气,向着鼻孔内直钻。于是他们二人都大吃一惊的想到:我们莫不是跌落在水牢之中了?同时,却又闻得一种声浪,从很高很高的地方传了下来,这是红姑一属耳就能辨别出来的,作这声浪的主人翁,除了那个恶道,还有什么人。细聆之下,他挟了十分高亢的音调,在上面很得意的说道:“你们二个妇人好大胆,竟敢闯进我这龙潭虎穴中来了。如今怎样,不是只须我略施小计,就把你们弄成来得去不得了么。现在我也别无所敬,只好委屈你们在这里喝上几口血水罢。”
说完这活,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此后即不闻得什么声音,大概这恶道已是去了,他们一闻到恶道说上喝血水这句话,更觉得有一股不可耐受的血腥气,向着四面包围了来。这在那婆子还没有什么,红姑是修道的人,当然不欢迎这一类的东西,教他那得不把眉峰紧蹙起来呢。然四围也是黑魆魆的,他们虽能在黑暗中辨物,却不能把四周围看得十分清晰。于是促动红姑,想起他身上所带的那件宝贝来了。只一伸手间,早已把那件宝贝取了出来,却是一颗夜明珠。
这是他有一次到海底去玩,无意中拾了来的。拿在手中时,真是奇光四彻,无远勿届,比灯台还要来得明,比火把还要照得远。同时,也把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瞧看得一个清清楚楚了。原来这那里是什么水池,也不是什么水牢,简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血污池。在池中浮动着的,全是一派污秽不堪,带着赭色的血水,而且有一种小生物在这血水中蠕动着,却是一种血蛆,繁殖至于不可思议,数都数不清楚。那婆子见红姑把夜明珠取出来,颇露着一种惊讶的神气。比见到这血水中的许多血蛆,又早已叫起来道:“啊呀,这是些什么东西?适才我见了那些庞大的鳄鱼,倒一点也不惧怕,很有勇气的和他们厮战着,如今却一些儿勇气也鼓不起来,只觉得全身毛竦呢。”
说时,身上早已爬满了这些蛆,有几条向上缘着,竟要爬到他的颈项上、脸部上去了。引得他只好用两手去乱掸。红姑也笑道:“不错,越是这些小小的丑物,越是不易对付得,倒是适才的那些鳄鱼,有方法可以制伏他们。你瞧,这些蠕蠕而动的血蛆,难道可以用剑来斫么?就是用剑斫,也斫不了许许多呀,如今第一步的办法,最好把这一池血水退他个尽,只要池水一退尽,这血蛆就无存在的余地了。”
他边说边又从身上取出一个小葫芦来,而把手中的那颗夜明珠,递与那婆子执着。说道:“你且替我执着了这东西,让我作起法来。”
这时红姑虽不知婆子是什么人,那婆子却早已知道他是红姑了。心想,红姑在昆仑派中,果然算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上了不得的本领,但瞧这葫芦,只有这一些些的大,只有什么用处?难道说他能把这一池子的血水,都装入这小小的葫芦中去么?当下,露着很为疑惑的样子,并喃喃的说道:“这葫芦未免太小了一点罢?你瞧,只要把一掬的水放进去,就会满溢了出来的。”
红姑也懂得他的意思,但仍微笑不语。随即把这葫芦子放在血水中,听那流动着的血水,从这葫芦口中冲进去。说也奇怪,看这葫芦的容积虽是很小很小,只要一小掬的水放进去,都会满溢了出来的,可是如今任这血水怎样的续续流入这葫芦,都尽量的容积下来,不有一些些的溢出,看来尽你来多少,他能容得下多少的,真可称得上一声仙家的法宝了。不一会,早把这一池子的血水,吸得个干干净净了,就是那些血蛆,也不有一条的存在,都顺着这血水流动的一股势,流入了葫芦中去。于是红姑很高兴的一笑,随手把这葫芦系在腰间,又把身上的衣服抖了几抖,似欲把衣服上所余留的那些血蛆,也一齐抖了去的。一边说道:“现在第一步的办法,我们总算已是做了,所幸的,我们都不是什么邪教士,衣服上就沾上了这些污血秽水,讨厌虽是讨厌,却一点也不要紧。倘使这恶道易地而处,那就有些难堪了,恐非再经过若干时的修炼,不能恢复原状呢。”
那婆子最初也照了红姑的样子,抖去了衣服上所余留的那些血蛆,此后却直着两个眼睛,只是望着那个葫芦,好似出神一般。红姑一眼瞥见,早已理会得他的意思,便又笑着说道:这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讲到道与法二桩事,道是实的,法是虚的。道是真的,法是假的。唯其是虚是假,所以一般修道士所作的法,也正和幻术家的变戏法差不多,表面上看去虽是如此,其实也只是一种遮眼法,不能正正经经的去追究他的实在情形呢。依此而讲,我的这个小小的葫芦中,能把这一池子的血水都装了进去,就没有什么可以疑惑的了。但是你要说我这葫芦中,实在并没有装得这些血水么?却又不尽然。那我只要再作一个法,把这葫芦尽情的一倾泼,立刻又可把这一池子的血水,重行倾泼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