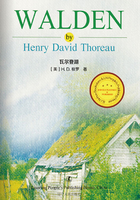与生俱来的浅层意识中,大量充斥着对名人的膜拜基因,马拉多纳和克鲁伊夫,乔丹和约尼尔,大松博文和海曼,庄则栋和荻村伊智朗,韩健与林水镜,科马内奇和李宁,盛中国和梅纽因,小泽征二和李德伦,费雯丽和玛丽莲·梦露,帕瓦罗蒂和瑞奇·马丁……这一溜长长的名人你不但张口就来,而且他们属于哪个行你绝不混淆。至于文坛,你当然更记死了不同时代的各国代表作家或同一流派中的不同宗师……应该说,你的记忆功能在很大的成分上是为了记取各种名人而存在,梳理如烟往事,残存记忆的丝丝缕缕,竟大都由名人牵引。比如说起“文革”你不可能忘记蒯大富,不可能记不起聂元梓;上山下乡后你知道了董家耕和邢燕子;学大寨那会儿你注视的是陈永贵和郭凤莲……当然,以后你终于渐渐知晓陈景润,知道顾准,知道死后才成名人的王小波……对名人记忆的顺序,基本上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你的人生经历,也可以或朦胧或清晰地凸现着你的心路历程。在记牢各个时期的名人同时,你的履历轮廓、识辨能力、智商程度以及你的观念、意识等有形无形的东西都在嬗变,都在调节修整,都在重组成形……
原先你做梦都不敢想当“名人”,以后在一定狂热的氛围里,你曾经一度有过蟾宫折桂的雄愿或者野心。学着名人的举动,枕着名人的梦境,打发了不知多少时日。万万想不到的是,“名人”的行列在不遥远的昨天居然向你招手了,一封封名目不同但内容并无二致的“入典通知书”或“入选通知书”曾使你激动难按,曾叫你热血沸腾,曾令你夜不成寐而奔走相告……表现欲,亮相欲,都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原始秉性之一是向往伟大,向往有出息,向往出人头地,向往鹤立鸡群,向往享受芸芸众生射来的仰视目光,向往前呼后拥的威仪和一呼百应的尊严—谁说你不应该成为“名人”?你出版过印数不少的小说集,你敢在大牌杂志上撰文对某经典之论进行质疑,你还曾应某大学文学院之邀去开过讲座,在大学生们提出许多锋芒犀利却脱不了稚嫩的问题中,你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此刻你拿出十二万分的虔诚和认真,并选择一个最利于思维和措辞的清晨,工工整整地写出你的简历和“成就”,宣泄了激动难按和理所当然,脸上写满了踏入“名人”门槛之际的得意,然后寄出—当然少不了“按规定订购两册书以上”—然后收到样书,然后……
最初翻阅这本洋洋上百万字的“典籍”,当然充满神圣感,但很快你便发现了荒唐,继而便骂自己“倒丁”(这句海南话和普通话的“神经病”同义却比后者生动百倍)。上面除了收录当下稍有名气的若干名家外,还有一批已入典的在校大学生,其诗集竟被括号注明“待出版”。这已经使你笑着摇头了。再翻读“系列名典”中的其他分册吧—有一位县文化馆馆员,其成就是为三首农谚谱过曲(简谱);有一位中学教师,其教改业绩竟是“在照顾好高位瘫痪的妻子的同时,还能自制粉笔,自制教鞭……”再读下去你已经笑不出声了,这会儿你感到最可怜的竟是自己。
任“名典”顾问的是数十位大名鼎鼎的名人,任主编的是名声显赫的某某某,至于编委,至少有三分之二多你不知为何许人也。中国的顾问大多是“不顾不问”,他们和主编一起,居然用自己的“名气”来冒这个险,你对他们也生出了可怜。
其实“名人”何用入典?比如鲁迅,你若称其为“著名作家”,岂不引来笑话?翻读一本本“名典”,想想我辈的所为,从此你还敢以入“名录”来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