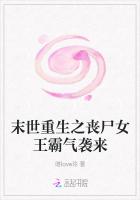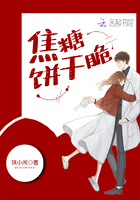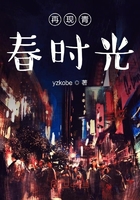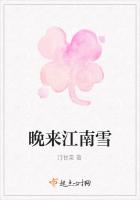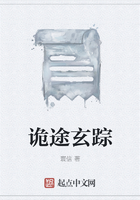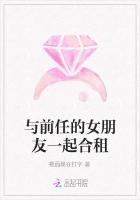以理服人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以情动人也是一种高效的沟通方式。成功的演说,更多的是演说者以自己的热诚来打动听众,以激动人心的情感来打开听众的心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无论怎样的说理,最终还是要演说者打动听众的心,让听众从心底里彻底归依于你。
情感冲动是人类特有的行动动机。比如,在人类的购买行为中,有学者统计过,事先并没有一定的规划,仅仅是由于一时的情感冲动而产生购买行为的,占68%。
触发人们的情感领域,使其产生某种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相对于触动人们的理性领域,产生某种冲动行为而言,前者投入低而产出高。
这正如人们的恋爱行为。女青年一旦情感上认可了男友,那怕从理性角度看,男友又穷又丑,女友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恋爱中的情侣,触动了双方的情感领域,因而就会抛弃理性的选择。
“热诚”是人们触动对方情感领域最重要的“工具”。即使再冰冷的心肠,遭遇“热诚”人的“攻击”,也会变得软起来、变得温热起来。
成功的演说,不仅与演讲者的热诚分不开,而且往往正是演讲者的热诚叩开了听众的心灵,触动了听众的情感神经。
1863年11月19日,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这是一场庆祝军事胜利的演说,歌颂那些为理想献身的人们。林肯用他最热烈的情感,赞美那些做出牺牲的人们。林肯当年的热诚,今天让我们读起这篇演讲稿来,仍然热血沸腾。林肯说——
“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孕育自由的新国度,他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并为此献身。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这是一场检验这一国家或者任何一个象我们这样孕育自由并信守其主张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的战争。我们聚集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将这个战场上的一块土地奉献给那些在此地为了这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作为他们的最终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适当和正确的。
“可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我们并不能奉献这块土地——我们不能使之神圣——我们也不能使之光荣。因为那些在此地奋斗过的勇士们,不论是活着的或是已死去的,已经使这块土地神圣了,远非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予以增减的。世人将不大会注意,更不会长久地记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然而,他们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勇士们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地,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勇士们未竟的工作,那些曾在此地战斗过的人们已经把这项工作英勇地向前推进了。我们应该献身于他们为之奉献了最后一切的事业——我们要下定决心使那些已死去的人不致白白牺牲——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至于从地球上消失。”
亚伯拉罕·林肯对那些为了自由而逝去的人们热情地颂扬,对他们为之追求的事业热诚地赞颂,让每一个听了他的演讲的人,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感染,为这些伟大的人骄傲,为自由的国度而自豪。
演说者在演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它要经历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往往是情感的铺垫。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在这个铺垫里往往作一些情感的交待,让听众缓缓进入状态。
随着一些背景情况、思考动机交待完毕,就要进入情感的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往往更多的是演讲者讲清自己的观点想法,列举相应的事例,让听众的情感渗透到演说者论及的各个领域,从而摧生出情感的波澜。
当理性的交待完毕之后,演说者就得引导听众进入情感的高潮。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第三段述说的内容,它引导了听众产生出高昂的情绪。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演说者呐喊的声音,听到了演说者为他的国度、牺牲的英雄强烈的情感的呐喊。
有的演说者为了强化听众的情感,让听众被鼓动的情感有一个强烈的喧泄,让听众之间有一个情感互动的平台,常常会主动地带头喊一些口号,或请他的现场辅助人员带头喊一些口号,让听众在口号声中将热诚一迸发出来。
有的人故意将热诚的高潮部分安排在演讲的收尾,对于那些要求听众立即采取行动的演说来说十分有用,比如号召大家购物或投票。有时某一位听众在听了演讲之后虽然触动很大,但他很可能还在犹豫不决,还时,异乎寻常的号召力促使他最后下定了决心。
有的演说才为了加重自己的“情感输出”,将语言配合一定的手势,如五指收扰,紧握拳头,伸过头顶,来表示自己激动的感情、坚持的态度、必定的信心。有的人伸出自己的手掌,掌心向外,指尖向上,来表示自己一往无前的气势,显示自己的坚决和力量。
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的热诚,带来某一个道具,如一张报纸来一叠宣传材料,在热诚高涨的时候,挥舞这些手中的“道具”,调动大家的情感一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