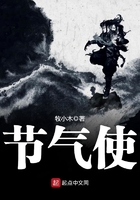高且闲扶起白羽,在他身上连点八下,封住血脉,卫幕力犸与没藏户这时抢了上来,与夜无月三人将两人围在中央。
卫幕力犸将钢叉虚刺了几下,正要上前,夜无月喝住,看了高且闲一眼,转过身,长袖一动,“嗖”的一声,一炷燃着的香已钉在不远处的柳树,听她幽幽地道:“我虽发过誓,一年之内不杀任务以外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手下不能,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高且闲没想到局势突变,落到这般被动的境地,深深地看了夜无月一眼,并不多言,扛起白羽踏湖北去。
一口气飞奔出二三十里,他心想自己死了便罢,决不能连累了白羽,当下找到了一处医馆,问过伤势,将身上的二十余两银子全部拿出,再三嘱咐大夫要用最好的药材,好生照料,两月之后他当再来,人若治好了再加二十两作为酬谢,倘若稍有小恙,定然取他狗命,说着一掌拍碎一张方桌。
那大夫见状,又是欢喜又是惊惧,唯唯诺诺得应承下来。
高且闲离了医馆,心想残烛之事未了,若不是白羽伤重,自己无论如何也绝不会一走了之,于是发足便往回奔。
盏茶功夫来至湖畔,只见波光粼粼,有如万条金蛇涌动,湖上舟楫船只络绎来往,岸边垂柳迎风摆动,哪里还有夜无月等人的影子。他暗自奇怪一炷香时间早到,自己沿途返回,为何不见夜无月三人踪迹?
疑惑间,忽见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高且闲凑了上去,只见人群中央躺着一人,那人倒在血泊里,身上九个透明窟窿,死相甚是凄惨,高且闲看出乃是那肥胖白卒下的杀手,又细细想了一番,不免捶胸顿足起来,暗道:“她只说我有一炷香的时间,却并没有说到底要杀谁!唉,是我连累了无辜!”
高且闲心中又是愤恨又是难过,大骂那肥胖白卒凶残。他原来一直认定是夜无月杀了残烛无疑,但给白羽讲了来去,相当于自己又梳理了一番,发觉此事确实疑点重重。
其实他心里一百个希望夜无月不是凶手,这样自己不用杀她,两人比翼双飞,岂不快美?但此事夜无月确是担有最大的嫌疑,除了她外再无其他线索,因而要查残烛的死因,只能继续从她身上入手。
高且闲寻思三人不追自己,必是回往西夏复命,以自己异乎寻常的速度,决计能够追上,于是立时往西北方向赶去。
追了一日,内力渐感难支,在客店打尖过,顺手牵了匹良马,又追了一日,进入庐州境内,却仍不见三人半个人影,不由犯起嘀咕:我跟踪无月时,她不向西,反而向南,莫不是这次故技重施?倘或如此,我这样追下去,岂不南辕北辙?
正想着,远远地瞧见路旁一家茶棚,其时烈日当头,途中跋涉,早已口渴,于是下马而行,一个胖老者见来了生意,连忙迎了上来,将马牵到一旁去喂。
高且闲走进茶棚,那茶棚颇为简陋,棚内只有两张桌子,桌面坑坑洼洼,显是年代久远。
高且闲捉过一条板凳坐定,一个老妇从灶上过来倒上茶,那老妇鼻歪脸肿,丑陋无比,高且闲端起茶碗,心念一动,问道:“阿婆可见过三个异域装扮的人?两个男人,大概三十多岁,一个执叉,一个执耙,另有一个女子,二十上下,碧眼紫唇,生得极美。”
老妇想了会儿,忽然仿佛想到什么,目中露出欢喜,连连点头。高且闲本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真能有所收获,不禁大喜过望,“噌”的一下站起身问道:“他们去了哪里?”
老妇张了几下嘴,却只发出“啊啊”的声音,同时手里不住做着比划,傻笑不已,原来是个哑巴。
高且闲看了半晌,见她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一头雾水,正待再问,胖老者到棚后栓了马回来,赔笑道:“客官莫怪,小的老伴几年前受了些刺激,自己割了舌头,之后一直疯疯癫癫的,客官要问什么,小的来答便是。”
高且闲重复了问话,老者闻言神色黯淡,老泪盈眶,高且闲奇道:“你只须说见没见过,何必这副形容?”
老者自觉失态,忙拭了眼泪道:“不瞒客官,昨儿傍晚确有三人在小的这里歇脚,不过却是三个男人,其中两个的兵器与客官所言的一般无二,另一个并非女子,而是个青年,眼睛倒没注意,紫色嘴唇小人却看得分明。”
高且闲暗想:“不过是无月扮了男装而已,定是他们无疑,只是他们怎么行得这般迅速,昨日傍晚就到过这里!”口上道:“他们哪里去了?”
老者答:“他们在小人家中歇了一宿,今早小人起床时只见床上放了五两碎银,不知到底哪里去了。”
高且闲先失望了一阵,随即暗喜,心想如此看来,至少自己并没有追错方向,接下来不吃不睡必可跟上三人。
老者道了句:“客官请慢用!”转过身去。高且闲听他声音哽咽,仿佛有什么重大的愁苦一般,问道:“老先生可是遇到了什么不平之事?”
丑妇见丈夫伤心,拿擦桌的抹布在老者脸上抹了几抹,老者知老伴是好心,抓住她粗糙的手,一把抱住嚎啕大哭起来。高且闲愈看愈奇,但见两人相拥而泣,不便插言,只讪讪得喝了几口茶。
待老者哭声稍止,高且闲又问:“老先生到底有何苦楚?”
老者长叹口气道:“这原是小人家门厄运,昨夜又因那个紫唇青年生出了许多事端,先才听客官口气,想是有急事在身,这些家丑,唉,不说也罢!”
他越是如此说,高且闲越发感兴趣,忙道:“但说无妨,说不定在下还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老者打量了一番高且闲,面上一喜道:“客官此话当真?”
高且闲道:“快说吧!”
老者让丑妇继续进屋烧茶,自己坐在高且闲对面,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娓娓道来。
原来这老汉与那丑妇成亲数年一直杳无儿息,直至二十三年前,菩萨保佑,两人终于看到了希望,自是欣喜若狂,十个月后竟一胎生下两女,两个女孩各有缺陷,大妞是个瞎子,二妞因聋而哑,初时并无其他不同,但随着渐渐长大,大妞越来越美,二妞却愈发丑陋。
所幸的是,姐妹两个感情一直极好。到了出嫁年纪,大妞凭着貌美,很容易便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员外,可二妞却犯了难,丑妇到处为二妞张罗,终究没一家愿意娶这样一个又丑又残的女孩。
大妞听说妹妹嫁不出去,恳请丈夫收了二妞为妾,丈夫不肯,于是大妞毅然逃回家里,并说除非有人肯娶她妹妹,否则绝不再嫁!老汉夫妇又打又骂,可大妞性子执拗,甚至以死相逼,两人只好作罢,搬家避祸。
几年前,终于有人愿意同娶两女为妻,那人虽是镇上一个不务正业的泼皮,夫妇两人合计了一番,便准了这门婚事。那泼皮喜滋滋得将两人娶回家,过不多久,两人又逃了回来,原来那泼皮言而无信,只是贪图大妞美色,将二人娶回家后,强行将大妞玩弄了一番,对二妞却是一碰也不碰,甚至加以辱骂鞭打,大妞气愤难当,趁丈夫不备拿出枕下藏好的剪刀戳死了他,领着妹妹逃回家来。
夫妇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再次搬家,隐姓埋名,因当初这门婚事乃丑妇一力促成,受了这件事的刺激,神智失常,竟割了自己的舌头。
大妞心里一直觉得自己行为莽撞,甚是对不住父母恩德,不仅没能让父母享上一天的清福,反而总使他们操心,因而始终暗暗留意。昨夜来了三个男人寄宿家中,大妞听父母说为首的竟是个俊异的青年,一下子动了心,便向那青年表露了心意。
谁想青年一口回绝,丝毫不留余地,大妞心想连我都不能打动他的心,更别说妹妹了。当下万念俱灰,但仍没忘了妹妹,又问起另两个三十多的男人是否愿意娶自己的妹妹,两人当面虽然谢拒,但待大妞出门,那持耙的追了出来,他想着姐姐这般模样,妹妹定差不到哪里,对大妞说自己愿意,说话时对大妞动手动脚,大妞虽然对这个肥头大耳的东西厌恶非常,但实不想父母再为此忧心,只要他能接受得了妹妹,姐妹两人委身于他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