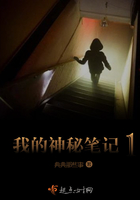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十二月,我对宫中规制也渐渐习惯适应。每逢双日,便一早入梨园跟随念奴排练乐曲;贵妃辰时左右必来梨园,偶有不来便命侍女将我诏去;圣上往往到午时方至,听张洛同几个乐工说,外公午前要处理长安送来的机要政务。
将至岁末,圣上对梨园乐舞尤为看重。与贵妃日日督促排演,几百人中往往能察觉谬误,给予纠正,让人颇为敬服。我渐渐觉得,圣上似乎不像初见时那般声色俱厉。即使众人谬误频出,前方明黄也不过笑道:尔等好好排练,且不可让三朗失了颜面。每到佳处,更施施然沉醉其中,俨然一个痴迷乐曲的艺匠。
同为琵琶乐手,张洛对我的厌恶却是一如继往,这跟火火说的“洛洛大大咧咧,极是好哄!”大相径庭,我觉得我就是把那琵琶坠珠金簪三跪九叩送给她,也不会改善些许。既然想不通其中道理,索性暂不去管她。好在李晴空待我仍算亲善,贵妃娘娘又暗中照顾,我琵琶技艺逐日精进,园中弟子也多愿与我交好。偶尔听到一些“宋辰倚仗贵妃娘娘才能自由出宫”之类的酸言酸语,我也只当被嫉妒,没什么好驳。
一日用过午饭,我趁贵妃休息向云容告了一声,欲回梨园练会儿琵琶。刚出贵妃寝宫,就见李睛空跑上来,二话不说拉着我便往宫门跑。我正自奇怪,远远看见张洛一个巴掌朝丝桐打去。心下一急,忙叫“住手!”那巴掌却已落在丝桐左颊。
我气血上冲急步赶上,将丝桐往后一拉,语气愤然道:“张洛,你身为兴信公主之女,需有些皇家的风范气度。为了一支金簪对我的侍女动手,白白折了公主的宽厚仁德。丝桐,明日找工匠比着那金簪做个十根八根,有位姑娘稀罕得紧!”
张洛早已气得涨红了脸,指着我声音发抖道:“你胡说——,谁稀罕你那破簪。你的侍女做了——什么龌龊事,你自己问她。旁人都不好意思开口!”
我听“龌龊”二字,不顾李晴空阻拦,声色俱厉道:“你少血口喷人!丝桐为人我最了解。”又一把拉住她左臂,“立即向丝桐赔礼!”
丝桐怕惹祸,和李晴空一边一个劝我放手,我看着丝桐红红的左颊,只将握着张洛的手又紧上几分,厉声道:“赔礼!”
张洛却仍是死犟:“就是她仗着容貌,引诱我表哥!倓才看不上你,你就是一口恶痰——”
我气得张手欲打,却觉手臂一疼,肩部“咔,咔”两声,被人反缚背后。只听一个女声道:“敢对陛下的外孙女动手,胆子倒是不小!”
张洛顺势哭道:“姑姑,你来了!就是她们,合起来欺负我!快帮我打她们一顿!”
纵是我疼得眼中飙泪,也瞄到李晴空脸色一变,心觉张洛——真是傻得可笑,便忍不住笑了出来。
背后那人却将我一放:“你倒是好气魄!今日之事到此为止,谁都不许再提!”
我见那人三十多岁,甚是强健。力不如人,当然见好就收,却仍正色道:“本就是你们理亏在先,今日之事我便不再计较。但往后若再有人对我们出言不逊,纵然闹到贵妃乃至陛下那里,我也要将这道理辩上一辩!”
张洛还欲说什么,那人一句“够了!”硬生生拽着张洛往梨园走去。
我正欲向丝桐问清缘由,却被李晴空拉着寻向右方假山,抬眼见房乘迎面走来。我有些惊鄂:“乘哥,你怎么在这里?——你在这里,却眼睁睁看我们受人压制?”
房乘面带微笑道:“我跟父亲前来面圣。每次遇见你,都在打抱不平,当真以为自己是湖海女侠吗?今日吃点儿亏倒正好!”
我心里记挂着丝桐,假装愠怒将头一瞥道:“不跟你说了!”转身去向丝桐询问今日之事,只余李晴空和房乘施礼闲谈。
原来这些日子丝桐秋容依制无法随我入梨园,只能在宫门旁偏厅休息等候。每当丝桐来时,倓往往寻些由头来此“叨扰”。次数一多,便不知被谁传到了张洛那里,才有了今日的麻烦。
丝桐很是羞愤地道:“小姐,有了今日之事,丝桐往后再不出家门一步,免得避不了李倓,反招是非。”
我笑着叹道:“他让你叫李倓的?火火读书懒散,对你倒是颇为勤谨!”
丝桐却神色一肃:“小姐再别说这话!建宁郡王心性未定,言语行事岂能当真?纵然当真,我李丝桐也不个是逆心屈势的!”
我知她行事向来刚烈,当下只能点头称好。细究其意,暗叹火火前路茫茫啊!
房乘过来劝我在宫里务必收敛脾气韬光养晦时,我非常讶异地问他,是否相信鬼神?因为他被我姑父附体!拉起李晴空说笑着往梨园跑去。
李晴空很是郁郁:“之前他说我门第太高,百般推拒。今日他父亲被封漳N县男,爵位世袭,自己也任职弘文馆秘书郎,却仍只是对我以礼相待,尚不及待你的十之二三!辰儿,你说这是为何?是我所做不够好吗?”
我不知该如何做答,细想回道:“他的心意,我也不好说。但我与乘哥以乐相交,想来是我俩皆喜古琴,多了些共通之语吧!”又想乘哥忽然进了弘文馆,之前倒从未听他提起。弘文馆与隶属东宫的崇文馆不同,为太宗所设全国藏书之所。太宗以来的弘文学士,如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封爵拜相者大有其人,其下学子更可依国子监太学生例参加科举入仕,是以长安贵胄争向往之。
却听李晴空又道:“我生为爹爹幺女,家中子弟众多,却凭着聪明通透自小得宠。看够了贵族相交的谨慎拘泥八面玲珑,便尤其想从自己嫁娶大事起可以纵情任性。我爹身居高位,朝中多少王孙公子妄想攀附,可我喜欢房乘,只想让他娶我,数月来明示暗示,他却总是拒我以千里。我只能自己胡乱猜测,以为他喜欢的是公孙芷兰,日日前去胡闹,却不想让他对我越加反感。爹爹不忍看我日日愁苦,安排我随圣驾来骊山舒缓散心,可‘求不得’的滋味便如同天降飘雪,柔美绵密,落手却只是湿了掌心。”
我由人推己,又由己推人,出言劝道:“人心肉长,精诚所致。你日后一心为了他好,终有一日能被他看入眼中。”哪里像我,若一心执著,只会因为枉顾人伦受尽谴责,更不敢如她这般宣之于口,不禁心中一片酸楚。
她却好似稍觉轻松似地又道:“前日听爹爹来骊山见驾时说起,年关将至各地官员将回京朝贡述职,请陛下圣驾早日返京。陛下不舍离开温泉宫,爹爹便谏言于骊山修缮百官官署,一则此后百官可随圣同往,便于处理政务;二则以骊山温汤赐浴百官,大显圣上皇恩浩荡恩泽朝臣;三则陛下也可以安心养身,福寿延年。还说房琯任职地方时政绩卓著,且是前正谏大夫房融之子,家学渊源,雅有巧思,推荐其负责主持修缮事宜……”
说到此处,她抬头看向我,见我凝神细听,又低头浅笑道:“我听爹爹说到此处,再也听不进去。一心想着房琯近日必定来此谢恩,不知房乘——可会随父前来?”
我抿唇了悟:“所以你才拉我来宫门等候?亏是来了,才看到张洛那臭丫头欺负我家丝桐!晴空姐姐,刚为张洛出手的姑姑是谁啊?也不知道她们会不会到御前告我一状?”
李晴空往我背上一拍,笑道:“侠女,刚才那么言之凿凿,我还以为你不怕呢!放心吧,那位姑姑是张洛的教养姑姑。张洛最爱任性胡闹,兴信公主怕她惹事,专门找了个武艺高强的管着她。御前告状这事儿呢?洛洛定然不敢。”她看了看周围,将声压低接道,“我爹爹曾说,咱们这朝自开国以来,前有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后有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干政弄权,武后更甚,竟至改朝更元,再加上前些年太子作乱,陛下一日失三子。是以咱们圣上对皇子后宫都颇为忌讳,在诸王公主的教养上也更为严格,盼其温良恭俭、勤谨顺达。洛洛虽胡闹,却决计不会到陛下面前自找麻烦。”
我感激她对我推心置腹讲解详尽,大肆张扬地一礼道:“姐姐博古通今,又详加提点。以后乘哥的消息,便由小妹鸿雁通传了!”
李晴空一喜,安慰道:“梨园那些闲言闲语,你不用理睬。过几日自然会消失于无形。”
二人互通心意,都觉得多日抑郁一扫而空,相携大笑离去。
我这“鸿雁”的职务马上便有了用武之地。只因次日我与火火正为姑父布置的题目绞尽脑汁时,房乘来到了崇文馆。说是协助父亲主持修缮官舍,部分资料残缺不全,特来崇文馆借阅查寻。姑父表示,次律世叔之事,必将全力相助。次律,是房乘父亲房琯的字,入京后听姑姑说,房家与姑父家先辈便同朝为官,相交多年。后两家皆迁离长安,虽渐渐有些疏远,却多有书信往来。
不过这些事我却不怎么关心,只是于第二日充分发挥“鸿雁”的功能,把房乘来崇文馆之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晴空,并将她收集的《阳春》、《白雪》古本转给房乘。
俶看着房乘欣喜地翻看手中曲谱,一阵惋惜:“本想回京后便找来送你,没想到你自己先找着了。”
我怕说出实情房乘不愿收下,事先和李晴空商量,只对房乘道:“有人请我转交。”背下才向俶、倓、郭晞道出实情,不想倓对我的作为却甚不看好,俶无可无不可,郭晞一副随你怎么胡作非为的表情。
一来二去之间,我又帮李晴空香囊、糕点地传了好几回,房乘皆含笑接受。
看着他和姑父、紫阳道长相谈甚欢,郭晞却与火火臭味相投,我时常向郭晞感叹:“你和乘哥性情互换一下倒更合理!”
丝桐果如其言,再不愿随我入宫,便是到了崇文馆对倓也是有多远躲多远。倓不明就理,很是烦闷了一阵,逼我说明缘由后,愤愤地入了宫。于是第二****遭到了一对核桃的怒目而视,从此张洛便对我敬而远之。
眼看到了岁末,陛下不得不下令回京。终于要见到长安亲友,人人难掩激动欣喜。许是因为心情好,脸上自带三分笑意,旁人便也含笑待我,亭台殿宇山野冬风也越发显得春意盎然,暖气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