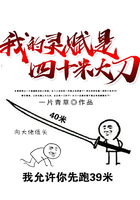秦泰一看来人气就不打一处来,在清泉县居住十来年了,老对头了,段县丞,这人姓段名叫段登,本地人氏,他家早年是农户,爹妈就盼望着他能中个举人,中个进士什么的,出人头地,连取名字都用了一个五子登科的“登”字,就像现代超生游击队恨不得把生的每个女孩都起名叫“招弟”、“再招”、“还招”一样,是一个心理,可你想“登”、“招”,那都是你的愿望,并不代表着老天爷肯定能听到,并且命运往往恰相反,越是这名的越是不中,真恨杀人也!话说这青年时期的段书生就是这么一个货色,看书真没什么天才,偏考试还十有八九发挥失常,你想,他正常情况下都不能考中,更何况失常乎?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大概没气得冲出屋去乡下把这人揍一顿,已经是开恩。
而段登其人呢,于是觉得命运不公,整天念叨着“命运多桀,时运不济,冯唐易老,老广难封”,这么多年一直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这实在也太丢人了,他家里人也是发了愁,才知道让孩子选错了行,比女人嫁错了朗还难受,幸好又过了几年……他考上了?没有。上面出来一个新政策,说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捐个贡生,这种政策类似于现代的“花钱买文凭”,但总归也可以算是条正路呀!
捐了贡生几年后,段青年——那时候的他已经快四十了,姑且这么叫吧,怀着一颗报国有门的心态踏上了再次赶考的征途,这次是进省城要考举人。也不怎么的,大概是心态好身体就好,吃嘛嘛香写啥啥顺的原故吧,据他自己回忆那年他写的文章,就跟花团锦簇一般,而且吧,那年老天爷也正好患了白内障,再搭上主考官被当时的秋老虎咬了一口,整天心浮气躁的,就顺手那么一划拉……结果怎么样?报喜的大队伍就朝着他住的旅行社的大门吹打开了。外面大喊:“给‘端’老爷报喜啦!您中了举人啦!”老段听了这话差点没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一样,当时晕过去,但他心理承受能力饶是过硬,居然能挺住了,他以一种“天下英雄出我辈”的豁达感轻松的说:“这个客栈里就我一个姓段的,把成绩单子拿给我看看。”一看,里面姓段的连一个都没有。经历冰火两重天的他当时就翻脸了,啊,有你们这么折腾人的吗?那报喜的还嘀咕呢,我说呢,原来是复姓啊!那端段音也不一样呀,你跟我着哪门子急嘛!
经历了这次打击之后,段青年一下子成了段中年。自知靠搞学问的路被堵死,他也只能在老家认真的做起了基层工作。所幸的是贡生也是可以在当地当个公务人员,他由一个县衙的小职员做起,几年的光景,居然步步高升,做到了县丞这个职务。
县丞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常务副县长,主管当地的钱粮、后期供应等,多少也算是个肥差了。和正县长比起来,那自然是差得远,行政品级上差了两个等级不说,这说话的底气也一直强硬不起来,因为学历问题的硬伤在那摆着了:县长是国家直接指派任命过来的,根红苗正,说不定过两三年有政绩就能升任州官,好的还能进京城,而县丞多是下层幕僚提拔上来的,而且这辈子的官命也基本就到头了,很难再被提拔。所以削尖了脑袋往上钻的段县丞一脑袋撞到这块制度的大铁板上,疼痛之余开始了新的想法:官运到头了,得想法儿多搞点钱了。于是乎贪污受贿的事儿他没少干,那么他一腐败而受罪最深的,就得必然是最下面的老百姓了。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给他名字里加了一个字,念来还挺好听“段天灯”。
可到现在谁也就治不了他。这不新鲜,作为一个优秀的坏人,他肯定是能有让自己得意洋洋的一套套路,在清泉县城似乎也只有他能手眼通天,一把手黄县令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俨然已经成了段县丞的傀儡。他儿子段义志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讼师,心肠极其狠毒,仗着熟悉《大明律》,干了很多********的坏事情。
秦泰为人正直,平常没少了跟此人发生冲突。但还真拿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计家江家虽说是正宗的书香门弟,但往往是地头蛇难防,能躲着这家人还是得躲着的。当然段家也怕这三家,特别是怕职权大脾气更大的秦泰,有几次秦泰火爆的脾气上来,把段登像拎小鸡的拎过来,“乒乓”扇顿耳光,段登也没办法,告到黄县令那儿顶多也数落秦泰两句,黄县令也多以“秦泰就是个粗人,你也不用跟他一般见识”之类的话劝解段登。
久而久之,段登是怀恨在心。这次他之所以这么急着骑马跑过来拦着,根本就没有好心。他不是担心秦泰出征后会出什么危险,能不能杀败蒙古军就更不是他操心的事儿了,他只是心里想“听说这次发现蒙军袭城的就是这家伙,如果现让他多得了军功,那万一他因此而升迁了,那不就更欺压在我的头上?不行,绝对不能让他再出什么风头了。最好他再犯点错,刚才那么多蒙古兵怎么就没有一个能弄死这家伙的呢!哼!”
但是段登还是会来事儿的,只见他皮笑肉不笑的下了马,硬是把秦泰也给“搀”,倒不如说是拽的,下了马。一边往下拉他还一边说:“千总守卫城池,可谓劳苦功高了,现在要出城杀敌,这可是关系全城百姓的大事情,可不能轻举妄动啊,万一有个什么差池,这责任咱们谁也担当不起……”
秦泰见是他,把眼一瞪:“万一个屁!我说,怎么段县丞连我军队的事儿也要管了吗?放跑了一个鞑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闪开!”
段登脸皮是真厚!他听了狠话居然面不改色,继续大义凛然道:“守土卫边,人人有责!你做这个出击的决定怎么也得跟县官说一声嘛,你就算不出事得胜回来这个功劳怎么也得有人家县令一点的吧!”
秦泰虽话粗脾气大但这些事儿心里都清楚,暗骂:“我就知道你的那些花花肠子。功劳功劳,老子把脑袋别到裤腰带里跟鞑子拼命去,还要跟你们分功劳!”不过他又一转念头,毕竟他也混官场这么多年了,因为从前心眼直吃的亏他还记得,于是强压怒火,降低了点声调道:“老子倒是想请示他,可打了这半天我连他个影子都看到,他还好意思当这个县令!”
“咳咳……”从城楼里钻出个带乌纱的脑袋来,尴尬的说道,“本县一直在此,一直嗯……观察敌情,搞好各方面的这个……啊调度工作,那谁,秦泰呀,出城这事儿嘛,我看还是小心为上吧。这天还没大亮呢,什么都看不清楚,黑灯瞎火的万一再中了他们的埋伏那可如何是好哇?这可是五六百人的性命呢!他们跑就让他们跑吧!他们不是也没讨着什么便宜不是?我看就这样算了吧,现在的结果已经蛮好的呢!也好向上面交待。”
秦泰这个气呀!
黄县令又接着安排道:“既然敌人已经撤退了,那咱们就已经是大功一件了,秦泰你守城有功,这个咱一定会如实的把情况反映上去的,那谁段县丞你也是一番好意,及时的制止住了这个……个别人的有点冒失的行为,好在最后的局面算是皆大欢喜,那留下点人收拾下残局,大家也都散了吧,哈……欠!困死了,这倒霉的鞑子,真不让人睡个好觉、过个好年啊!”
大家再看城外的敌军已经退去了,城外的漫坡地上只剩下大量没熄灭的火堆,和模七坚八乱躺在地的蒙兵尸体。
“不能散!”这时候猛然跑过来一个中年文士,四五十岁的年纪举止潇洒,但他现在有点急了,他大喊道,“不用多久,蒙兵必会去而复来,而且还会全力攻城的!大家快趁这个机会做准备吧,再晚了就来不及了!”
黄县令皱下眉,再借着火光细看来人,才想起这原来是城南住的江家举人。这时江厚也走到黄县令近前了,给黄县令施了个作揖礼,黄县令忙拱手还礼,热情招呼并客气询问道:“江夫子何出此言啊?”
江厚深知黄县令胆小怕事的特点,于是压低了声音,只在黄县令耳边说:“方才敌兵偷城失败,转为强攻,可是咱们城高士气旺盛,所以他们没讨着什么便宜,但是就这么几次攻城,我看他们的大队兵马还在后面观察呢,刚才冷不丁的退走,一定是他们内部意见不统一,但他们这一来,伤兵折将没抢到东西,他们是肯定不会甘心的,所以会决定先休整一下队伍,回过头来想再趁咱们防范松懈的情况下再来攻城。但如果再等,又怕咱们的援兵赶来,于是也就只有再在一半个时辰内翻回来。我看咱们就再坚守一个时辰到天亮吧,正好也借机准备好守城的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