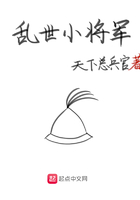3、
是日,我正昼伏经史典籍之间,忽闻堂外金属槌地之声,余音嗡嗡,紧急着传来寅的怒骂:“赣头赣脑死赤佬,不可交也!”
原来,允明遣童子递话,云近日身体微恙,友人悉而探望,无大碍,遂举荐惠州兴宁知县,因祸而福,需整行收囊,不便辞行,奉纹银数两,解时日之急,留书一封,日后有故,可求本方吴县令。寅自是气愤,甚感其辱,甩手将银两抛地,待我忍着白天刺眼的光亮奔到堂前柴门的阴凉处,碎银已洒一地。
童子慌不敢言,忙弯腰拾掇,又被寅一脚踢开,“滚,告诉你家六指主子,我伯虎不识此人。”童子哪里敢停留,连同信书丢下,逃也似的抽离桃坞。
寅兀自言语,“什么东西,笑人贪官之利,自己倒捐了芝麻县令,笑人慕名之义,倒使些钱财坏我名义。”良久,见门前影稀,复关上大门。
我心灵的震撼不亚于银子落地的震动。自我出世之日,见过为求一餐之福跪地乞饶的穷丐,见过大敌来临倒地装死的负鼠,也见过争食相残的同伴。寅的高贵如同他硕大的身躯一同高大起来,我需仰视才能瞻其风采。
不料,寅忽然弯下腰来,逐一拾起地上碎银,并四处张望,细察有无散落。我身旁也遗得一锭,虽疑惑寅的所为,也不愿多劳其神,只好振翅造音,寅终于觅得声源,也看见了我。
见了我,寅顿时换了愉快的情绪,轻轻地夹起银锭,笑着说:“人常说蜚蠊百害,想我数次出手相救,倒晓得报恩。这些许阿堵物,虽毁人心智,不能我留,明朝早市便散去,换得备用之物,也是度它有用之处。”一席话又令我悟解,刀至屠夫,自是杀戮之器,或至厨夫,便成美菜佳肴之具。
不至次日,当夜,寅便由街市切得熟肉,捧得黄酒而归。因念往日有点薄恩,又叫来隔壁老王同饮。
那老王知晓寅是文化人,素来敬重,寅的邀约,自是惶恐,也不敢空手,遂带来酱汁猪肉、清荷粽子、金丝枣饯等时令小吃。只恨那可恶的阿黄也晃着尾巴跟了进来。
席间,老王诚惶诚恐,每每端杯前,便要起身,寅笑着说:“老王,不必拘谨,我伯虎虽曾乡试摘魁,但毕竟已是庶人,何来如此多礼?”
老王卑恭道:“文化人终究是文化人,我等下民,丁字不识,只会失礼。”
寅又道:“什么卵泡文化,都是他人奉承。天子说你有才你就有才,考官说你作弊你就作弊。虽说做得了诗,绘得了画,但没有官家的吹捧成不了气候。想那祝枝山、文征明,画作不在我上,均因有了功名,动辄几十两纹银,而我辛苦几日,也只换得几两薄酒。”许是酒精作用,寅历数过往,几次哽咽,慌得老王只好以“城会玩”、“我小学没毕业”等托词应之。
那阿黄起初得了点肥肉,很是欢快,须臾,见二人只顾唠叨,不再施舍,便有了烦意,几度低吼。我一直以来向往寅的故事,不愿其从中作梗,便振翅直扑其鼻,那厮不曾防备,唬得倒退几步,烛光昏暗,又不能辨别,只好钻进桌底,四处张望。我复冲几个来回,终于惹得阿黄大叫起来:“汪汪!”
这一叫,惊了寅的心绪,老王连忙起身踹了阿黄一脚,“惹瘟,还不滚回家去?”阿黄知主人发怒,只好悻悻离开。
临走,老王起身拜谢,不免又想讨些好处:“先生厚意,老汉我还有件事不好意思开口。”
寅大方道:“但说无妨。”
“我家婆娘的堂姐的儿子的岳丈在县衙当差,县衙的师爷向来仰慕先生,又知晓其女婿的母亲的堂妹嫁与先生邻居,想托我讨得片纸字画。”
寅沉吟片刻,似有不悦,旋即又道,“画是来不及作了,字是有现成几页,你就拿了去吧。”遂从内袋取出一封书信,我看的分明,却是白日童子所弃。
常言说得好,知饱暖方思****。那段不堪日子,寅为省着体力,要么卧床不起,要么扶枕而息,虽日温益高,尚不思净体,周身气息,汗垢相混,甚合我意。现在有些细银,又老王惠赠些小***神不少,支走了老王,遂起灶添柴,烧些温水洗身。洗浴之木桶也是我欢喜之所,地面虽砖块所砌,然湿度宜人,白色的霉纹,恰似杏花点点,木桶底身也因着迷人的潮气,斑驳着绿色的青苔。蚊蝇轻舞,细虫探戈,自是一种繁华。待热水进桶,热气下渗,有翅者翔,有足者驰,又是一种热闹。
我不愿走远,待在砖隙间,看寅慢慢褪去青褂、短衫,露出桃树皮似的慥黑色皮肤,特别是下体耷拉着河鳝般的****上忽生一簇花白卷毛,如暗河蓬生的枯草,又似腐尸疯长的青霉,看得我面红耳赤,怦然心动,恨不得从此长卧期间。
寅的声响颇大,雾气缭绕之间,水花四溅,我慌得跳进散落在地的衣物,又被一阵芬芳迷倒。这短衫布褂,自受寅的肌肤之亲,别有一种气息,令我不能自已,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人的味道。
寅的心情很是不错,离桶宽衣,还来西洋镜前细端。这西洋镜于今虽是普通之物,于当时确是稀罕之货,本朝无工坊可造,均自外船舶来,比之铜镜,影像尤为逼真。当日草堂落成,允明也当重礼相贺。前几日张家小妮子收洗衣物,因无钱可付,愣愣的想取了这西洋镜,要不是张家老妪碍其易碎,不便存放,寅倒是心动。可怜了寅上好的字画入不了老妪昏眼,赎衣不得,逾了期还得依典当每日收资二毛,当日气得寅连声骂道:本来个无产的命,便生的资本家的毒心肠。又诗曰:“数过清明春老,花到荼蘼事了。光阴估值,估值钱多少。望酒摽,先拚典翠袍。三更尚道,尚道归家早。花压重门带月敲,滔滔滔滔,醉一宵,萧萧萧萧,已二毛。”不是今朝窥镜,寅倒忘了这遭,忿忿道:“他日必羞辱这厮二毛党。”
言罢,寅复又起兴,哼着昆曲小调“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自书柜中翻出一本《素女秘道经》,至床前细细研读。
我喜欢寅看书的样子,时而大声吟诵,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像寿镜吾老先生般,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直至从椅子上翻倒过去,时而掩卷沉思,半响不语,语必“搞七粘三,花里扒拉”。这次似有怪异,寅没有坐上书桌,而是正坐榻前,单手托书,腾出一只探至裆部,脸色也转而红润,忽而抽搐,一阵怪风掠过我的腿毛,我本栖在寅的衣物之中,下意识的弹跳开来,有幸避开一笃浆糊。虽然蟑螂喜潮,但黏糊之物,向来惧怕,气味再腥,我也不敢触碰。但见寅气息渐匀,又取地上衣物擦拭,料无甚大碍,方才安下心来。
半夜,寅如厕几次,许是肠胃久未沾荤腥,此番酒肉穿肠,一时难以消受,折腾至四更,方才沉睡。我白日未休,晚上又在寅左右驱除蚊蝇,见天色微曙,赶紧回书柜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