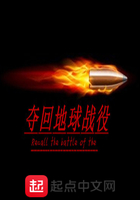西晋末年。
烈日当空,大地一片焦灼。经过不断战乱和饥荒的折磨,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街道上,随处可见因体力不支而倒地不起的饥民。而那些尚在行走的人们,也不过是在这乱世当中强自挣扎罢了。
阿恒抬头看了看天,强烈的阳光亮晃晃的灼着他的眼睛,他舔舔干裂的嘴唇,终于再也支撑不住的倒地——他已经三天没吃过一点东西了。阿恒酸涩的笑了一下,想想从前,那锦衣玉食的生活仿佛梦一样飘渺,他也曾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有钱人家的公子呐!然而八王之乱一起,竟是顷刻间父死母丧,纵有万贯家财,也全部被劫掠一空,徒留他自己,在乱世当中苟活。阿恒闭了闭眼睛,将泪水逼了回去,茫然环顾四周。为了逃避战乱,他从洛阳一路向南,不敢走大路,只好捡山野小径前行,如今这不知名的青山翠垅就是他的葬身之地吗?也好,也好,阿恒想,起码他不用像其他人那样成为别人争权夺利的炮灰。
不知又躺了多久,那种烈焰焚烧般的灼热感终于稍稍减退。周围一片寂静,连夏日最常听见的蝉鸣都没有,饥民早已把能吃的都吃了吧?阿恒苦,再抬头时,居然已经入夜了,周围黑黢黢的山影层峦起伏,银白的月光穿过略显阴森诡异的树丛,静静的洒在阿恒身上,阿恒突然感到一阵久违的平和。
“娘,你看,那边是什么?”
“唔,是木桩子,不用管啦!咱们快走吧,再不回去,你孟伯该不高兴了。”
“不对!娘,你仔细看,好像是个人!”
远处隐隐传来几声对话,似是一对过路的母女。母亲不愿多管闲事,女儿却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一阵伴着银铃的细碎脚步声由远及近,阿恒只觉一只柔嫩的小手抚上自己的头发。
“娘,是个小哥哥,你快点过来看啊!”一个小女童有些焦急的冲远处喊。
一个慵懒的,仿佛凡事都不会挂心的声音无奈应道:“忆儿,你慌什么?今天见的饥民还少?先看看死了没有。”
女童慢慢将小手移到阿恒鼻下,阿恒只觉有淡淡兰香入鼻,只听女童惊喜叫道:“娘,他还活着!你快些过来呀!”
“没死?……倒是命大。”一个女人的声音隐约传来,阿恒未听得她脚步响,就觉得一只冰凉的手已捏住了他的鼻子,他情不自禁的张开了嘴巴,一股甘甜的液体顺着他冒烟的喉咙缓缓流下。
啊!阿恒忍不住舒服的呻吟了出来,他微微抖动睫毛,想睁开眼睛看看眼前的救命恩人,不料那只捏住他鼻子的手猛然一松,阿恒被毫不怜惜的摔回地上。只听那个女人轻松笑道:“好了,死不了了。咱们走吧,忆儿。”
“……娘,他这个样子……真的死不了?”小女童怀疑的说。
“死不了死不了,他现在不过是没力气而已。幸好咱们今日派发的米粮还有剩,水和干粮我已经放在他旁边,等他醒来吃上以后,保证他活蹦乱跳的!”女人说着哈哈笑了起来,声音甚是轻松愉悦。
这个女人!阿恒刚才的满腔感激一下子消失殆尽,一股怒火瞬间涌上头顶。活蹦乱跳?他?哼!阿恒瞥了眼自己骨瘦如柴的手,咬住了嘴唇。很明显,女人不想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安慰女儿罢了。阿恒感到屈辱,他的少爷脾气不允许他就这样接受施舍,他狠住心肠不去看那诱人的水和粮,翻过身去,挣扎着要爬走。
“呦……”女人似乎没想到阿恒会如此倔强,顿了顿,笑对女儿道,“你看是不是,他还能爬呢!”
“……”小女童显然不信母亲的话,她跑到阿恒身边,制止挣扎的阿恒,“小哥哥,你别乱动啊!你没有力气就别动啊!我家就在山上,不如,你跟我们回家吧?”
阿恒还未答话,那个女人先自惊讶叫道:“忆儿,你傻啦?平时让你养条小狗你都不愿,如今愿养这半死不活的小子?……他看上去不如狗儿健壮嘛,当心养不活哦!”
“狗儿应归自然,人应安居乐业,万物有灵,都应各归其所各司其位,这不是娘你教我的吗?”小女孩儿答的虽有些孩子气,但理直气壮,条理清晰,听上去不似一般山野村户。
“呃……是我说的吗?好吧好吧,就算是我说的吧,不过那也要看养不养得活吧?这小子明显饿得不成人形,还有骨气跟吃的作对,怕是以前没挨过饿的……”女人的声音有一丝冰冷和谨慎。
“可是狗儿没法和忆儿聊天啊!娘,家里都没有能陪忆儿玩的人!陆伯伯整天闷声不响,爹又不在身边,你也没法给忆儿生个弟弟妹妹,好不容易捡到了个小哥哥,你就让他陪着忆儿好不好?”小女孩儿哀求道。
阿恒只气得浑身发抖,这母女俩不但拿他与狗相提并论,而且听其对话像是要把他捡回家当仆人使唤了,真真是奇耻大辱!阿恒羞愤的将脸埋的更深,他脑海中电光火石般忆起母亲慈爱的面容,鲜衣怒马的过往,眼中已然酸涩。
“哦,说的也是,也很久没人陪我玩儿了……”女人若有所思的嘟囔了两句,回头瞥一眼阿恒,“喂,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咦,你该不是哭了吧?”
阿恒只觉气血上涌,他再也受不了女人这般淡然玩笑的态度,猛地抬头冲女人大喊:“我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
月光下,一个白衣女子立于翠竹之间,眉目晶莹,轻纱淡笼,一头青丝并未绾起,而是如瀑般散垂于胸前,清风过处,超凡脱俗。她一手牵一个清秀可人的小小女童,一手随意拎着一个包裹,阿恒只觉她的眼睛如一潭清泉般映着自己呆呆傻傻的模样,满面羞红又无所逃遁。而她自己,是那样的清爽平和,仿若看惯了红尘过往,世上的一切都不能使她轻易动容。只听她三分冷淡三分好笑的问:“小子,你叫什么?”
阿恒觉得那声音里多了一份自己无法抗拒的尊贵和威严,不由喃喃答道:“我叫阿、阿恒……”
“小子!那边那边……对对,那还有一只……快点,臭小子!”
伴随着女人的吆喝声,阿恒累得满头大汗的在院子里上蹿下跳,终于将十二只鸡全部赶回了鸡笼,出了鸡笼,一抬脚,将鞋底新鲜的鸡屎随意蹭在院中一棵桃花树上,抹了把头上的汗,阿恒颇有些感慨。夏去秋来,被那母女俩捡回来已经几个月了,他已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变成现在这个杀鸡宰羊烧火劈柴无所不能的小伙计了。可是原本想象的屈辱感不但没有产生,反倒是常常感到一种平和安宁的快乐,仿佛山下的战争饥荒与他无关,山上的庄园里永远是这般岁月静好。
想到这儿,阿恒忍不住再次打量着这个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庄园。这庄园虽不像他以前居住过的宅邸那般富丽堂皇,却排列布局的异常严谨细致,仿佛一个避居世外的世家大族,在竭力用平凡掩饰着自己尊贵的出身。相较之下,自己家原来那明目张胆的奢华反而透露出一种小户人家的不自信了。庭院遍种桃花,花开时节,满室芬芳。正堂居室外的水榭回廊,那碧水清涟映着几株残荷,在秋日夕阳晚照的黄昏显得格外雅趣莹然。庄园仆人极少,但个个训练有素,总管孟伯沉默寡言,但其举止形态隐有大家之风,显然是比他这个昔日少爷要强上百倍的。这样的人居然甘心为奴?虽然知道以自己目前身份绝不该多管闲事,但阿恒还是忍不住暗暗好奇,这庄园的主人究竟是户什么样的人家,到底有什么显赫的过往?
“小子,再去给我取壶酒来!”女子的声音从室内窗口传来,阿恒情不自禁朝那个刚才对自己遥控指挥的女人望去,只觉头痛。茜纱窗下,一个素衣女子横卧于小榻之上,以肘撑头,拎一个酒葫芦乱摇乱晃,轻纱袍袖宽大的下摆微微沾上酒渍,长长青丝随意散着,如一只慵懒魅惑的猫。阿恒每次看到这般情景都会有一种戳瞎自己眼睛的冲动,当初到底是哪根神经不对,竟将这游戏人间的放荡女子看做不惹尘埃的天女下凡?
阿恒不情不愿的捧了一壶酒放到女人跟前,正忙不迭想要退出去,却被一只皓腕一拦,阿恒立时苦脸。
“小子,你吃我家的住我家的已经有几个月了吧?可你到现在好像还未唤过我一声,怎么,我很不好称呼吗?”
阿恒只是低头不语。眼前这女人也是让阿恒好奇的原因之一。这庄园中能称得上主的人,只有她们母女两个,可要说这庄园的主人就是这女人,阿恒断断不信,因为洛阳城中的贵族千金没有一个是这副模样,当世严苛的贵贱之分也不容许家族中有这等野性难驯的女子。可是,这庄园中却不见男主人的身影,所有仆人都以这女人马首是瞻,孟伯也似乎与她亦友亦仆。而且这女子虽说放荡不羁,但身上又时时隐现一股难以忽视的贵气,那一派威严气度若非从小耳濡目染,是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模仿得了的。
“……怎么,叫声夫人就这么辱没了你,恒少?”女子略带讽刺的轻笑在阿恒耳边响起。
阿恒耳根一热,多少有些羞恼。自己的出身瞒不过这个女人,而且阿恒觉得,当初就是因为出身才使得这个女人在收留他时略有犹疑。他来的这些日子,和忆儿,孟伯等人已是极好,身世自然没有刻意隐瞒,他能从孟伯瞬间松下戒备的眼神中看出自己的家族在孟伯眼中是不值一提的轻微,少爷脾气也就随之收敛了很多,再不敢耍性子。忆儿天真可爱,孟伯沉稳老练,倒也很容易相处,只是这个女人……阿恒头疼的觉得,他来到这儿后陪忆儿玩的少,倒是被这个女人玩儿的不亦乐乎。
“阿恒不敢。”阿恒恭敬应了一声。
“哼,”女人鼻子里轻哼一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些什么,你不肯叫我夫人也不肯叫忆儿小姐,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叫了之后你就成了真正的奴仆,有辱家门,是不是?小子,你能活到现在,还真是命大呢……”女人自斟自饮的说道。
全中……阿恒作声不得,只得立住一动不动听女人继续教训,但他心里却是不服,口中忍不住轻声说了出来:“你不也从不好好叫我名字么……”
“你说什么?”女人举起的酒杯一顿,眉目一展,巧笑嫣然。阿恒只觉脊背一麻,已被女人抓到近前,女人细长单薄的凤眼盯住他打量了一瞬道,“嗯,看你的样子长得倒是不错,骨头也硬,倒有几分像……有趣,有趣……好吧,你可以不叫我夫人,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叫……嗯,以后你就叫我,叫我……叫我姐姐吧!”
“……”阿恒无言半晌,慢吞吞道,“你女儿叫我哥哥……”
“那又如何?迂腐!不过是个称呼!”女人不屑的将阿恒丢过一旁,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指着刚进院子的孟伯道,“要真论起来,他也要叫我一声姐姐!”
那不一样吧!阿恒很想翻个白眼儿,但终究不敢,只得无奈的将求救的目光投注到孟伯身上,希望孟伯能赶快过来岔开话题。谁知孟伯明明眼见是有事回禀的,瞥到阿恒的求救讯号后,脚下生生一转,竟向忆儿房间走去。孟伯!!!阿恒心里狂喊,也只能无奈见其走远。
“你不用看他,他跟我多年,早已磨练的波澜不惊,从不会自找麻烦。”女人说着,呵呵笑出了声,似是想起了许久以前的趣事,顿了顿,忽而柔和笑道,“也罢,你就叫我……姑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