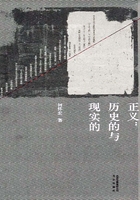淳熙三十七年正月初二,毓缡以凤城为界,正式举兵南下。
初六,克新埕诸郡,守将石义庆阵亡,州牧许绍仓皇弃城北逃。
初十,乾襄粮仓无故起火,北庭守兵强取豪夺而激民愤,是夜,两城城门先后大开。毓缡五万大军一分为二,长驱直入,锐不可当。
短短数日,雁门之北、凤城之南以新埕、乾襄、北庭三城为中心的州郡一一克复,“毓”字旌旗在北风中猎猎作响。
冬意渐浓,凤都的雪早已积了厚厚一层,银装素裹之下,皑皑泛出些许亮色。守城的兵士不住地哈气,暖着那双没有血色的手,偶尔,稍稍跺几下自己冻地发麻的脚。
北国的冬日总有那么几天是极冷的,这个时候,莫说富贵人家,就是普通百姓也鲜少出门。女人习惯在屋里燃个暖炉,做些针线绣活;男人也多半留在家中担水劈柴,即便出去了,也只短短几个时辰。
今年寒期来得早,往年总要等到正月底二月初。所以,本该是过年过节的热闹日子,倏的就冷清了。街面上的店铺三三两两地开着,高悬的大红灯笼被一片银光淡去了颜色。有心人趁此机会制造谣言,说:天象异变,是为易主之征兆。不过这“主”具体指哪一位,说法又是各有千秋。
这一传十,十传百,闹得凤都人心不定,朝臣惶惶忧思。但皇帝似乎浑然未觉,依旧沉湎于声色犬马,醉死于笙歌软香,所以国中大小事物仍由秋慕云定夺。
十三日,兵部尚书崔敬不见皇帝早朝,心中愤懑愈深,一时气急,便指着秋慕云嘲讽道:“听闻右相前些日子又进了二位美人给皇上,不知是何意?!”
闻言,秋慕云淡然一笑,目光缓缓地逡巡着殿上众臣,不答反问:“崔大人的意思,是说我欺君专权喽?”
此话一出,有幸灾乐祸的,有冷眼旁观的,几个刚才还窃窃私语的大臣都尴尬地撇过头去,不敢再说。见气氛不对,左都御史曹尹出来打圆场:“秋相莫怪,崔大人快人快语,并无不敬之意。如今毓缡起兵造反,滋事体大,皇上又政务繁忙,还望秋相多加提醒才好。”
“曹大人所言甚是。”秋慕云点头称许,“不知曹大人有何对敌良策?”
“我们可效仿古人‘围魏救赵’之策,毓缡起兵南下,凤城必空,若派人先行围剿,必可乱其阵脚,分其兵力。待他仓促回防,军心疲惫,再以重兵攻之,一举剿灭。”
“计是不错,只可惜——”秋慕云摇头笑道,“有去无回的会是我们。”
“秋相可是在长他人志气?!”崔敬冷“哼”一声,“世事无绝对,试都没试又怎可断然下定论!我们以数倍之兵,难道还攻不下区区一个凤城?!秋相究竟是不敢,还是不想?!”
“恕秋某愚钝,不知崔大人这又是何意?”秋慕云笑问。
“此事你我心知独明。”崔敬不让半分,语气犀利,“该是我问秋相,频频去凤城又是何居心?!”
曹尹看两人针烽相对的模样,不禁为崔敬抹了把汗,别看秋慕云平日谦谦儒雅,可为政手腕却是极为凌厉,否则,这样一个文人学士怎可在短短几年就权倾朝野。偷偷拽了拽崔敬的袖子,曹尹示意他不要再说,省得惹祸上身。
崔敬强压下心头怒火,很勉强地对秋慕云行了个虚礼:“崔某不会说话,让秋相看笑话了。”
“是啊是啊。”曹尹佯笑道,“为人臣子,说来说去都是为了皇上。秋相深得皇上倚重,秋相若是能多加劝谏,皇上必是听的。——仅以三万兵士对敌,实属不妥。”
“曹大人果真是明理之人,不过——”秋慕云似是为难道,“这君是君,臣是臣,秋某总不能僭越了这君臣之纲,皇上要如何,岂是我能左右?!”
“这......”曹尹一时语塞。
可崔敬不依:“事在人为,皇上是明理之人,而今柒澜正处多事之秋,定能体谅我等苦处。——若秋相不愿,我们可自行去见皇上。”
“最好不要。”秋慕云笑着制止道,“‘皇上有命,所有人等一概不见。’崔大人莫非是想抗旨么?”
“抗旨又如何?!”崔敬义愤填膺,一副凌然之态,“是非忠义,我问心无愧,就是死,也不污了我家祖坟!”
“好个是非忠义,好个问心无愧!”一声冷笑,一记隐怒,那明黄色的身影从偏殿缓步而出,迈上金殿,慵懒地落了坐,眼神里尽是疲态,不过说话却依旧威严。众人见皇帝来了,纷纷垂首下拜,口呼“万岁”。没有让他们起身,皇帝只懒洋洋地笑道:“崔爱卿,你这么想死,朕就成全了你。来人——”
“皇上且慢!”崔敬没有求饶,可曹尹膝行几步,叩头请命,“崔大人心忧社稷,皇上不能错斩好人!”
“哦?”皇帝眉眼中是一丝兴味,身子又往后靠了靠道,“这么说来,是朕的错喽?”
“微臣不敢,如今毓缡兵乱,皇上若不一举剿灭,后患无穷。”曹尹言辞恳切,妄图打动皇帝,“崔大人素有奇谋,是不可多得之材,皇上何不让他戴罪立功?”
“崔敬,你可知罪?”皇帝瞥了眼脸带桀骜的他,微阖了双眼。
曹尹心里舒了一口气,听皇上这口气,事情应该是了了,可崔敬下面一句话,又让他心惊肉跳起来。只见他昂头朗声答道:“微臣没错!”
“你说什么?!”皇帝睁开眼,脸色阴沉。
心知自己怕是过不了这道坎,崔敬索性把多年来的怒气与愤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柒澜缭乱已久,国事衰微,始帝宏图,成了满口空言。外有曦凰虎视眈眈,内则君不君臣不臣,我入仕多年,眼见百姓流移而不可为,心恨家国无力而叹扼腕,庸碌隐忍,而今仍落得这副光景,可怜可叹!”
“屈子投江,少时曾恨其不争,而今方知他争而无得之绝望。”崔敬大笑一声,忽而抽出侍卫腰间佩刀,猛地一刺,血溅五步。秋慕云身上淡青朝服,也隐隐染上暗红。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臣就不麻烦你了......”
一时间,众人相视无语,整个大殿显出一室的寂色。
“皇上——”曹尹悲哀地唤道。崔敬素来正直,不过平日向来少言,他也一直忽略了这个汉子的满腔热忱,今日听君一席话,顿时感慨万千:此国此家,当真值得么?
“你们既称朕‘天子’,那么朕自当有天命庇护,区区一个毓缡,一群乌合之众,怎能轻易撼我魏家江山?!”皇帝似是不以为意,“不过卿家之言,还是有几分道理,那就再添三万,另择将帅出征吧。——众爱卿可有合适人选?”
“臣有一人。”秋慕云欠身答道,“他叫靳砚楚。”
靳砚楚?众臣面面相觑,一脸茫然。
“哦,秋相也来荐人?”皇帝笑道,“不知是何人,能入的秋相之眼?”
“皇上严重了,只是一校尉而已。”
校尉?!人群里有人“吃吃”地暗自笑起来,皇帝也满是好奇之色。
“那就如此吧,朕封他为将,明日就出征吧。”皇帝挥了挥手,示意众人起来,然后打了个哈欠,向着偏殿走去。曹尹道了声“不可”,还要说些什么,却被皇帝堵了回去。
“爱卿,朕今儿才懂了这‘醉生梦死’是为何意了,哈哈哈。”朗笑几声,皇帝在黄门的搀扶下去了,空荡荡的大殿,只剩下了那个孑然修长的身影,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棂射将下来,使得衣服上暗红的血顿时鲜亮不少。
叹了一叹,秋慕云唤过一旁站立的侍卫,示意他们把人抬走,然后道:“送去崔大人府上。”
“是。”侍卫应道,“秋相还有何吩咐?”
“没了。”秋慕云背过身,“下去吧,把门带上。”
尽管有一丝疑惑,可他还是照做了,门关上的那刻,侍卫眼中这个年轻右相的双腿似乎颤了一颤,阳光照着的身影,仿佛透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