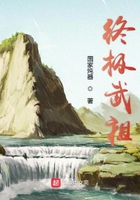营救罗丁一家的行动在最后的一刻终于奏了效。回家的路上母子俩真是又惊又喜。他们都有着死里逃生的感觉。他们都知道这是谁的功劳,因为罗丁事前已经把祝平跟他说的告诉珍英了。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祝平是如何地为他们奔走的,但是他们老是去胡乱地猜测。突然间,珍英想出来了。只见她把罗丁的肩膀一拍,说道:
“丁儿,你知道那个军代表是谁吗?……说不定他……上次我就听人家说咱街道的军代表是本地人,是住在城西那头的……”
“妈,祝平的家就在城西!”
“丁儿!”
“妈!”
随后珍英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晓波堂叔因为这事坐了牢,而我们家却得了这份恩惠……可是一定是军代表不知道咱们家和晓波堂叔的关系,要是知道了,咱们不更加遭殃才怪呢……上天保佑……”
罗丁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眼前人影晃动着,有时是祝平,有时是那个军代表,有时又是晓波……眼看祝平的影子就要和晓波叠在一起了,却又被一块巨大的牌子给遮住了……那是一块多么沉重的牌子啊,它勒在晓波的脖子上,垂在货车的车厢外,这些年来又紧紧地压在罗丁的心头上。
珍英又叹了一口气。
“五年……还有五年……多难熬的日子呀……”
罗丁突然间扭过头去望了一下珍英。
“你说什么?什么五年?什么还有五年?”
“丁儿,你不懂事,”珍英的声音变得很小很小的,“晓波堂叔被判了十年徒刑,他已经劳改了五年,接下来还有五年……”
“妈——”
罗丁不由得大声叫了起来。
从第二批开始,移民的队列便有锣鼓声欢送了。虽然从公布的名单上看,头几批都是有政治问题的,只不过是在顺序排列上有轻重缓急之分,但是因为被区分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和第一批的移民不同,接下来的便有一点上山下乡闹革命去的气氛了。其实离乡背井都是凄凄惨惨的,真正的革命派都尽量地退缩在城里待机,他们都知道什么运动都是虎头蛇尾,待到落实政策的时候,他们就万事大吉了。但是那些没有希望让自己撑到最后去的人只好强打起了笑容,在胸口上别上一朵光荣花,穿过一串又一串燃放的鞭炮去流落他乡了。
罗丁也像一件行李一样被装在货车的后厢。他背靠着那些从屋里捆绑着搬出来的杂七杂八的家当,最后望了一眼那个装满了童年的梦幻的院落。那部货车就停在操场旁一条刚好容得下一部货车开进来的路口,和另外几部也是用来运送移民的货车组成了一个队列。车队缓缓地开始移动的时候,围在车队周围的送行的干部和群众也都大声地欢呼起来。那欢声和骤然响起的锣鼓声鞭炮声混杂在一起,竟然也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场面。
这时候,罗丁看到有一道灼热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他是在麻木地瞧着四周的人群时和那道目光相碰的。他缓缓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当他又很麻木地把四周给瞧了一遍之后,他又碰上了那道目光。他同样缓缓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他的目光始终都是麻木的,无论是在和那道目光相碰的时候,还是在缓缓地移开的时候。他知道那道目光始终都在瞧着他,即便是他乘坐的货车已经渐渐地加快了速度。可是直到最后,他不但无法用任何一点表示去对那道目光说一声再见,他还在心里觉得十分诧异,他为什么被安排到第二批来接受这样的欢送,他是属于第一批的,他应该由民兵来押送,然后把他丢到与狼共舞的荒山里,让他受只有地狱里才有的罪。
八
终于,再也没有把自己给拴住的东西了。罗丁让自己整个的身心都投入到了深山密林中去,除了蓝天和绿叶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复存在了。当鹧鸪的叫声在近得不能再近的地方一阵一阵地鸣叫的时候,突然间罗丁也发出了一声长鸣,那声音吓得鹧鸪“扑——”地从草丛中腾空而起,刹那间大地有了一点点生气,而罗丁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的东西,有一股热的血。有时候,一条秤杆粗的大蛇突然间横在他的面前,他的神经也绷紧得几乎要裂断开来时,他却又看到那大蛇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它仍然像原先那样缓缓地爬行着,匍匐而去。于是他明白了,这里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世界,他和它们是一群擦肩而过的旅伴。这里的一切都有它既成的规矩,无论是动的还是静的它们都和平共处着,只有来自人间的他,残留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带着流放者的叛逆。
劳累也一点不给他承受不了的感觉。相反地,他拼命地干活,把身体里所有的热能都释放出来,然后倒在像牛棚一般的窝里,睡他个天昏地暗。梦里也只有深渊和峡谷,让你爬上爬下的危岩,一个人坠入雾中,一个人飘上云端。村里学大寨,农闲时开荒造田。穷山沟有自己的规矩,梯田是公家的,可开发出来的山地种出来的甘薯都是自家的。罗丁最喜欢干这个活。倒不在乎为了日后能多收几斗口粮,而是他能够满山遍野地跑,远远地离开人群。他把杂树伐倒,堆到一起去燃起篝火。开头那一堆枝叶老是点不着,把一盒火柴划掉了,只烧着了他一个黑不隆冬的脸蛋。这火要是烧不着,地也就开不出来。于是他从别处弄来了一大把干草和枯叶,并且把树枝和树叶给压得紧紧的。终于有了一团窜起的火舌,夹杂着呼呼的声响。那一霎间的快乐竟然燃起了他来到山里后的第一个笑容。随后火势便猛了,还有碎裂的爆响。罗丁有些慌张,抬头往四周望去。四周都是茂密的山林,腾起的火焰让罗丁觉得势头不对。他丢掉镢头,抡起一把带叶的树枝拼命地扑打着,直到那火焰被扑灭了,他仍然不敢停下手来,生怕那一堆冒烟的柴火死灰复燃。可是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看到把山火给扑灭的不是他,而是村里的修松和他的女儿修梅。
罗丁吓得面带土色。人证物证俱在,说不定是一桩破坏山林案。
“烧山先要开火路,还要看风向……”
修松说着,解开头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山火已经扑灭了,可罗丁却愈发紧张。
接着修松把地上的土抓起一把来在眼前看着。
“这块地开了也没用,种下去也只能长出拇指粗的地瓜,”说着他转身对修梅说道,“咱带他到那山去挖,那里的地肥了些……”
罗丁有点傻眼,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
修松把他寻到的一块沃土分出一角来给罗丁。他还教罗丁如何把石头垒在一起砌成梯田的墙角。有时候,他自己的活儿干完了,便把修梅给遣了过来,去帮罗丁的忙。于是,到了傍晚有时候可以看到两个扛着锄头的身影从深山老林里钻了出来。那锄头的一头捆着一堆柴火,一头吊着一只空下来的饭罐。转眼就要逝去的夕阳的余晖把那两个身影照在一级又一级的石板路上。夜幕也逐渐地拉开了。
“歇一会吧。”
修梅说道。
“不。”
罗丁咬紧了牙关。
“得歇了……”
修梅把担子卸下来,坐到了路旁的石头上。其实她并不感到那么吃力。随后罗丁也赶紧把自己的一挑靠到石壁上,然后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们在村头的路口分了手。这时候修梅在把担子掉了肩膀的当儿望了罗丁一眼。
如果再昏暗一点的话,那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修梅的那一眼成为了从重重地包裹着的夜幕中漏出来的两道微弱的光。
那两道光亮害得罗丁好苦。群山在一层一层地退却,溪流在一波一波地流逝,然后是小巷的砌墙,小河上的石桥……一切都像电影镜头一般急剧地倒转着。他原来以为什么都消失了,所有的东西连同他的记忆都被他给埋葬掉了。他自己也成了啼叫一声的鹧鸪、匍匐爬行的大蛇……可是没想到那么轻易的,一个挑着柴火的山村姑娘在暮色中的一个眼色,竟然“哗——”的一声撕开了把他心中的伤口给捂住的那一条绷带。
第二天,他把镢头扛回了他原来烧出山火的那个山头,他要去挖那块荒瘠的收成无望的山地。他抡一下锄头,砸在一块石头上,溅出了火花。定睛一看,他看到了那一道目光。那目光短暂得和溅出的火花一样,大概也只有零点零零零几秒吧。他赶紧闭上了眼睛。可他的眼前又泛起一团红色的光亮,那既像是透过枝叶间的阳光,又像是一块飘起来的红绸巾。那红绸巾在金色的阳光中熠熠发亮……这时候,一块松动的石头从坡上滚下来砸住了他,他的眼前溅起了火星,那火星又像是从那块红绸巾上迸发出来的似的……
“罗丁!罗丁!”
他听见有人在大声地唤他。他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修松和修梅,他还看到他已不是躺在他原来抡着镢头的地方。接着他又看到了修梅的手里有一块烤热的地瓜和一碗清冽的泉水。他感到害怕,想爬起来,但是又没力气。
从那以后,修松用贫下中农才有的负责监督改造的权力把罗丁给“看管”了起来。他们父女开出的地有一部分让给了罗丁。归到罗丁名下的那部分实际上已经开好了,只让罗丁松了松土壤,锄掉一层草皮。
可是那一切并不是白白给他的。有一次,修松对他说:
“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书,可她连斗大的字都识不了几个,你教她吧!”
于是,深山老林里有了一个课堂。上课的时间是开荒休息的时候,地点是在岩石上或是小溪旁,折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那便是黑板和教鞭,一本毛主席语录便是唯一的教科书。
“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