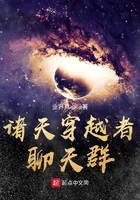闷热天,热而生燥,燥而生火。在燥火的刺激下,思维异常的人很难觉察到别人的异常思维。
早晨上课的铃响了,6301班的同学已经习惯了铃声响后都向123男生宿舍集中。小小的房间里,四张架子床的上下七个铺位,挤坐了三十多个人。每个人都是个小火炉,每个人也都在接受着别人释放的热量。桂小芹坐在门边的角落里,不住地擦汗,默默地低着头,等待大家继续批判。不料,何法娃按老哈的指示,对大家说:“今天上午是围绕着海队长的报告务虚,谈体会,提高思想认识。至今还有一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表态,还不知道他们对党是啥态度,对阶级敌人的进攻是啥态度。”话说完后,又走到桂小芹跟前说,“你回去写检讨,准备下次会议的发言。老哈让我转告你,检讨要有具体内容,有新意,要触及灵魂,深挖根源。”
桂小芹慢慢抬头,疲惫的双眼中显现出茫然无措和惶恐,她恳求道:“我心里很乱,能不能让我先到操场上走走,然后再回宿舍写?”
何法娃停顿片刻,板着陶土色的面孔严厉地说:“可以!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按照老哈对你的要求检讨。”桂小芹离开后,何法娃回转身,放缓了口气又对周伊波、顾衣锦、牟成天和韦保名说,“你们四个人也不要在这里开会了,老哈让你们到他宿舍去。”
周伊波跟着顾衣锦、牟成天和韦保名出门,四个人一阵风似地往2号楼疾走。
周伊波和三个领导小组成员一起被老哈叫去,在班上同学眼里,工作队又恢复了对周伊波的信任,黄山芸颇感欣慰。
何法娃按照老哈的安排,把整理好的文件和报纸放在桌子上,一张一张读着,并结合海队长的报告,加上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他读累了,把文件交到孙雅的手里。孙雅念了一段后,不耐烦地又把报纸塞给了华美银,让传着念,表示出对这种务虚方式很厌倦。
桂小芹从123宿舍里出来往楼外走,在楼道里她听到了从几个房门里传出此起彼伏的怒吼。当她站到楼门口时,听到楼上二层、三层也是一片喊叫声。她快走几步越过路道,走向操场的远处,让人心碎的怪声在身后逐渐减弱。她在南墙边散漫地挪着沉重的脚步,心里悔恨不迭,“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孙雅那样一眼就看出写大字报的人和五七年的****一样呢?自己虽然没有说过‘变天’,但对于校园里突然出现的大字报高潮,确确实实判断它是革命的,自己的心情确实激动;确确实实认为写‘一条黑线’大字报的人,出发点还是为了搞好运动,自己对大字报的观点,确确实实是赞同的。正因为这样,自己才会盲目表态,才会不自觉地站到了阶级敌人一边。归根结底是家庭留下的烙印太深,思想没有改造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真是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啊!”她预感到自己可能被定为反动学生,学校里已经不乏先例。如果这样,不但上不成学了,而且很有可能去坐牢,这一辈子就全完了。她眼眶中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苦思冥想着,“哪怕有一丁点儿补救的办法也好!”她转身慢慢地往回走,准备回去认真地写检讨。
老哈听见有人敲门,微笑着把门拉开,和顾衣锦、牟成天、韦保名握手,待到了周伊波跟前,他收敛了笑容,只是点点头。然后,他提了个方凳,放在屋子中间,严肃地对周伊波说:“你坐在这里!”又指指桌子侧面的座椅对顾衣锦说,“你在这里记录!”转身对牟成天和韦保名说,“你们二位坐床上,喝水自己倒!”他自己坐在了桌子后面,面对着周伊波。
在他们几个说话时,周伊波默默地坐着,没有再和任何人说什么。他已经感觉到房内气氛的严峻和凝重,意识到老哈不但没有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而且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他的对立面,划入了另册;同时进门的三位同学,都是老哈依靠的对象。
老哈坐下后,先无声息地用眼睛狠劲地瞪了周伊波一阵。周伊波感受到了从老哈两道寒光中传递出的威慑力。他刚躲避过老哈的视线,就听见他带着冷笑、慢条斯理地问道:“周伊波,听说你还写诗是不是?”
“很少写,也写不好。”周伊波迷惑不解地抬头把老哈看了一眼,回了一句。
“你是不是在诗里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老哈提高了声调追问。
周伊波一听就火了:“你听谁说的?是谁这么血口喷人?”他盯着老哈等着他的回答。老哈回头看看坐在床上的牟成天和韦保名,韦保名紧张地拖着娘娘腔说:“你们宿舍的人
看见你本子里写着。”
顾衣锦放下笔,对韦保名说:“说清楚点,我们宿舍里还有四个人呢?”在他看来偷看别人的日记是很不道德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老哈让他坐在周伊波对面,本来他就不自在,不觉得有光荣感,现在又让他不明不白地充当告密者的角色,实在觉得窝囊,不得不开口。
“反正有人看到了……就在抽屉里……本子上写着,记得有,‘云蔽日,雷声狂,暴雨……不胜防。’”韦保名被顾衣锦逼问,结结巴巴地答道。
“还有两句‘叹大地深情永在,怨天气变幻无常’。”牟成天在韦保名答话时已经把袁凤梧告诉他俩的“反动诗句”想完全了,他干咳了两声,利索地补充道。
“你要不要再去看看?是写春游的,写天气的。有些人可真有想像力,既无聊又无耻”周伊波不满地对着老哈问了一句,就又轻蔑地把目光转向缺少底气的牟成天和韦保名。
老哈听不出道道,看看身边几个人,没有谁敢在周伊波当面坚持、硬说这几句诗就是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老哈出师不利,脸已经胀得彤红。突然间,他从木椅上站立起来,拿着空茶缸在桌子上使劲地砸了两下,怒吼道:“周伊波,你看着我!老实交待,你和黄山芸是什么关系?”
周伊波不防老哈会发出这么狰狞的声音,惊了一跳,再抬头看时,只见他怒目圆睁,满脸的肌肉抽动着,像是个赤膊上阵的武士,也像是和自己打过架的吉丹,如果不是吉丹,可能也是吉丹的哥哥,他已经完全没有在班上初次露脸时做作出来的书生样子。
周伊波在中学就见过老师向调皮学生吼叫,自己也因为和吉丹打架挨过严厉批评。更何况,从小在家里经常挨揍,父亲比老哈厉害多了。所以吃惊过后,他很快镇静下来,回答问题没有慌乱:
“同学关系,团支部安排我和她联系,做她的联系人。”
“你们年级田雨书记,早就提醒过你和苏莘莘,让你们留心那两个女生。田书记的话苏莘莘听了,她和黄山芸保持距离。可是你还要当她的联系人,和她保持密切关系,甚至违反校规谈恋爱。是你改造她,还是她改造你?”
“当她的联系人,是支部让黄山芸找我的。田雨书记说的也不一定全对,难道有政策规定,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不能接触?”
“你还狡辩是不是?你对贫下中农子弟也这么热情?黄山芸想拉你下水,她一拉,你就下?我们是看你陷得不深,知道你的一贯表现和家庭出身还可以,所以,才不想把你放在群众面前轰,更不想把你推出去,是想挽救你。你要知道好歹,先把态度放端正,然后再回答我的问题。”老哈的话语忽软忽硬。
“我已经回答过了。”周伊波也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你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给你脸你不要!你必须老实交待,她在你跟前说过什么反动话?你老实交待!”老哈出乎意料地骂了周伊波一句,又拿着空茶缸在桌子上使劲地敲击,顾衣锦无法再记录。
“工作队员怎么能骂人?这么野蛮!”周伊波抬起头质问老哈。
“别说骂你,还想打你呢!你不只是包庇黄山芸,还有桂小芹、马夫、张信平、齐子长、宋婵婵等等,凡是那些家庭有问题的人,你都和他们拉扯得很紧,你什么意思?”老哈站在桌子后边先伸伸手臂,像是真要打人的样子,接着继续声色俱厉地敲打桌子。
周伊波知道,在几个同学面前,老哈只是过嘴瘾。当然,即使他打过来,自己也不怕。虽然没有他壮实,也一定敢还手。而且周伊波相信,那几个同学即使不拉架,也不会帮老哈。在周伊波心里,总以十五岁入团,一直当班干部,具有“五爱”品质,受老师器重、受同学拥护而自豪,何曾受过这种政治歧视和屈辱?他还自信“懂政策”,因为熟读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曾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4年末,在学生大饭堂,直接听过中央来的姚浜同志讲话。他清楚记得,那时姚浜就批评过“逼供信”,说这种所谓“经验”是违反中央政策的。他沉默了一阵,带着蔑视的口气说:“你少来这一套,大学不是农村!”
老哈没有再敲桌子,他拿起茶缸起身倒水,以舒缓绷紧的神经。
牟成天和韦保名想配合工作队,从周伊波这里得到些“原始材料”。但他们没有想到老哈以这种方式和周伊波谈话。在一个班上近三年相处,他们知道周伊波是个“顺毛驴”、“倔驴”,吃软不吃硬。老哈这样做绝对是下策,方法不对路。韦保名像饿扁了肚子一样,有气无力地以固有的娘娘腔劝道:“伊波,老哈也是关心你,想拉你一把,对你和对她们那些人不一样。你向工作队交待了,就没有事了。”
入大学后,周伊波一直觉得韦保名不像男人,很少答理他。
“伊波说吧,嘿嘿!你帮助老哈揭开咱班阶级斗争的盖子,对班上今后的文化革命相当重要。你对班上情况掌握得多,今天主要想从你这里了解黄山芸的情况。老哈对你期望值挺高,嘿嘿!”牟成天长得很浑实,声音很粗,带点呼噜,说话时常夹着短促的干笑。
顾衣锦一直低着头记录,他表面上不敢怒也不敢言,而心里却为周伊波抱不平。
“我给你提示一下,有人揭发你,你和黄山芸在一次英语课上,和历史反革命分子沙蹈矩勾结在一起,用‘狼和小羊’的寓言,来影射攻击党的政策;你还在《矛盾论》学习讨论时,为黄山芸的反动观点辩护。你不仅给她当联系人,而且还当她的保护伞。我今天只向你提示这点政治问题,你想好了再回答。你俩相好也罢,密切也罢,先把生活作风问题放到一边。我给你个机会,希望你不要错过。”老哈喝足了水,喘息了片刻,领会了牟成天和韦保名对他的暗示,转换成和缓的口气对周伊波说。
“老哈不是让你现在就回答他,是让你回去想想。”韦保名怕周伊波没有听懂,帮助解释老哈说话的意思。
周伊波仍然不答理这两个同学,他觉得不屑和他们说话。
“我今天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黄山芸的严重政治问题。她的问题你不是不清楚,而是缺乏觉悟和勇气站出来揭发。你只有老老实实交待出来,才能和她划清界限。党和组织要求你不要和她再拉在一起。你回去好好想,想好了写出来。要干条条,要干干的、一定不要拖泥带水,只要是干的,巴掌大的纸写满就可以了。最后再叮咛你一句,今天的谈话不准给任何人透风,如果传出去,你要负全部责任。”老哈在向周伊波发出最后通牒和威胁时,嗓子已经哑了。可是周伊波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睛一会儿看看脚下,一会儿看看天花板。这让老哈觉得像是他在农校踢球时,一脚踢到了石头上。
“你先走吧!”老哈对周伊波命令道。一说完,他就倦怠地靠在椅子上,把头仰向后方,显出沮丧和痛苦的样子。
周伊波刚走出2号楼门,就听到每天广播三遍的革命歌曲:“工农兵心最红,革命路上打先锋……”这是午饭的开始曲,也是结束曲。可是此时此刻周伊波觉得这曲子让他没有食欲,真恨不得把那些大喇叭都砸掉。他浑身已经湿透,心情十分烦闷和压抑。
一走进饭堂北门,他一眼就扫见黄山芸仍然站在东门边的角落处用餐。她正朝北门口张望着,俩人的视线碰到了一起。周伊波立即走过去,急促地对她说,“如果让你谈问题,没有的事绝对不要乱说,不要给自己拦事儿。最近咱们不能接触!”说完就匆匆离开。黄山芸还想多问几句,没等她张开嘴,周伊波就走远了。黄山芸很想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候,能约着周伊波聊聊。可是,她不知道周伊波为什么变得对她不耐烦,说不到两句话就躲开了。她相信周伊波不是那种势利小人,更不会落井下石,也敢担当。可是,为什么工作队刚把他重用一次,他就连话都不愿和她说了?她手里拿着剩半碗菜的搪瓷碗,对着墙壁黯然神伤,脑海里浮出了一句话,“困难见真情,路遥知马力。”
周伊波端着饭碗从饭堂出来回宿舍,瞥见老哈和牟成天、韦保名、顾衣锦相伴相随从楼里出来。周伊波走进118宿舍,把饭碗一放到桌上,就转身出门径直走向李有志老师的办公室,见朱勇实老师和工作队分队长老白也在那里。他没有管他们在说什么,就站在那里对着李有志老师愤怒地嚷嚷:“工作队的老哈,凭什么逼着我交待问题?他把我叫去关起门来拍桌子打板凳,还骂我‘给脸不要脸’。”
李有志老师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能推断出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再问周伊波什么,就转过脸对朱勇实说:“老朱,周伊波可是个好娃,你说是不是?”
“他周伊波我了解,没嘛瘩!”朱勇实担任了年级****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成了李有志的领导,不过俩人素来关系良好。
分队长老白笑着说:“这次运动可没有划框框、定调调,可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开始底子不清,得摸摸!”
“摸,也得有根据,更不能骂人!”周伊波不服气地反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