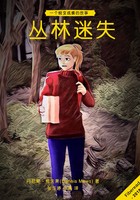孙雅,唐韶、韦保名和华美银相继发言表态,拥护工作队两位队长的讲话,批判‘一小撮坏人’恶毒攻击党的反动言论。他们发言之后,桂小芹要求发言。她照例先说了海队长报告的重大意义,如何让自己澄清了很多糊涂观念等等,然后又结合实际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了平时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深,近来对文化革命感到迷茫等等缺点。
不等桂小芹说完,孙雅就打断她的话,出其不意地说道:“你哪里是迷茫啊!你心里十分清楚,你是认为你们的机会到了。既然你跳了出来,那就先说说你6月3号晚上,从外边回到宿舍,喊叫了些什么?”
桂小芹像是被人从后边打了一闷棍,看了看孙雅愤怒的面容,紧张得身体开始发抖。周伊波从中学开始认识孙雅以来,见过她多次变脸,但从来没见过她变得这么迅疾,这么狰狞。黄山芸吓得不敢抬头。会场上,除过桂小芹头顶架子床上的几个人外,都把目光聚集在她脸上,屏着气静等她的回答。
桂小芹嗫嚅道:“我说让你去看大字报!”
“你不敢承认了?我帮你回忆,你说‘现在外边天都变了!’对不对?你心里若不是总想着变天,怎么能喊出这样的话?”孙雅死死地盯着桂小芹,反问的语调非常肯定,让人感觉桂小芹必须回答“是”。
桂小芹的确被孙雅打晕了,脑子一片空白。她什么话都回不上来,只觉得委屈,眼睛里开始闪出泪花。在几个人“赶快说呀”、“老实交待”的吼声中,她把头低下去,仔细想了想,又抬起头恳切地说:“孙雅,你肯定没有听清楚,当时乔藿芬和宋婵婵都在,我是说‘校门那边大字报贴满了,路上明晃晃的,天都好像亮了。’让你们赶快去看。”
“你的意思就是外边天都变了!”乔藿芬含糊其词地对孙雅表示支持。
孙雅对着宋婵婵问:“你从外边进来时,她还对你说了,你记得吧?”
“我回来迟了,也累了,她让我去看大字报,我没去。其它的,没听见。”宋婵婵把脸也板得很平,她不愿落井下石。
孙雅一口咬定桂小芹:“你就是说‘天都变了’!”
这几天,老哈已经按照工作队的要求和自己在社教工作团的经验,进行了“扎根串联”、“秘密谈话”、“摸查阶级队伍状况”、“确定依靠对象、争取对象、孤立瓦解对象和重点打击对象”,桂小芹属于孤立瓦解对象。老哈声色俱厉,一改初始的拘谨、谦和的神态,问道:“两个人都证明你就是这样说的,你还能抵赖掉吗?”
“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那样说的吧。但我请老哈和同学们相信,我绝对没有想变天的思想。”桂小芹对自己说过的准确字句,已经不敢肯定。但她为自己的本意辩解,不希望大家曲解。
“你还在狡辩,你就是盼着资本主义复辟嘛!”唐韶阻断桂小芹辩解,武断地喊叫起来。
苌安全前一天才听韦保名说了一个内部消息:“工作队只能把苌安全列入‘争取对象’,因为平时和周伊波‘关系密切’,与黄山芸、桂小芹接触比其他人多。”这一内部消息让他感到失落。他决心重新站队,在关键时刻表态,希望经过考验,能早日被工作队和领导小组纳入“依靠对象”。于是,他接着唐韶的话,用不太灵便的舌头诠释着“天都变了”这一浅显比喻的含义:“天变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夹着尾巴逃走了,又竖起尾巴回来了,是不是?你们就可以反攻倒算了,是不是?”他说完后,看看老哈,老哈并没有对他的话做出反应。
唐韶和苌安全的话,就象锥子一样扎在桂小芹身上。她不明白,唐韶曾是自己的入团联系人,自己平素向他多次暴露“活思想”,汇报家庭情况,谈对周围发生重要问题的看法,在春节期间一起“学雷锋”做好事,为什么还会误解自己?苌安全平时多次主动和自己接近,向自己示好,可他为什么也跟着起哄,歪曲自己的本意?她没有时间细想到底为什么。
孙雅突然又暴出了冷门:“你不仅自己散布反动言论,而且还对恶毒对党攻击的人表示同情,和某些人串联在一起,为她的反动思想开脱。你自己老实交待吧,不要让别人再揭发了。”她看桂小芹低头哭泣,又不耐烦地怒斥道,“不要流你那鳄鱼的眼泪了,你在女厕所外边和向红艳、黄山芸都说了些什么?”
桂小芹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她感到自己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该说什么。
何法娃脸上带着狡黠,先看看孙雅,又瞟了一眼黄山芸,以舒缓的语调说:“你要是不说,那就让黄山芸替你说。”
黄山芸在孙雅向桂小芹发问时,异常惊恐。以前,她虽然在宿舍里听赵春碧说过三班批判李紫丰的场面,但因为不是自己班上的事,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并不在意。而这次,她没有想到,一起朝夕相处了近三年、一起温馨快乐地参加多次集体活动的同学,怎么会反目为仇?怎么有这么浓烈的仇恨,就像上了战场?为什么盯上一个人,就得让她受煎熬,非得有个你死我活不可?她的心跳,渐渐地缓了下来,但两个耳边还是嗡嗡作响。她没有听清大家对桂小芹吼叫什么,只是觉得有人对桂小芹的话在无限上纲。她无力去替桂小芹辩解,平时就有人把她俩的友谊往“阶级感情”上拉,怕越帮越槽,把事情再搞复杂了。她下决心,坚守周伊波转告她的那个原则,“多听,少说”。可是,新任****组长的何法娃还是点了她的名。
她不得不发言,不仅是表态,而且也必须涉及到孙雅所说的事儿:“我觉得,我是把这次文化革命,当成学习******思想、继续改造自己的机会。我知道桂小芹起初的想法也是这样,当然,她后来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没有发言权。孙雅提到的几个人在厕所门口说话的事,是向红艳避开赵春碧提醒我们,要和她划清界限,告诉我们‘赵春碧在‘一条黑线’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工作队把这张大字报都定性了,谁还能表示同情?当然,我在宿舍里见赵春碧病了的样子,还劝她吃饭,劝她去看病,给她倒过开水,算是同情她吧!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事。”
“你少罗嗦!我不是让你在这里为桂小芹辩解,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是问你,桂小芹给你说了啥?”何法娃以审判的口气质问道。
“我说过了,是向红艳给我俩说话,桂小芹听罢就走开了。”黄山芸平静地答道。
“我问过向红艳,她说,桂小芹为赵春碧辩护,你还为她打圆场?”孙雅把向红艳抬了出来,以表明她问的话是有来头的,逼着黄山芸再提供桂小芹同情赵春碧的证据。
“那你让向红艳来作证吧。”黄山芸冷冷地对着孙雅说了一句,噎得孙雅没有再说什么。
“现在,我们还是围绕桂小芹叫嚣‘变天,的反动言论,继续批判!同时要继续深挖隐藏得更深的、更狡猾的家伙!”何法娃先和老哈耳语了几句,又适时地引导着会议的走向。
“桂小芹,你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狂妄地叫嚣‘世道变了’,你心里想的就是******反攻大陆。班里还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早等不及了。你们****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欲盖弥彰!”华美银经常在多种场合,述说自己为革命前辈献血的英雄行为,表达自己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她也经常背地里称呼出身不好的同学为“那些地主、反革命的孝子贤孙!”这一次发言,她更是觉得要爱憎分明、是非界限清楚,要能表现出自己阶级感情的深度、阶级觉悟的高度。
华美银的话对桂小芹像是霹雳灌耳,又像是从天而降的冰雹砸在身上,她懵了。
黄山芸能听出来华美银话中有话,坐在那里头上阵阵冒汗,心跳加速。岂止是黄山芸,就连马夫、张信平、齐子长、武思逸、宋婵婵都象是患了感冒,身上发紧。
从几个人的发言中,顾衣锦听清楚了桂小芹说的话。作为新任命的班****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表明态度和立场,他不紧不慢地说:“自己说过的话,说了就要敢承担,错了就要改正,不要坚持错误!”
苏莘莘启发桂小芹追寻思想根源,表现出前任团支书的思想工作素养和沉着态度:“你虽然也是在党培养教育下长大的,但是在你们那样的家庭中,一定会受到潜移默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错误的思想。所以,你应该从阶级感情和家庭影响方面,找找根源。”
“桂小芹,你的反革命老子被镇压了,你是什么态度?你家里人是什么态度?还有你周围一些人的问题,你都没有向组织认真交待过,你让我当你的联系人,可你什么都不谈。到了现在,你还不交待,怎么划清界限?怎么能不走邪路?你只有把家庭给你的反动衣钵脱掉,才能脱胎换骨!”唐韶又一次发言,以知根知底的样子诱导着桂小芹。
老哈看了周伊波两三次,眼神里带着期待和不满。而周伊波觉得,从老哈眼神里传递出的不仅是不满,而且是敌意。他对于自己被排除在领导小组之外已经顿悟,早看出来何法娃、唐韶自私,孙雅心眼儿偏狭甚至心术不正,他们很可能去老哈那里告过黑状。但他确实没有想到老哈竟然能看上这些人,也没有想到他们一被看上就这么蛮横。他憋着劲,就是不发言。
老哈又狠狠地打量了一次桂小芹,挥动着手里的自来水笔,用权威性的语调命令道:“你的‘变天’思想,不是无缘无故的。你要好好从根子上找找原因,问问源头在哪里,把脑子好好挖挖,把见不得人的东西,统统都暴露出来,老实交待出来,才是唯一出路。”他说完后,会场上寂静无声,没有发过言的人都低着头。他把视线还是落在了周伊波的身上,见周伊波仍然没有发言的意思。他憋不住了,还是点了名,“周伊波,你以前是班长,了解情况多。听说,她们有话愿意对你讲,你要有个态度!”
“古人有首诗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到头来,豆子煮烂了,豆萁也化成了灰烬。”周伊波一张嘴,就背诵了几句古诗,背完只解释了一句,就停止了发言。老哈没有听懂,仍然不明白周伊波是什么态度。但是,班上大部分人都能听懂。
何法娃看看老哈迷惑不解的样子,越俎代庖地质问周伊波:“你在这儿读这黑诗,什么意思?谁和谁是同根生?”
“咱们大家呀,我和你,你和大家,咱们不都是吃祖国母亲的奶长大的?不是同根生吗?”周伊波反问何法娃道。
“我问你,桂小芹和你是不是同根生?”何法娃继续问道。
周伊波不正面回答他,又反问道:“她是不是吃祖国母亲的奶长大的?”
袁凤梧抢先帮助何法娃回答:“她是吃她爸、她妈的毒奶长大的!”他的话立即引起全班人哈哈大笑。
“怎么这么不严肃?周伊波,你在这里胡扯些什么?”老哈对着周伊波发脾气。
“你听听,是谁说话不严肃,是谁在逗大家发笑?”周伊波不服地反问道。
老哈不愿意和周伊波纠缠,把脸又转向主要斗争对象,呵斥道:“桂小芹,你休想蒙混过关!刚才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必须记住要求你的那几点,只有自己救自己。不然,你是不会得到组织和群众谅解的。你回去想想,检讨要有实质内容,下次会上见。”
桂小芹感觉6301班的三十几个人,合成了一个怒目圆睁的巨人,以不可抗拒之势,把她打翻在地。她虽然极端委屈,却也只有求饶,认输。不然,这个巨人就会再踏上一只大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她一直拿着笔记本,仔细地记着,生怕漏掉了什么重要的话。
散会了,每个人都是一头一脸的汗,不过有几个人的汗和大家不同,是凉的。
这天傍晚,229宿舍里的人都去吃晚饭了,桂小芹独自躺在床上流泪。于景从外边进来,走到床头,和平时一样,轻声叫道:
“桂小芹,走,打饭去。”
“我吃不下,没有胃口。”桂小芹声音颤抖着回答。
“走吧,走吧!无论有什么事,饭总要吃!”于景一遍遍地催促,声调平和,带着关切。
桂小芹忽然委屈地大声地哭叫起来:“我没有****呀!我没有****!”整个楼道似乎都能听见她的哭叫声,几个外班的同学,站在门口观望。
桂小芹起身,把脸上的头发向后捋了两把,背对着门望着窗外,只见一阵不大的旋风,裹着灰尘向前旋着,一片纸飞起来,接着又飞起了几片,无助地在半空中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