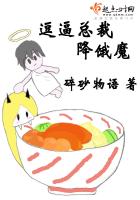如今的写作,几乎成了传媒信息的附属品,偏安一隅,随时等待着潮流的发落。所谓的纯文学的主流文化,在市场面前的容颜已十分难看。要么随波逐流,读者要什么,你就写什么,从出版商发行商数,换取银子花。要么坚守崇高,一股道走到黑,或者有名声又有钱,或者就饿死了。作为市场的大多数读者,受到传媒的诱导,成了传媒不用付费的传声筒,某某作家如何,某某书畅销,便买一本瞧瞧。仔细读了没有,真正读懂了没有,则是另一码事。浮躁的时尚像发酵的沃土,滋长着写作者灵感的杂草,也开放着读书人貌似鲜艳的花朵。纯文学的崇高,早已被市场的宠儿当做笑料。所谓的文化经典,也只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珍藏起来,时不时还有断奶的危机。何况崇高的经典也在变味,已经从神圣的殿堂滑入市井里弄,与世俗难分难解。被排斥在作家群体之外的自由撰稿人,却被世界名人大辞典所标榜,泡沫的文学大师随处可遇。写作在变成另一种机制下的职qk,越活越鲜烈。天赋人权亦天赋用文字说话的权力,似乎做文章出书是任何人都可以玩弄的把戏。作家的垄断消失了,非作家的精神产品源源不断地充斥着市场,皆冠以写作的名义。
文化市场的拓展与繁荣,尾随的是时代的精神处境,不免要频频献媚于商品世界。曾经用笔呼唤来的阳光灿烂的春天,有欢笑也有哭泣,有风景也有陷阱。依赖于传统文化积淀的写作人,面对眼花缭乱的商品市场和网络幻景,显得笨拙而弱智,大叹今不如昨。淘汰是必然的,也是残酷的,同时也给真正创造经典的少之又少的大师们提供了机遇。大智若愚,无言的大师们正躲藏于喧嚣的背后,窃笑着磨砺宝剑。有急功近利的成功者,也有大器晚成的巨匠,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作向来有体例的划分,应用文字是一些大路货,而艺术的语言却是稀物。物稀为贵,有了文野雅俗之别。人生在一定意义上是模仿艺术的,从而有了高贵与低贱的分类。所谓快餐文化和娱乐文字,填写了纯粹艺术之外的空白,随手捡起,有意无意地浏览片刻即随手丢失。它的直接性和实用性以及感官愉悦,代替不了滋养情感与灵魂的作品,如同饮料不可取代美酒一样。假如忍耐不了卜年磨一剑的寂寞,那干脆剪一把纸的或锯一把木的剑器,也许会唬人。
问题却不在于这层大道理,闭门思过,面壁修行,一昧地自我感觉良好,只能孤芳自赏而已。也许你已属于过去了的年代,唱一首低回哀婉的挽歌,追念逝去的时光,也算找到了位置。潮流此起彼伏,一泻千里,你已经缺乏充沛的精力和敏锐的思维,弄潮于波谷浪山。你需要时常步出书斋,抖落经卷的霉味,感受阳光的活力与风的调侃,然后回到自己的内心里去。落寞不等于颓败,且让经验的酒糟酝酿着,让想象的羽翼飞翔,让知识的窗户敞亮洞开,你就守住了写作的自信。
将文字当做石头一样搬运的写作者,愈来愈承受着体力与心理的煎熬,抑或壮烈,抑或悲哀。游戏依然进行,捧杀与棒杀兼之,炒作兵不厌诈,对骂此起彼伏,好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名乎利乎。宽泛意义上的写作,可以有富翁横空出世,却并不等于大师的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发大财的人寥若晨星。卡夫卡没做到,李白杜甫东坡雪芹没做到,大作家的福禄寿古来难全。也许轻松心态的写作,会赢得人生的潇洒。而雇用写作的枪手,只是一种谋生方式。玩文学,说到底也是个玩儿,据悉这是个玩的时代,看谁玩得好。
《西安晚报》2001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