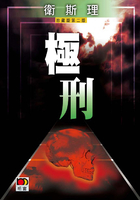“吹落了思乡的尘,却吹不去额头的纹,走完了天下的路,才想起了回家的门……”年的脚步越来越近,纷纷扬扬的雪花铺了一层又一层,腊月底,村庄处处漾溢着浓浓的香甜和喜庆,家家户户忙着煎炸糕点、杀鸡宰鸭、裱贴吉联……
漂泊愈久,思乡愈浓。千里迢迢自东莞抵达乡上,夜已深黑,四野灰茫茫的霜雪,让人恍若隔世。风砭人肌骨的冷,加班的中巴车上挤满了风尘满面返乡过年的游子。河龙街头几盏昏弱的路灯泛着凄迷的冷波,寒意凛凛,晚烊的几家小店透射出零星灯火。我戴着棉手套,冻得脖子直往衣领缩,街道两旁尽是脏污的残雪,空气中氤氲着凛冽的寒气。
卸下行囊,我赶紧奔进小店,家里电话不通,于是拨通近邻表姑家电话,让她过去转告父母。时值十点,天寒地冻,想必父母早已躲入了温暖的被窝。河龙街离家十里远,踩着迷蒙的星辰微光,坎坷泞泥中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往前探行。
土路泥泞湿滑,雪融后更加不堪,乡野一片混沌,灰扑扑地辨不清路面银花花的是雪还是水滩,踏下一脚,冷不丁溅起一溜浊泥,弄得鞋裤尽湿,懊丧不已。河龙路段地势平缓,属闽省辖区,我村的田畴大半在此,望着路边曾经劳作过的熟稔田地,对黑夜的恐惧稍稍有所消减。
泥泞坑洼的土路着实难走,肩上的行李累得我气喘。转眼走到亭子边,我心生惶恐,这亭子以前常有乞丐、流浪汉和癫佬窝居于此。我下意识地放轻脚步,惴惴不安地走着,两眼警惕的扫视着周遭的动静。
一路不安地摸黑走着,走了好久,终于抵达黄家山的坡脚下,我放落行李,平气歇肩。路旁草茎的霜雪泛着冷冷的银光。一路紧赶慢赶,累得周身融暖,寒气早已驱散。再往上走是九曲回环的八岭坡。八岭坡坑洼陡曲,旭日初露,远远地被它抛在了腰间,曾有客人惊呼:这真是比太阳还高的地方!土路两旁黑黝黝的松杉魅影森森,风一吹荡,树上冰凌哗啦碎落,让人惊心。虽然不大信鬼,但心中仍有几分害怕。儿时父辈们常加油添醋地讲各类鬼故事,说荒僻诡异的八岭坡常有飘忽不定的磷火出现,会追着独行的夜路人……
母亲咋还未到?我不敢再往前走了,心下甚急。暗忖,表姑接到电话,再冷她也会起床去告知母亲的。茫然间,远远闪过一线微弱的光晕,我心头一喜,苍茫阒寂的黝黑山野,灯火总能给人以温暖和亮堂。
约摸十分钟后,隐隐传来细微的呼喊,喊声由远及近。我竖耳细听,辨出是母亲的声音,激动万分,立马高声回应。一会,母亲昏黄的手电便照到了我跟前。
“这么夜了,也不晓得买把电筒,摸夜路多危险……”母亲心疼地嗔怪着,她头上围着暗绿色头巾,一脸兴奋。
父亲戴着一顶棕色棉帽,口里冒着热气,冻得咝咝呵呵,他耸着肩,脖子紧紧地缩在衣领里。母亲挪过我肩上的担子,父亲捋过我手上的行李。父亲略显老迈,因常年劳作,又喜烟酒,在刺骨的寒夜更是不停地咳嗽。多处路坡崖坎边的松杉被冰雪摧残,连根拔起,连同塌方一道横堵在马路上,将土路拦腰砸断。我们只得从横着的树身下屈穿过去,我挽着父亲,偶尔及时推抵一下脚下打滑的母亲。父亲将电筒一前一后地照探,我们在陡坡雪地上且行且滑,吃力地缓缓前行。
母亲侧过脸说:“刚才在山腰转弯处,我便让你父亲把电筒晃远一点,使你看到光后心里不会害怕,这么寒冻的夜,转来得这么晚……”母亲絮絮地说着。默默聆听着母亲的话语,心头顿时涌起一股幸福的暖流。
有位哲人说:“儿女是父母最伟大的作品,也是父母永远的骄傲。”父母对子女的爱早已深入骨髓,铭刻于心。父母将我们带到尘世,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将我们养育成人,他们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视野,殷殷地关切着儿女成长的每一步。
天寒地冻,万籁寂静的山野,母亲手中那盏昏黄的火光,照耀着我,温暖着我,也温暖了大地母亲那寂冷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