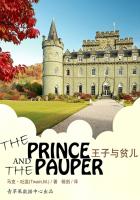自从县里引进了烟草种植,一贯闲散的乡民比以往要忙累许多。旧时,村里仅有少数村民零星种几株自享的黑烟,俗称老烟。将泛黄熟成的烟叶采摘回,搁在篱墙上晒得乌七八黑,然后封存于胶袋,再用厚柴刀切成烟丝,经年品啜。这种烟浓烈呛人,劲辣十足。引进的烤烟却要精耕细作,毫不含糊。为此,起初各乡镇还特意从外县聘请数名技术骨干,轮番前往各村言传身教。
那时打工潮还未涌到偏远的乡村,家家户户都搁着数个剩余劳动力,年复一年地春种秋收。自引进烟草种植后,大大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我乡地处闽赣之巅,山高水冷,向来只能种单季水稻。开始几年,烟叶产量较低,还严重影响到后季水稻的产量,出炉的烟叶也不够金黄抢眼,价格等级大打折扣。经过数年不断摸索和借鉴,后来县里又引进营养袋育种法,畦垅覆盖薄膜法,施底肥等科学有效方法,烟草终于获得色质优良,高产喜人。
春意拂面,百花争艳,随着气温陡升,畦棚内茸嫩的烟苗正幽幽滋长。此时的烟民最忙了,纷纷将禽舍的粪肥挑往田中打底肥。由三人一拉两扯,往畦上覆压保温薄膜,着力地将薄膜扯拽得紧绷稀薄,为着节省成本。施底肥的益处在于幼苗期不用淋施劲肥,幼期施肥较难掌控,稍不慎肥料就会烧伤白茸茸嫩乎乎的根系,致使烟苗滞长,重则萎败。
随着气温的陡升,植入田畦槽位的烟苗在薄膜内快速萌长,不久便绿乎乎地将薄膜萌挤得鼓鼓实实。烟民于是下田将薄膜撕开个小口子,把嫩叶细细的捋出棚外,让它经风雨历练,茁壮成长。白茫茫的田园泛出点点青绿。随着根系的蔓伸,当它们触到底肥时,加上雨露的恩泽,烟苗便拔节滋长。不消多久,田畴日渐葱茏,白茫茫的田园被蓬蓬勃勃翠绿阔大的烟叶所覆盖。
烟树长到一米高时,要进行人工打顶,以遏止它无谓疯长,徒耗养分。将未展舒的多余烟蕊剔除,一株烟树约预留十匹上好的烟叶。整株的烟叶全部张放时,隔三差五便要去烟田打烟孙(枝蔓)。刚开始种烟时,得勤耕细作方能提高烟叶的厚度与产量。后来,县里又引用浓稠艳黄的化学药剂,药剂释水后,只要用小壶嘴从烟树的顶端淋漓而下,以往隔三差五便肆意疯长的枝蔓从此销声匿迹,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科学就是不同凡响,大大减省了烟民无数心血和精力。
种烟的田块大都是低洼肥沃的田块,春夏雨水多,田垄里长期淤积着漫脚裸的烂泥浑水。每次下田作业,都会脏湿裤腿。摘烟时更是双手黏黄,头发及全身粘粘燥躁,十分不爽。烟民往往在收工时抓把烟树根部的泥土使劲搓手,回家后再用皂粉反复揉搓,却极难洗净。
烟叶渐次熟黄,烘烤时段即将来临。摘烟的最佳时间宜选在清晨露水莹莹或日斜黄昏时,日头热时烟叶萎奄是不能采摘的。每次摘回的烟叶一亩少则四担,盛产期间一次十多担。一时,大厅灶房,院前屋后,檐廊茅舍,目光所及,烟叶成山,等着乡邻夜饭后来帮忙用篾签串成一吊一吊。
家务已了,左邻右舍陆续拢来帮忙串烟叶,无需叫唤,大家互相帮衬,这几乎约定俗成。男女老幼散座在烟叶间,眼疾手快的往扁薄锋利的竹签上戳串烟叶,主人负责将待戳的烟叶分成青色、半黄和黄色等,再将串好的烟叶一吊一吊倒置摆放。篾签不好使的,只听得青脆烟梗啪啪的断裂声。这时主妇们便抽身来到灶前,手舞足蹈,擂泡起浓郁芳醇的擂麻茶,炒煮糕果食点等来感谢近邻。乡亲们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好生热闹。烟多时,主人拾掇完零乱的厅堂院落和杯盘碗盏,每每忙至午夜方能歇息。
烟叶装入烤房后,要经过变黄、升温、排湿、开天窗、地窗、烘烤、干筋等程序,约六天的周程。有时,这烤烟快下烤了,如逢天落大雨,那也得去摘烟(其实推迟一天也无妨)。这时最辛苦了,浑身透湿不说,田埂濡湿后又滑又烂,一不留神一个趔趄,连人带烟跌倒在风雨里。种植烟草,烟民肌骨不知要濡吸多少湿气水露。种田的农人,年轻时因洇润水湿太多,落下病根,老年时便出现风湿性关节炎、腰腿酸疼等各种病灶。
烤烟房约十二平米,内设四层。每层横着四条杉木横梁,地底是拐弯抹角散热的火管设施。每次卸完整烤烟叶,为不让热度过多散失(节省燃料),稍息片刻又要趁热装置下一烤。下烤时烟叶金黄酥脆,极易压碎,这时便全家出动,一个传一个,轻拿慎放。
下完烤后,再将昨晚串好的烟吊摆架在米余长的棍条上,一棍均摆串六七吊。房外的人不断将沉沉的棍条递传给房内的人装置。吊满的烟棍又湿又重,往头顶艰难举放密置,热烘烘的烤房内,装烟人早已汗如雨下,躁热难耐,实在热憋得窒息,便赶紧逃出门外大口喘歇。为降低成本,那时普遍烧柴,还得烧柴质硬劲的杂木,杉木的火力是断然不行的。
几年后,附近山里的大树和杨梅树被砍伐殆尽。烧柴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添柴,烤烟人夜里便躺在烤房近旁的临时床架上,以便随时添柴。烤房三五成群,大都挨在一起。一烤烟,往往要几家人合并方能装满。雨天里,烤烟的大人小孩便聊天玩牌,天晴时他们边烧火,边就近忙些家务,有时顺帮邻房添加柴火。上山砍柴时,驮湿重的柴禾最沉,砍回的柴被人们用一字大锯锯成一段段,再用锋利阔斧狠力劈开。
有时,几个烤烟人夜间结伙去田间捉青蛙,用来焖饭吃。青蛙焖饭十分鲜美,野味十足。有时烤烟人宰鸭下酒,酣然畅饮。烤烟时,一边生火还要不时爬上短梯察看温度计,以便掌控和及时调整火温和湿度。还得经常攀上热烘烘的顶层,推移天窗隔板,以调节温度。一些村民白天活计劳累,夜里烤烟时沉沉入睡,忘了填柴,一觉梦到天亮,醒后骇然失色,由于灶膛歇火跌温,导致房内蒸气下滴,落在烟叶上,灿黄的烟叶于是洇出许多豆大的麻点和污点,白白糟蹋了许多黄灿灿的好烟。更不幸的是,有些烤房在炙烤过程中,有烟吊从撑棍上失重脱落到火管上,由于开门巡查不及时,最终酿成火灾。烤房和烟叶于是化为灰烬,让人痛彻肺腑。
白天大家一边择烟一边生火,烤好的烟大致可分为上一、中二、中三、下四和乌烟等数个等级。乌烟属次品,烟草站是不收的,可以随意贱卖给烟贩子。整株烟全剐摘完后,乡民立马拔树剔根,犁田耙地,争分夺秒赶抢时令,赶种后季水稻。这时,往往全家忙得热火朝天,恨不得多生出一双手来。
将烤烟一束束择捆好,分等级叠摞,封存于干燥的屋隅或谷仓,再用薄膜覆严,以免被空气濡蚀腐坏。每年烟叶欲上市前,乡政府便会派干部下村蹲守。我村是赣闽交界,一里外便是褔建辖区,五里远便是福建乡镇。全乡有三个村与福建毗邻。岩岭乡政府为防止烟草外流,导致乡财政亏失,每年卖烟的数月间便派干部日夜驻守,直至闽赣双方烟草站收购截止,方宣告撤退驻守。
那时,邻省河龙乡的赋税比我村要轻得多。那时,我乡的村民宰杀一头猪,无论高矮胖瘦一律得收缴七十多元税收,这样直接导致许多村民不敢养猪。而相邻几里远的河龙村民卖猪却分文不收,乡里仅在街面上收取屠户少量检疫费。那时,烟草站可谓是个油肥的站点,收购烟叶时,难免有个别人员会降低等级,将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烟叶随意甩在各个等次。有时,福建的烟叶等价比我乡稍高,乡民便想方设法把上好的烟叶潜卖到福建。许多福建的烟贩子骑着摩托车,终日神情诡异地游弋在江西境内,与守烟干部玩起猫与老鼠的游戏。
乡干部每周两人轮番值守,选住在三叉路口的民舍。夜间放锁杉木哨卡。半夜,车辆一来便烦噪地摁响喇叭,“叭叭叭……”鸣声撕破村庄静谧的夜幕,惹得众犬群吠。酣梦中的人辗转呓语,讪讪嘟囔。喇叭鸣响,浅睡的干部悻悻然,于是披衣下床,手执电瓶上前查探一番。有时双方亦没好声气,怒目冷眼。偶有摩托车驰过,他们也会起身到阳台上照探……
闲极无聊时,他们便同村里一些游手好闲的村民搓响麻将。守烟期间,乡政府领导时常打探到一些风吹草动,然后火速布施搞突然袭击。众人午夜徒步数十里丛林山径,穿小路堵截烟贩,置毒蛇虫害和露湿于不顾……
一些偷运烟叶的村民有时不幸被逮,每每吓得唇舌打结,面如土色……
有些村民用摩托车载着烟叶去福建卖,被乡里知道后,不幸招来大麻烦……乡里马上派人前往做其思想工作,一些屡教不改的还会受到一定的处罚。种烟卖烟,市场与潜规则,演绎着一场场纷繁的烟事……
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时代飞速向前发展,故乡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机关单位人浮于事,新世纪之初,全国实行机构精减,响应上级“大城镇”建设的号召,全县的小乡镇纷纷精减缩并。岩岭乡政府亦兼并由高田镇直接管辖,仅设个岩岭管理区,如今,又缩为一个村了。乡粮管所等许多国营企事单位被取缔,“下岗”一词应运而生。乡政府及各国营单位临街的一排排公房全部改装卖给了各村乡民。
国家减免了农民的税收,并颁布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优惠政策。这是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真正地为农民带来了实惠。如今,农民不用再缴纳公粮、提留等赋税,还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抚今追昔,感慨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