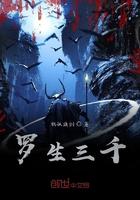晚上,为它照明的火炬和焰火,耀亮了半个北美大陆。
葬礼车载着林肯的遗体回到伊利诺伊州,大群民众夹道致哀。车子本身包着皱绸,火车头也和拉灵车的马一样,罩上一块点缀着银星的大黑毯。
火车慢腾腾地向北走,铁轨两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表情越来越悲哀。
火车到费城车站以前,先通过数英里密实的人墙,驶入市区。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街上。哀悼者的队伍由独立厅向外延伸了三英里长。他们一寸一寸向前挪动了十个钟头,只为了瞻仰林肯的遗容一秒钟。星期六半夜,厅门关了,哀悼者不肯离开,整夜留在原地,到了星期日凌晨三点,人潮更密了,甚至有些小伙子以十元出售他们所排到的位子。
士兵和警骑尽力维持交通顺畅,避免阻塞,几百名女性晕倒,曾参加盖茨堡战役的荣军奋力维持秩序,竟也累倒了。
丧礼预定在纽约举行,事前24小时,游览列车日夜不停地开进城,载来该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潮——旅社住满了,他们拥进私人住宅,冲到公园和轮船码头上。
第二天,16匹由黑人驾驭的白马,拉着灵车走上百老汇,伤心的女人,沿路抛花朵。后面传来“哗哗哗”的声音——那是16万送葬者手拿摇摆的旗帜,上面写着“啊,遗憾,亚伯拉罕——遗憾”……“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等名句。
50万群众互相扭打践踏,想参观长长的游行队伍。面向百老汇的二楼窗口,每一个座位要40美元租金,窗子都拿下来,以便尽量容纳观礼的人。
唱诗班穿着白色长袍站在街角唱圣诗,乐队边走边奏哀歌,100门大炮每隔一分钟就在城市上空回响一次。
群众在纽约市政厅的棺架边啜泣,很多人跟死者说话,有人想去摸他的面孔,有一个女人趁卫兵不注意的时候低头吻遗体。
星期二中午,当棺材合上以后,成千上万未能瞻仰遗容的人匆匆赶车西行,前往灵车将要逗留的另外几个地点。灵车未到春田镇以前,始终被丧钟和礼炮包围,白天通过长春藤和花朵做成的拱门,经过孩子们挥舞旗帜的山坡;晚上,为它照明的火炬和焰火,耀亮了半个北美大陆。
举国激动得发狂。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葬礼。到处有因过劳而崩溃的人。一位纽约青年用剃刀割断喉管,大叫:“我要去陪亚伯拉罕·林肯。”
暗杀发生48小时后,有个委员团从春田镇赶到华盛顿,恳求林肯太太将丈夫葬在他的家乡。起先她严厉拒绝。因为她自己很清楚,她在春田镇几乎没有朋友。虽然她有三个姐妹住在那儿,可是她讨厌其中的两位,又瞧不起另外一位,而且她对春田镇那个爱说闲话的小村庄充满轻蔑。
她对她的黑人裁缝说:“上帝!伊丽莎白,我永远不会回春田镇!”
所以她计划将林肯埋在芝加哥,或者放在国会议堂原先为乔治·华盛顿建造的坟墓里。
可是,禁不住大家七天的苦苦哀求,她终于同意将遗体送回春田镇。小镇筹募了一笔公共基金,买了一块有四条街廊的土地,州议会派人日夜挖掘,整理成一个墓园。
5月4日早晨,灵车终于进城了,墓园已经完工。数千位林肯的老友聚在一起正要举行仪式,林肯太太突然大发雷霆,推翻原定计划,不让遗体葬在已做好的坟墓里,而要下葬在两英里外树林中的橡岭公墓。
她决定的事不准打任何折扣,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否则,她就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把遗体带回华盛顿。
她反对的理由十分荒谬:坟墓建在春田镇镇中央的马瑟街,而林肯太太瞧不起马瑟家族。几年前,马瑟家的人曾惹她生气,现在,面对着丈夫的遗体,她仍不忘旧恨,不同意让林肯在马瑟家人沾染过的土地下安息。
这个女人对任何人心怀怨恨,和“将慈悲心广布天下”的丈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20多年:可是她的冥顽不灵,使她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改不了。
于是,11点钟,遗体被取了出来,搬到橡岭公墓的一个公共骨灰堂去。斗士乔·胡克骑着马在灵柩前开道,后面跟的是“老公鹿”,身上盖的红、白、蓝三色毯子上绣有“老亚伯的爱马”等字样。
“老公鹿”回到马厩,身上毯子早已经连一块碎片都找不到了;争夺纪念品的人把它剥得精光。他们又像秃鹰般地突袭灵柩,争先抢夺披棺布,直到士兵带着刺刀冲向他们才肯罢手。
暗杀事件发生后,林肯太太躺在白宫里哭了五个星期,日夜不肯离开闺房。这段时间,伊丽莎白·凯克莱一直守在她床边,凯克莱太太写道: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面——心碎的号哭,奇异的尖叫,恐怖的痉挛,发自灵魂深处的哀声。我用冷水为林肯太太洗头,尽力安抚她的情绪。
泰德跟母亲一样悲哀,可是母亲情绪失控的恐怖状吓得小男孩不敢做声。
泰德夜里听见母亲的哭声,常会穿着白色睡衣爬下床,走到母亲床边说:“别哭,妈妈。你哭我睡不着,爸爸很好,他到天堂去了。他在那边很快乐。他和上帝及威利哥哥在一起。别哭,妈妈,否则我也要哭了。”
由于各种原因,林肯的遗体曾被搬动了17次。今天棺材嵌在坟墓地板下六米深的一个钢铁和水泥大球里,那是在1901年9月26日放下去的。
开棺那天,人们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面孔。当时看到他的人都说他看起来好自然。他已经去世36年了,但是涂油师做得很好,除了脸色黑了一点,黑领结的一侧有点发霉,林肯看起来和生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