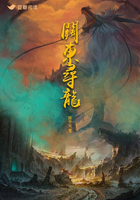大年五更胧胧月
堂屋南山
拴着个抿角大叫驴
贼去偷它
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就喊,瘸子就撵
一歇撵到千里县
碰见一颗金色豆
拧成绳,拴住他,送回来
拴到后院枣树上
上桑树,砍柳棍
打他一百榆木棍
扫腿一棍,打住脖筋
你若不信
扳起脚心看布淋
章柿又要去上学了。季瓷说,你想好,要上就当事上,要是不想上,趁早回来干活,还给家里添个劳力。你爷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干不动了。
章柿给爹娘保证,这次一定好好上学。
两年后,十七岁的章柿在白果集小学毕业,到县里去上初中。这时,章槐也在白果集小学快毕业了,章楝两三岁,满院子跑着玩。
会还是那么多,批了这个批那个,季瓷的舅家属于南边另一个县,定为地主,她那个活着的二舅也被到处游街批斗。当年这位二舅最喜欢村里人喊他二大,现在,这位二大整天灰不溜秋地到处挨批,弯着腰回到村里,人们在背后指着说,看,二大回来了,早先时拽得受不住,这会儿腰塌成这样。
季瓷在扫盲班学会了写字,能歪歪扭扭写出一家人的名字。
桃花一坐到夜校板凳上,屁股上就像扎了葛针,咋样坐都觉着不对,那些字在黑板上曲曲连连的,像虫子乱爬。还真是守信家说得对,世上没有读书好,世上没有读书难,这哪胜在地里干活得劲呀,这哪胜和四海半夜里往河滩里跑舒坦哩。桃花受不了这洋罪,终于在一个晚上从夜校扫盲班抬屁股走人了。
章四海一被批斗,再也不主动找她了,可她不答应,恨四海怎么就把她晾下了。有一天,她把正垂头丧气走着的章四海堵在村头的苞谷地边。
“咋了?把你斗昏了,想不起我了?”
“唉,我现在连个苞谷面饼子都给你拿不去了,家里叫分得光光的。”
“谁要你的东西?”桃花喊了一声,泪花就崩出来,火星子一样在脸上乱跑。“我跟你好是为着你那点东西吗?你忘了咱俩说的那些话了?”
章四海看看前后,又看看身边苞谷地:“站这儿说话不好吧,叫人看见又是罪。”桃花伸手拉他,进了苞谷地。两个人都深深地弯下腰,走呀走呀,直往苞谷地的深处去,他像当年一样气喘吁吁。“中啦中啦,再走就走那头儿去了。”桃花回过身,扑到他怀里,嘴急切地凑上来,带着火星子电闪子说:“我啥都不要你的,只要你跟我像以前那样,我有力气,我有地了,我能干活,我能养活你,你只记住一点,不得不理我,我要你还来这苞谷地里,你愿意不?你说,你愿意不?”章四海被桃花的烈焰烧得“噼噼啪啪”作响,忙不迭地说:“愿意,愿意,只要你不嫌弃,我死到你身上都愿意。”
“叫他们斗吧,叫他们批吧,咱俩就是好了,就是舒坦了,气死他们王八孙。”桃花说。
稍微大一些的村子都有扫盲班,白果集更别说了,中学里晚上灯火通明,旁边两个小庄子的人也来这里认字。退休回家的季瓷他爹又被请回来,担起了教乡亲们认字的任务。晚上喝罢汤他自己出门到白果中学,儿媳妇跟着村里的女人一起去,下课后,两人再和村上的男人女人一齐,过了颍河上的石桥,一路上大家说着话回家。季刘氏不在他教的那个班,不论是谁先下课几分钟,都在门口等着。
那晚,季先生下课后到另一个教室门口等,见人早就走空了,他有点奇怪,她咋自己先走了?回到家,他问季瓷娘,咋,小妮他娘先回来了?季瓷娘说,没回来呀,咦,是不是我没听见,叫我到后院看看去。一会儿,从后院回来,说,还真的没回来。老两口等了一会儿,见季刘氏低着头进屋,见了公公说:“哟,爹,你回来了。我下课后肚里不舒服,到茅子去了一趟,出来就看人都走了,黑乎乎的,怪吓人哩。咦,小孩都睡了?”她问婆婆,脸上红扑扑的。
“都睡着了,你也去睡吧。”婆婆说。季刘氏低着头出了门。
半夜里,季先生好似做了个什么梦,突然惊醒了,似乎听到后院里有响动,像是人碰翻了墙边放的砖瓦。他一激灵,联想到儿媳妇那天回来晚了,脸红扑扑的,似跟平日不同。随后的几天,大家一起回时,她跟在人群中,别的媳妇说笑她似乎也没有听见,桥上过时,身影像是飘着一般,一看就是魂没在身上。也许他从梦中惊醒就是缘于内心几天来的不安。他推醒了身边的季瓷娘:“我听到了后院有声。”季瓷娘在睡梦中说:“深更半夜的,哪来的声儿,睡吧。”“有声儿,你听,从咱的山墙边往前走了,走到院子里了,这不是开门声。”季瓷娘也醒了,怔怔地在床上。
季先生起身,趴窗户上往外看,月明地儿里,见季刘氏那飘乎乎的身影从大门走回来,头发披散着,穿一件小布衫,扣几乎没有扣,虚虚地在胸前揽着,小脚轻盈地踩在地上,顺着季先生的堂屋窗下走回后院了。“哗啦”一声响,季先生听到有个东西在自己心里打碎了。
第二天,季先生不由得留意看儿媳妇。唉,这一仔细看,她还真是个寡妇相苦命样,胯骨窄小,细溜溜一个身架,真不知她咋还能生了俩小孩,脸小得有一巴掌宽,杏仁眼,细眉毛,一张薄薄的小嘴,终日里紧紧闭着。当年我只是跟她爹友好,看她从小家教好,就说给了自己的儿子,却不知她是这样的命,年轻轻守了寡,这也五六年了。当初曾问过她,愿不愿再往前走,她说过不愿,现在是不是得再问问她。
季刘氏给他端上来饭时,他伸手接住,问她:“夜儿黑是不是小孩子起来到院里尿了?我听见把瓦碰了,屋里有尿罐,别叫小孩夜里出来,沾了邪气不好摆治。”
季刘氏脸“唰”地红了:“是我,半夜里肚子不舒坦。”说完脸又突然白了,因为茅子在南屋的东山墙,她怎么会碰到摆在公婆屋后的瓦呢?
晚上喝罢汤,季刘氏对公公说:“我肚子还是不舒坦,今儿黑不去识字了。”
这晚,她没有来,急坏了一个人,那就是教大家识字的周老师。周老师往日都能在下面仰着脸听课的人中看到她,在昏暗不明的灯光下,季刘氏的脸更显得像仙人般虚虚飘飘不真实。
周老师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眼能看出女人的优劣高低。第一天晚上,他走上讲台,扫一眼下面的人,男人不必说了,没啥看的,女人中,他发现一个与乡野村妇不同的人。她纤细白净,哀怨忍耐,眼睛忽忽闪闪地不看他,可他知道,她心里想看,她的想看与别的妇人不同,她把自己隐在暗处,那眼光似羽毛般,一下,一下,又一下,轻轻扫在他的心尖上,有时候又似懂非懂般地带着好奇和询问,如灶膛里大火燃尽后的火苗,蓝色的,娇羞的,疲倦的,似有若无,从一堆灰烬中突然俏皮地跃出一朵,在他脸上舔呀燎呀缠绕呀。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哀怨,为什么有着欲言又止的忧愁,她还有着似乎从没有被男人侵犯过的贞洁和不谙此道,可她看着也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了。没有男人能经得起这种目光,周老师在讲台上站着,表面镇定自若,内心已燃起烈焰。他让同学们照着黑板上的字写,他一个个过去看,走过一个个闺女媳妇,走过一个个臭男人,来到季刘氏身边,停下来,看她写人口手。
第二天晚上,季刘氏坐在最后的角落,周老师明白了她的心意。再巡视的时候,迟迟不到她身边去,只在别的学生跟前停留,看一看,手把手教一教,说一说,笑一笑,也许那些闺女媳妇都以为周老师只为在自己身边停留。他满足于这种被宠爱,他拖延着不去她身边。恋人有时会用这种残忍加深对方的煎熬,加筑自己的甜蜜与激情。直到快下课时候,他在教室里转着,给大家说:“这写字呀,要天天练天天看,你要是不练不看,今儿黑学的都是白搭,到头来还是你不认识它它不认识你。”他走在她身边,像是个趔趄般歪了一下,起来时一个纸团就在她怀里。她知道他定会这样,她知道他硬着心肠不过来可他的心一定在她身上。一个个长夜的孤独冷寂,修炼出她一颗通达灵性的心。她与寂寞为伍太久了,她这几天面对或许将要到来的一切常常硬着心肠给自己说,大不了一个人躲在夜的怀里流泪,大不了哄睡孩子后一个人来到堆放杂物的西屋,关好了门,蒙在被子里放声地哭泣。她握着那个纸团,在手里舍不得立时展开。周老师走上讲台,说:“好,今儿黑就到这儿吧。”这些刚识了几个字的学生还没有学会规矩,“呼”地吹了自己的油灯,“哄”的一下起身,碰得板凳桌子乱响,呼啦啦走了。季刘氏丢了魂般,手按着桌子缓缓站起来,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把那个纸条展开放在油灯下,上面是周老师写的三个毛笔字,人、口、手,在“口”字里面,用铅笔画了个油灯和火苗。
她手里握着油灯,来到后院。这是教师们住的地方,本校的老师中午在这儿歇息,晚上都回自己家去,只有几个外乡来的新老师晚上住在这里,那里只有两个窗子亮着灯。她觉得自己轻飘飘了,只管往前走,身后的一切,家里的一切,连下了课后等着和她和大伙一起回去的公公都忘了,她被自己这股劲吓住了,天哪,怎么就像蛾子一样要扑向那火苗。两个房里亮着灯,是哪一个呢?越走越近了,“嗵嗵嗵”的心在胸口跳着,“呼呼呼”的风在耳边响着,像是把她带起来要飞离尘世。她按住心口,就见一个窗户上突然显出他的头影,是他,他只闪了一下就吹灭了灯。她走过去,正要抬手推门,门“吱纽”一下开了,里面的人把她呼地拉进怀里,像是抱一只小兽般搁到床上,两人拉风箱般一上一下喘气。“哪个庄的?”“小季湾。”“谁家里的?”“公公是季先生。”“男人干啥的?”“死了。”“咋死的?”“土匪打死的。”这场突然而短促的激烈拥抱,带着闪电般的惊吓与甜蜜冲击,对她来说是地狱般的黑暗中突然撞进了万丈光华。
周老师心疼地给她扣好衣裳,理好头发,这才顾得上给她说,他家是南边一个县的,今年三十六岁,解放前参加革命,家里有老有小,他是被抽到这儿临时当扫盲老师的。季刘氏拿起油灯:“我得走了。”周老师紧紧抱住她,明知故问:“不走不中吗?”“不走不中。”“再等会儿吧。”“必得回去了,真的。”两人连成一体来到门口,门开了,人还是不丢手,剥离开胳膊剥离开身子剥离开勾着的腿,最后是嘴唇的艰难剥离,季刘氏推了一把,魂魄丢在这里,躯体出门而去。握着油灯,一口气跑到石桥上,放慢了脚步,张开嘴巴,把狂跳着向外蹦的心往嗓子眼里放啊放,缓缓抚摸胸口,想好回家要说的话。
季先生正在家里,学校里几个老师来了,里面就有周老师,手里提着两包馃子一瓶酒。周老师说:“来这里快一月了,忙来忙去,还没有出过白果集,也该来看看德高望重的季先生。”另两个老师说:“季先生回家以后,俺也没来看过,今也算是借了周老师买的馃子和酒,来看看恁。”季先生赶忙叫季瓷娘换豆腐打鸡蛋,又叫来季刘氏,掏了钱,叫去集上割肉,被几位老师硬拦下了:“来得就冒失,有豆腐和鸡蛋就好得很了。”
几个人在家里吃了午饭,又说了会儿话,告辞走了。这只是一场合情合理的拜访。
今晚,季先生把这些事前前后后一想,他断定夜里来到他家后院的是周老师无疑。
他下了课,留意看那年轻人。
周老师正心神不定地往后院走,脚下像踩空了般。他幻想他那没来认字的心肝儿也许会在房中等着他,他想着他走过前面那个弯,她细细的身子会站在那里,他再走两三步,那人会从暗中跳出来,抱住他,他回身将她搂在怀里,掠向他那甜蜜黑暗的小屋。
季先生站在那儿,看着那年轻人不安的身影走远。他庆幸自己没有急急叫住他,叫住了说啥呢?挑明了对谁有好处哩?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谁不知那是怎样的大火,能把人烧煳烧焦,燃成灰烬。可是由他们这样下去吗?万一哪一天儿媳妇的肚子鼓起来,这可让一家人的脸往哪儿放。
季先生缓缓上了石桥,他停下来,看着河水,想起自己死了的儿子,心更加烦忧。要是儿子活着,咋能有这种事哩?就算是有人想吃腥就算是儿媳妇想偷人,那可以光明正大地打一架,把那人打跑,回家把媳妇打闹一场,认错的认错,服罪的服罪,今后日子该咋过还是咋过。谁没有犯浑出错的时候,也不是太窝囊的事,可是,现在,你叫一个寡妇自己打心里不想男人,那比啥都难。
夜里他睡不着,听着院里的动静。半夜里,果然就有了。季刘氏猫一般跳着来到大门,将那人引进来,转身关了身后大门,扯了手从他堂屋的窗下走过,从他的眼皮子下走过到后院去了。这次他们很小心,没有碰到院里的任何东西。
老婆问:“咋办?”
“咋办,还能咋办呢?总不能到后院把他俩堵到小西屋吧?撕破脸皮,那就太难看了,净是叫她恼了咱俩。”
再也合不上眼了,二人躺在床上,也不说话,只是一递一声地叹气。
夜静得死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