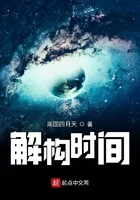这个山东商人叫鲁平,做私盐买卖,从扬州那里听说了海州这里的盐场可以随意买盐,便摸索了过来。他带了一艘小船,一二百吨的样子,不过却一下子就抽空了邓西盐场的存货。
邓西的盐场现在规模扩大了五百亩上下,手下有一千人,每年产盐六百多万斤,但是他手里现在有三条四百吨的大船,加上扬州的私盐路子已经打通,平时也不愁出货。这次鲁平到来一下子就抽空了他的库存,邓西打算继续扩大规模。
赵泗正在法庭里跟一群人商议事情,这个法庭在大家的心中的概念现在很不一样,西方人都知道这是审理案件的地方,一点不奇怪。村民们开始把这里当成了传说中的衙门,后来看到知县也不做堂,反而常常是一些乡老,富商在这里给人解决争议,慢慢竟把这里当成了祠堂,有人要和人打官司前还在门前烧一炷香。
法庭设立后,就按照石碑刻纹来判决案件,很快大家都发现了问题,就是碑文上面根本没有处理方法。由于一次大明商人应邀处理一个洋人跟村民的纠纷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险些酿成了又一次的暴力冲突。一个刚刚来到海州的荷兰商人在一个村民的店铺里看到了一个铁铸的猪头,觉得很新奇,便掏钱买了下来。那时候开店铺的妇人恰好不在,他八岁的儿子把猪头卖了,刚交了钱还没来得及拿走东西,妇人回来了。妇人立马夺回了自己的东西,她不愿意跟夷人做生意,因为当初跟夷人冲突死的人中竟然有他的丈夫。荷兰人很不满意说自己的钱都交了,妇人二话不说把他的钱掷于地上,坚决不同意卖给他。俩人都不服气,荷兰人非要买走东西,俩人就闹到了法庭去了。
当日轮到一个有名望的大明商人来主持裁决,这人虽然是个小商人但是却饱读诗书,待人谦和所以也被众人推举可以去法庭做主持人。可这小商人太谦和了,平时很少与人争执,见到妇人跟荷兰人各自说明了缘由后。他想着石碑上刻有公买公卖的条条,便判妇人赢,说荷兰人不能干涉别人的买卖自由。
虽然没做任何处罚,但是妇人还是很高兴,荷兰人却气不过。他是刚到这个地方的,根本不知道村民们对他们西方人的态度,不然也不会去他们的店里转悠了。气不过的荷兰人便找他们商馆的主事主持公道,现在荷兰商馆已经不是威廉姆主事了。威廉姆是个工程师荷兰在南洋不停的扩张他们的商站,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留在海州。
荷兰商馆的新主事是个文员,曾经还学过法律,本来想做律师的,可被东印度公司的高薪吸引来到了东方。他听了荷兰人的诉说后,感觉是自己人对,便又向法庭提出申诉。于是继续开庭了,这次主持法庭的是八大海商的一个掌柜。这掌柜可不是好惹的,他原来是主人家的管家,被派到安南来本来心里就不满,所以他出手判决的时候一般都很严厉,往往要打板子什么的。
掌柜也审理的结果跟上次一样,也说荷兰人不能干涉人家的自由买卖,还判他们无端启事,要让手下打荷兰人的板子。荷兰人不服他们的商馆主事吕特开口申辩,说不关什么自由买卖的事情,双方当时已经钱货两清了,是卖家后来反悔的。是他们破坏了公买公卖的原则,而且一旦答应卖了相当于履行了一次契约,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要判妇人输,掌柜一听有道理,便又判妇人输,他到没打妇人,要求妇人把铁猪头交给荷兰人。
妇人不干,也不服气继续要求重审,于是这个案子来回折腾直闹了一个月。主持审理的人来来回回换了七八个,最后闹到赵泗这里,赵泗也觉得妇人不对。便让妇人把猪头给荷兰人,妇人不肯,说大人既然判我错,我认了,但是就是不卖他,要怎么罚接着就是。赵泗蛋疼了,这是女人打又不好打,就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对就该把猪头给人家,又不是什么宝贝。妇人还是不肯,就说让赵泗责罚她。赵泗无奈了,便说那你道个歉算了。这下荷兰人不干,妇人也不干,说要杀要刮随便,他丈夫是夷人打死的,不行把自己也打死了算了。荷兰人要赵泗打妇人板子,赵泗下不了手啊,她又不道歉,实在无法就说打五板子。荷兰人说判的太轻了,至少都要三十下。有人求情了,说就是个妇人,不愿意卖就不卖了,又没有讹荷兰人的钱,他们犯不着这么较真。荷兰人不服气就要扯什么破坏公平原则了,赵泗一怒说,我已经判了你们赢了,不要得理不饶人,判多判少我说了算。
时候荷兰人觉得不公平,常常闹事,赵泗这时候也觉出来石碑上刻些不能做什么似乎不太妥当,便又找人商量着具体的处罚手段也要刻上去。便聚集众人开始商议,最后定下了杀人要偿命,偷盗十两以下打三十板子,十两以上五十,五十两八十,等等具体条款。又聚众商议没有意见找人刻上去了,后来又觉得一个案子闹闹腾腾一个月,实在太耽搁事情,便规定一个案件最多只能申诉三次。
处理完这些事情,赵泗才有去了邓西处,跟那山东商人鲁平商量些生意上的事情。鲁平除了来买盐外,还希望能买些铁,他说他是做辽东生意的,可以弄来人参马匹皮毛。问赵泗对这些有没有兴趣,海州港现在货物众多,可铁却不是主流的货物,最多是些农具之类的,量也不是很大。不过要弄些来,赵泗也是有办法的,佛山就是产铁的地方,离这里十天内就能运来。但是人参等物虽然是好东西,赵泗却不知道如何卖出去,至于皮毛倒还好说荷兰人英国人都会收购,可马匹却没什么用处,港口拉货用牛车就够了。
最后赵泗只答应帮鲁平采购一些铁,没有同意他用毛皮等物来换,告诉他只能用现银来买,还说他可以运这些东西来,至于能不能卖出去就不负责了,最多帮他推销推销。这相当于生意没谈成,有银子什么货买不到,所以鲁平不是很满意。他打算过了今晚明日就走,至于以后会不会来这里做皮毛马匹贸易,就看看行情再说了。
晚上赵泗在邓西这里陪鲁平吃酒,后来吃的天都晚了,几人也都有些罪了,便留了下来。
“大人不好了。”
一个村民突然冲进了邓西家里大喊。
这时候赵泗等人还没有起床,摸着还有些痛的头把,村民叫进了屋子。
“妈的,以后再也不喝了。”
“大人不好了,官兵杀来了。”村民着急道。
“什么?那里的官兵。”赵泗大惊。
“我们也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到处抢东西呢,我们拦也拦不住,几个兄弟上去阻拦一下子就被砍翻了,死活不知啊。”
“哦,八成是那里的溃兵吧,没听说最近打仗啊。难道是又跟莫朝打仗了。”赵泗这样想着,道:“走带我去看看,如果是溃兵给他们一些财物打发他们走就是了。”
一路小跑到了到了港口一看,果然乱糟糟的一片,到处几分狗跳,还有人哭喊求饶。
这些溃兵太不知好歹了,赵泗看着自己雇佣的那些村民都束手无策,任由几百个溃兵进进出出,手里拿这抢掠的大批财物不管,不仅有些生气把众人着急到一起,道:“都跟我过去看看,这大概有多少人啊。”
一个村民道:“有三百多人吧,是坐着船一大早来的。”
坐船?这到有些奇怪,不过不能眼看着不管,赵泗立马带着众人往仓库跟民房那里走去,正好一队溃兵经过,赵泗大喊:“我是知县,你们都住手,你们的长官是谁,叫他来答话。”
溃兵突然停了下来,左右相互看看,交换了个眼神,突然挥刀冲了过来,喊道:“快,那个是赵泗,活捉他有赏啊。”
赵泗懵了,眼看着不到百米开外的十几个安南兵冲过来,连怪溃兵骄横的想法都来不及生出来就被一个村民一推,反应过来撒开脚丫子猛跑。也没有方向,一路乱窜,后面追兵不断,而且越追越多。而那些村民根本不敢挡着官兵,不过也不挡赵泗,赵泗混乱中竟然又往北跑去了。
猛跑了一气,赵泗竟然比那些溃兵体力好,甩开了一大段距离有二三百米。这时候迎面来了几个人,赵泗惊弓之鸟以为被包抄了,看清楚才安心原来是鲁平跟他几个手下。
“跑快跑。”赵泗便跑,便给鲁平等人摇手。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鲁平看着向自己跑来的赵泗问道。
“我自己都不知道,快跑到邓兄的宅子里避一下,”赵泗又想不对啊,“不行不能去那里,把乱兵引过去不合适。”
到了鲁平跟前,眼看后面的追兵已经在四五百米外了,而且都停了下来,好像在休息。赵泗也停了下,说道:“鲁兄你的船在那里我们还是先商船吧。”
“就在盐场那里,看就是那条。”鲁平往东面一指,果然在几百米外有一条船。
“走快跑,他们又追来了。”赵泗刚休息没几句话功夫,看见乱兵又冲了过来,人数比刚才更多了,粗粗一看足有一二百。虽然是一二百那气势赵泗都没看见过,只见一个个举着明晃晃的刀枪,嘴里嗷嗷叫着,是个人都得怕。
赵泗拉着鲁平才跑了几步就不得不停了下来,这鲁平是个胖子,平时走路都呼哧呼哧的,此时根本跑不动。
赵泗不好一个人跑,毕竟是要去人家的船上躲避,便用力拉他,可也没用。眼看着乱兵逼近到一百米的样子,赵泗道这下子完了。却见鲁平身边几个人,突然不知道从那里一人抽出了一把短刀,为首的一个对身边的道:你保护东家,其余人跟我上,拖住他们。说着就挥刀冲了上去,赵泗继续拉着鲁平跑。
眼看着离船近了,船上人也看到情况不对下来了几个,鲁平突然对船上喊:“有情况抄家伙。”
呼啦啦下来了二十几个人,人人一把弯刀,他们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都体格强壮,最怪的是脑袋上的头发削掉了一圈,只有中间一撮儿变成个鞭子。赵泗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群奇怪的人就嗷嗷叫着风一般从身边冲了过去。
终于到了船上,赵泗才有空儿去看岸上的情况,发现就在两百米外,鲁平的手下已经跟安南兵杀到了一处,赵泗大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