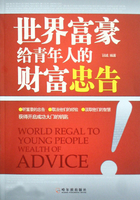而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生活如此愉快,忧郁症患者的所谓忧郁更像耍赖,他们在要挟别人把目光关注在他们身上,替他们解决生活烦恼,帮他们拖地、洗衣、付帐。但是,谁愿意用病症赶走亲人,用忧怒拣选友人,用麻木轰走情人,用痛苦取悦路人?做一个勒索者幸运,还是做一个被勒索者幸运?
可是我们不管,昨天,当我听到一个邻居女人说:“我得了忧郁症”,那一霎,我的眼竟然放射出“幸亏不是我”的光,然后,面对她痛苦的唠叨,又留给她一个昂头离开的背影,这个背影甚至在向她炫耀:“看,我多快乐。”
真罪恶。
没有谁不愿意幸福、快乐,只是他们做不到。朋友离开,他们无法挽留,亲人厌弃,他们无力反抗,世界苛待,他们只能瘫坐在一隅,呆呆地瞪着面前一尺见方的墙壁。看着陷在忧郁里的人,真的感觉像在观赏被一块玻璃镇纸封住的蝴蝶,颜色栩栩如生,说话直达耳畔,可是,他们说的话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说的话他们无法做到,到最后尴尬互瞪,彼此僵视,像是来自不同的两个星球。
假如我们明明理解不了他们“那一国”的语言,但能够作出理解的样子,或者虽然做不出理解的样子,但做出努力倾听的样子,就足够慈悲。若你肯拉着他们的手直到他们慢慢入睡,甚至肯在他们的床边唱一首摇篮曲,你就成为他们精神上绿荫、清水、温暖的火炉,和酷烈骄阳下的遮阳板。不要转身就走,不要指指点点,不要让我们的面孔模糊成一张张青色的脸,嘴巴里喷吐出灼烧人的内脏的火焰。
忧郁的反义词其实不是快乐,而是活力。我们没办法把他们的身体变成漏斗形的容器,然后把活力一股脑倾注进去,我们只能用我们一点点委婉的善良和关注,悄悄地在枯萎的树根部一点一点地滴灌,然后,看着它渐渐地泛青、变软,抽芽、长叶,他们重生,我们喜悦。
当忧郁症患者终于有一天肯对你诉说:“我老公和我吵架了,我长了龋齿,天怎么还不放晴,狗叼了我的袜子,唉,日子真难过。可是我的精神很好,一切都还不错。”那么,真诚地恭喜你,替他砸碎了那块透明的镇纸;真诚地恭喜他,因为他像一只真正的蝴蝶,正在翩翩飞翔——你的友善纯净而芬芳,像透明的气流,托起他的翅膀。
菜如菊,人如鱼
餐厅里熙熙攘攘,给人感觉一张张餐桌就像一口口的大鱼缸,每条鱼都在竭尽所能吐泡泡。有种鱼声色频繁,言语轻佻,一张嘴恰似两扇关不紧的门,被风吹得咣当乱响,浮躁的泡泡咕噜咕噜满天飘,咕噜噜亮了,咕噜噜灭了……有种鱼神色端凝,坐阵一方,绝不多言语,却是每语如箭,正中靶心——如同大鱼,泡泡不吐则已,一吐就囊天括地。任你小鱼小虾斑斓彩色,也掩盖不住它沉默里的王霸之气。
这两种鱼都不宜多,每桌一条足够,霸王鱼多了王不见王,容易打仗;躁鱼多了鸡讲鸭讲鹅也讲,容易叫人晕头转向。所以更多的鱼宜随大流,霸王鱼说话它也听,噪鱼说话它也笑,大家一起吐泡泡,看似周到,其实一嘴两用,一半说话,一半吃菜。
那么,这一桌桌的菜,又像一座菊花园。菜若上得丰盛,那是花开得好,满城尽带黄金甲,好气势、好华丽、好格调,好比杀气腾腾的黄巢,我花一出,谁与争锋;菜若上得寒素,好比今天中午,一桌十个大男人,只上了六凉六热,且荤少素的多,又上得慢,一道菜上来,那盘可怜的菜好比一朵金丝菊花,被一群饕餮争相下嘴,你撕一瓣我撕一瓣,不一会儿就剩一根光秃秃的菊花梗,空盘子泛着油光,里面躺一粒虾壳。凉拌菜心,没了;老醋海蜇头,没了;豆豉油麦,没了……一桌空盘是凋残了的菊花园,“蒂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
昨天晚上是有一顿丰盛的宴席的:红烧大肘、白切的肥鸡、金红的虾子炸得焦脆,想吃口素的吧,还得要从肉里辛苦翻拣,一片菜叶也如获至宝,丢嘴里忙忙地嚼,一个个起劲抱怨全肉不好。那个时刻,大家都没想到第二天的俭约。
其实这两种上菜方式都不好。
一口鱼缸里尚且要有一条领军之鱼才能压得住阵脚,一座菊花园里也必得在异色纷呈之际,有一朵主花,才能不使人双目失焦,所以饭桌上过素净不好,太肥厚也不好。好比一群人,躁极是要静的,静极的时候也需躁,怕的是静之又静,气就“死”了;躁之又躁,气就“疯”了。
看一场晚会的节目,出来一台是美女歌舞,再出来一台又是美女歌舞,然后上来一群小孩子表演非洲鼓,四个小孩子上场,绿格子短上衣,牛仔帽,短短的腿,各在前胸挂一面鼓,咚咚咚咚地敲,配着西化的痞痞的舞步,别有一种稚拙的豪放,引来掌声一片;本想于此已是极致了;却是一左一右两边舞台又各上来一对,一高一矮相搭配,高的弹吉它,矮的摇手铃,嘣嘣嘣,哗哗哗,配着娇憨的舞步和歪戴的牛仔帽,又引来掌声如潮;又想着此已是极致了罢,却是又上来一位女孩,白衣红坎,肥腿的牛仔裤,移步起舞,顿开喉咙唱歌,高亢的嗓门不羁、狂放,原来这个才是中心啊。
所以说,如果一桌子菜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好,没重点,华丽得茫然;如果是“一径寒山归暮鸦”,也不好,就算饭桌是桃源,讲的也是一个桃红烟绿柳如线,清景过寒,非喜庆之道。而菜品更如人品,既不可油腻沉重,也不可轻薄浮躁,一张嘴说得热闹,到最后却是吹了一个空空的泡泡,过后想怀念都抓不着重点,如踏流沙,被时光冲得立不住脚。
人如鱼,菜如菊,小饭桌也是大舞台,一个个起承转合间,人生就过去了。
向死而生
刚看了一本小书:《殡葬人手记》,作者托马斯·林奇,美国密歇根州一个小镇的殡仪馆的老板。
这个特殊的职业虽使他见惯死亡,却在心里保有鲜活的,非职业化的感想,这一点殊属难得,就好比沙漠里开出鲜艳的潮润温软的大瓣花朵,那感觉很奇特。
生者营营,一个牧师打高尔夫球,穿爱尔兰亚麻布的法衣,开高级轿车,还想当红衣主教,这个家伙居然放胆宣言:死的时候不要铜棺,不要鲜花,只要有一个简朴的葬礼和一个平民化的坟墓;托马斯很客气地跟他讲,不用到死的那天才这么搞,你现在就可以做活着的圣徒:退出乡村俱乐部,不开豪华敞篷车,不穿高档毛衣和皮鞋,不吃上等肋条肉,不殚精竭虑地攒钱,你的钱我还可以帮你分给穷人——然后,他收获了这位高贵的牧师的诅咒的眼神。这样的人并不稀罕,他是世间虚伪的典范,表面明光闪耀,内里一团败草,只有死亡才能使他摆脱欲念的困扰。
相对这个牧师而言,托马斯的邻居米罗朴实善良,他开着洗衣店,不声不响地帮助刚刚离异,带着四个小孩艰难生活的托马斯,每天早晨来带走五大包脏衣服,中午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送回。“我”去交付欠帐的时候,顺便向他致以谢意,他笑着说:“别放在心上,一只手洗另一只手,谁跟谁呢?”现在,米罗死了,双眼紧闭,目光熄灭。“我”郑而重之地对待他的遗体,先是让右手压在左手上,然后再左手压在右手上,后来,“我”不再折腾了,因为不管怎么放,都是一只手洗另一只手,有什么关系,又分什么彼此。
托马斯的父亲也是殡葬师,托马斯子承父业的同时,顺便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于死亡的深广的恐惧,他们眼中看到的一切,包括疯狗和能传染疟疾的蚊子,以及冒充邮差与教师的歹徒,都有可能谋杀自己的孩子,就连蝴蝶都难逃嫌疑。见惯了死亡,也深刻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却仍旧对于孩子的死倍感恐惧,是因为老人的死和孩子的死,实在是有着不同的意义。“当我们安葬老人时,我们埋葬的是已知的过去……记忆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最终的慰籍。但埋葬孩子就是埋葬未来,和被我们的梦想所拔高的美好前程。这样的悲伤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记忆的完满和梦想的永未实现,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永远都是前者可供欣慰,后者足资伤痛,古今一理,天下大同。
可是,无论怎样,有生便有死。刚生下来需要清水洗一洗,刚刚死亡也需要用清水洗一洗,这既是仪式,又是需要,就像托马斯充满幽默风趣的调侃:“在生命的此端,我们宣告:他活着呢,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在生命的彼端,我们回应:他死了,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可是,无论洗与不洗,对于生者也许是必需,对于死者却已是毫无意义。“意义的丧失正是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头一个明确迹象,”的确如此。
虚伪的人活着搜罗鲜花和尊敬,真诚的人死后收获怀念和哀悯;老人死后获得尊重,幼者死亡引发悲伤,可是无论什么样的人,一旦死亡来临,便铜棺和木棺平等,鲜花和荒草平等,地宫和土坟平等,老人和幼儿平等……生为物役,营营不休,逝随流水,一无所求。
偶翻纳兰性德的《饮水词》,看到一句“风絮飘残已化萍”,词意不过是援引古说,讲杨絮飘零,会入水化作浮萍;那么杨絮便是浮萍的前世,浮萍便是杨絮的今生。几天前,家人闲话,说起早已逝去的祖母。母亲说这么多年,谁都不肯给她上一次坟。我的父亲此时已七十余岁,平生胆小,一向怕打雷,怕坟地,现今正端坐如佛,乖乖看电视,却忽然大声抽泣。当时不以为然,我是无神论者,偏要讲往生,安慰他说不要哭,上不上坟都没关系的,人早转生,如絮化萍,我们所见,只是一座空坟;可是现在想起,却心里酸痛,因为它印证了这本书中的一句话:“我死了,是你们活着的人面对死亡。”
这是死者对于生者的最后宣言。是的,逝者早得解脱,面对死亡的,从来,一直,永远,都是生者。
一路离情
“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杨绛《我们仨》
得知钱钟书先生逝世,是在电视上。当时在老家,孩子还小,偎在我膝前安静地玩耍。先生扯闲话,婆婆打毛衣,公公打盹。没有人注意电视上正在播报什么,只有我听见,“……钱钟书先生已于……因患……病逝世,享年……”我哟了一声,再说不出什么来了。没有人知道钱钟书是什么人。我只能在心里送钱先生一程。
钱先生逝世之后,我也并未曾想到杨绛先生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从意识里,是把钱先生当作一个公众人物来看的,可以引起自己泛泛的感伤和新一轮的崇敬。我忘记了,除了学者的身分,他更是一个人夫,人父,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走后,会让亲人痛断肝肠的伤心和如痴如醉地怀念。如若不是这样,以杨先生的高龄,不会忍着思念的伤痛提起笔来把已成前生的丈夫和自己的足迹再重新走过一遍。
至于钱媛,也就是钱先生和杨绛女士的女儿圆圆,还是在杨绛先生写的《围城》后记里读到才有的印象,但是也并不鲜明。只是晓得钱先生老爱和这个惟一的宝贝姑娘闹着玩,比孩子还玩得凶,害得圆圆经常无奈地冲着姆妈告状。这个阿圆,承继了父母的优点,学东西有一股子痴气,所以学有所成,重任在肩,累年不得休养,结果到最后一旦躺在病床上,就不得起来,先父母一步,回了“自己的家”。害得孤弱的杨先生,一头照顾病重的钱先生,一头变了梦屡次探望病中的女儿。心上给捅了一下又一下,绽出一个又一个血泡,流出一注又一注滚烫的眼泪。最初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当娘的心痛得胸口都要裂开了,还得忍着满腔满腹的痛送别依在病床上两三年,让杨柳青了又黄,黄了又青若干次的丈夫。大限到来,先生对厮守一生的妻子说,“绛,好好里(好好过)”读到这里,我的泪下来了。
一个在人生驿道行走了大半辈子的老人,送别自己的女儿,送别自己的丈夫。厮守几十年的家三分之二都已失散,剩下自己,成了一个孤单的锐角三角形,不再完整,陪伴自己走完剩下的路程的,只有满满一路的离情。而三里河的家,此刻已经不复是家,只是客栈了。老境如此凄凉。
一向以为学者的心思都是缜密而冷静的,看感情也看得比常人透脱,视人生死无异于如蝉如蜕,可是透过平淡质朴的文字,却透视出一条丰沛的感情的河流,从旧年的岁月里流来,载着飞花落叶,时而拧着旋,打起一小股一小股的浪花,驶向生命的终结。
才发现世界上还有这样纯真和投入的一家在。一家三学者,哀乐不忘情。
俞伯牙要走到荒寒之地靠老天安排才觅到一个真正的知音,而且还英年早夭,害得自己灰心摔琴,大叹自此之后,天下更无知音。羡慕钱先生一家,一门三学者,彼此为知音。难得老夫妻二人,一辈子心性淡泊,妻子不逼丈夫抓钱抓权要房子要待遇,丈夫不嫌妻子不去洞明世事走内线给自己铺平升迁道路。难得二人书痴,坐在书围城里过自家的光景。你说我懂,我说你懂,这是什么样的境界!自小心高意气深,遍觅知音,侬是知音。羡慕。
自己的女儿,不仅聪明,还继承父亲的书痴之气,求学问不止,当教授不疲,和父亲也说得,和母亲也说得。动时三口玩作一团,静时各自伏案笔耕,这是什么境界?羡慕。
不痴不笑是木头学者,过家庭生活了无趣味。难得一家人童真不减,赤子之心不失,携手同行若许年。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自身的生命重量,比起官高位显,名车美人的生活,不晓得要值得多少倍。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