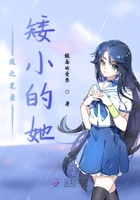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她没有松开,紧紧的拉着我的手。她的思绪混乱不堪,看起来就像秋天最后的帷幕,如果有一场狂风她便会倒下去。我试图改变她的目光,可漆红的家具依然,她的岁月依然交织着痛楚,没有留下痕迹,没有留下痕迹的路走起来岂不是会很艰难。我看着母亲的目光,那目光痴呆,就像一个小时前发病的精神病人忽然一个小时以后又回复了安静,安静的可怕,痴呆的也可怕,甚至可以看得到血丝。
我弱小的心里在流泪,为了我的母亲。
妹妹哭着醒来,每当她发现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她就会哭着闹着。母亲领了妹妹,我们三个人就站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西风第一次吹落我们三个人的生活,那可怕的现实陡然爬了出来。
忧虑第一次爬上了母亲的眉间,也爬上了我小小的心灵。
妹妹忍不住说:爸爸呢。
母亲看了看她说:你爸爸走了,明年你就可以看到你爸了。
那个时候,她已经内心里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流了下来,她依然坚强的站在那里。院子里的梧桐,母亲身边的我和妹妹,便成了我十二岁那一年的一切。
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下来,落在了妹妹的肩膀上,我悄悄的拂去那片黄色的叶子,看看妹妹发红的面颊,此刻,我们依然在故乡的这一片土地上,母亲也在,在只属于我穷乡僻壤的这片土地上。
我想,那个时候,我该跪着感谢它的养育之恩。可二十年成就了一片绯红,那不属于月儿也不属于血液,依然爱着那山里面穷困的夜月,以防我在书写我自己人生的时候重蹈覆辙,可我不是父亲,也并非母亲。
天色稍微的暗了下来,庄稼里的收成早已归入我们的口袋,可以换作钱,然后我们去花。我们村子离镇上有二十公里的路途,那个镇子便是我向往的地方。
我们一年的收成以后,当做买卖,换成钱,然后供我们消费。
最为欢喜的时候就是随着母亲去赶集的时候,那条街也就五公里长度,只有一条街,而那条街成了我唯一的乐趣。
那条街上有我最为喜欢的玩具,有各种好看的衣服,还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有趣的事情,所以它在我的童年中留下了痕迹,那痕迹随着时光推移,从未消失。而每当我记得,在这条街上,我忘记了所有的抑郁,和一个公子一样大摇大摆的过街,十二岁的天空也该这样,我们仰望着不同的方向,唯独发现垂直于地平线的方向才是起飞的开始地点,也是我们终结的终点。
母亲走在前面,她穿着红色的妮子衣服,深蓝色的裤子,一双自己做成的鞋子,看起来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但她是种抬起头来,包着她那蓝色的头巾,她看着路边的摊子,有买布的,有买鞋子的,也有买日常用品的。
她停顿在买布的那里,她踮起脚尖,摸摸那布又摸摸这布料。
她问:给这两个孩子,做一身衣服该要多少布料?
买布的人给她量了一下,然后就用口咬破布料,滋滋的撕下了一块布,包装好,交给了母亲。
赶集的人都散了,已是午后。
我们跟着母亲在那山脉上,秋日的风儿阵阵吹,我走的累了,累了,妹妹又在我的肩膀上,她已累的睡着了。
母亲又怕妹妹着凉,便脱了自己的衣服裹着妹妹,她抱着妹妹,我跟着母亲。
我们村子去赶集那二十公里的路,是翻越一座山,上山,下山,中间是一段平路。
是啊,活着岂不也是上山下山,之间有过一段平坦吗?
我们在一段平坦的路边休息了下来,母亲擦着汗水,脱掉了自己的蓝色头巾,她有些憔悴,然而十二岁的我不会发觉这么多,只是觉得母亲已不是从前的母亲,或者父亲那个夜晚让我的母亲受了伤害。
我一直再想着我的父亲。
但我更加想我的母亲。
休息的时候,母亲抱着睡着了的妹妹,她对我说:桐木,走的累不累。
我说:不觉得累。
她再也没说些什么。
我提起了我的父亲:妈妈,爸爸今天啥时候走的?
母亲说:早晨的班车六点半,你爸爸六点就走了,走的时候你还在睡觉。
我说:恩!那他明年这个时候就回来了?
母亲说:不知道还回不回来。
我感到异常的氛围笼罩着我和她还有我熟睡的妹妹。
或者是我敏感与这个世界的分离,变得更加敏感,但我不知道分离已经不再那么敏感,敏感的是我的心,而不是我的灵魂。
我的父亲是离去了,他没有和我告别,只是在黎明之前就已经独自离去,我有些想念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而现在我就在母亲的面前,她的容颜在这片土地中,映衬着午后阳光,我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