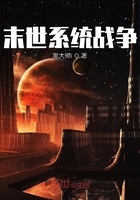后来我知道那些画面不是凭空的幻觉,而是千真万确的存在。能够那么快洞悉其中的玄奥,必须感谢这个在办公室做小职员的男人。他平庸,现实,甚至有些猥琐,却独有一项美德,那就是诚实。他并不总是那么诚实,只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过是一段露水情缘,我不可能与他恋爱。既然没有未来,也就不必处心积虑地掩饰自己,两个人反而能够坦诚相待。他无所顾忌地谈起自己从前的女朋友以及在性方面的经验。前者少得可怜,后者却蔚为壮观——他有丰富的嫖妓经验。我饶有兴趣地询问,他也就慷慨地都讲出来。我惊异地发现,某些细节与我所看到的幻象完全一致。昏暗的房间,画着浓妆的女人,原来那些都是他曾经历过的。我怀着好奇又与他做过几次爱,每次眼前都会出现不同的场景。唯一相同的是,这个毫无魅力可言的男主角。就好像在观看关于他的纪录片,冗长,沉闷,琐碎。一路回溯到他大学毕业那年的夏天,才终于有一点故事:他和三五个同学在学校门外的大排档喝啤酒,吃毛豆和螺蛳。他可能有点想搞对面坐着的那个扎着马尾,额头上长满青春痘的女孩,不过心里并不是很确定是否真的喜欢她。如此微弱的,游移不定的感情,在他的世界里或许已经算得上跌宕起伏。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平淡得像死人的心电图。我很快失去了耐心。九月来临,我不辞而别,拖着皮箱跳上火车,前往另外一座城市的大学报到。站在军训的新生队列里,与那些喜欢大惊小怪的娇弱的处女们一起,迎着毒辣的太阳,粗粝的迷彩服摩挲着皮肤,摩挲着那个柔软而濡湿的地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一扇门已经打开,风景从虚掩的门缝里探出头来,向我招手,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做完,才刚刚开始。
那几年,我一度放纵自己,与不同的男人尝试,检验自己的天赋是否总是存在。答案是肯定的。身体里好像有一台精密的仪器,每当男人探入进来,它的马达就会开启,伸出不计其数的触角,阅读残留在他们皮肤上的往事。它们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我看到他们从前的样子,看到他们是如何由从前的样子变成现在的样子。我看到他们的失意和辉煌,卑鄙与高尚。他们最希望展现的,他们最需要遮掩的,都在我的眼前暴露无遗。我看到,不管我是否想要看到。这可怕的天赋,令人感到不安和恐惧。可是在最初的时间里,我还来不及体会它究竟有多么危险,就已经被兴奋的情绪彻底攻陷。
我喜欢跌宕起伏的,爱恨交织的记忆。有些用世俗眼光来看很出色的男人,他们的记忆却相当无趣,乏味得像一张荣誉履历表。反倒是另外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记忆比小说更加跌宕起伏。多么可怕,我好像根本不是在和一具身体做爱,而是和一堆散落的故事做爱。我在和记忆做爱,在和逝去的时间做爱。
“我们活在二维世界里,历史被封堵,失去了时间的纵深感。所以,我们看起来薄得像一张纸片。”叶澎这样说。他没有我的“天赋”,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却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真是不可思议。在造访了他的记忆之后,我发现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就好像走进一间曾经生活过的屋子。“选择那个能够给你‘家’的感觉的男人一起生活”,女性时尚杂志这样告诫女读者,在它们给出的各种意见中,这是唯一被我采纳的一条。叶澎是听从了谁的意见我不知道,不过我们选择彼此,因为都相信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年龄相当,样貌般配,又是门当户对,双方的父母都很满意。我们相处得很自在,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过,消极和懒惰的生活态度变得更加严重。两个人都没有工作,也不想去找,似乎打算靠父母养一辈子。
杜仲出现的时候,我和叶澎已经在一起四年。我们虽然亲密,却并非无间。我总是觉得我们会忽然分开,那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两个人虽然是相爱的,却缺乏牢固的黏合力。这种黏合力或许是欲望。叶澎对做爱不感兴趣。他并没有什么障碍或者缺陷,倘若他愿意,完全可以表现得很出色。可惜这件小能为他带来的欢愉极为有限,仅有的一些,已经在对着电脑屏幕上的AV女优手淫的青春期用完了。自上大学开始,他的身边就从不缺少女孩,他和那些女孩也从不缺少有关性的研究和讨论。三十岁不到,性的神秘感已经消失殆尽。女孩的身体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其实,我周围有许多人和叶澎一样,男孩女孩都有,他们对性的摄入量很低,就像那些患上精神性厌食症的模特儿。
好在那种诡异的天赋拯救了我的欲望,让我没有变得和他们一样。没有欲望,也就没有生趣。叶澎就是这样。他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所以一直寄希望于战争或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他是向死而生的人。比英雄和烈士更加向死而生。英雄和烈士还需要谋求死亡的意义,不免有些功利,而叶澎的死亡不需要意义,来得更加纯粹。当然,这些都是在叶澎死后我才想到的,似乎是一种对他的追认。
6
那个夏天,快得好像飞快旋转的陀螺。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法语学习班,课程安排在每天下午。我一节课也没有上过,上课的时候,我都在郊外的那间厂房里。
我和杜仲,我们在古老的柜子、椅子、桌案之间穿梭,在结满蛛丝网的角落里交合。他有意延长了序曲的时间,并且显现出一种与自己极不相称的温柔。可是温柔依然套在那件馊酸的宽袖衬衫里,依然踩着像咧嘴癞蛤蟆一样的凉鞋,看起来有多么滑稽。他以为他是谁呢?他肯定以为我爱上他了,因此获得了许多自信。他卖力地亲吻着我的脖颈和耳垂,留下一道热烘烘的口水。很恶心,当然。可是必须承认,他身上的饥饿感,那种恶狠狠的气息,非常吸引我。他的饥饿感,是在过去那个性压抑的时代打在他身上的烙印。不管现在他如何饕餮也没办法消去。就像叶澎再也找不到欲望一样,杜仲怎么也没办法失去欲望。
当他操控我的时候,那种欢乐和满足,就好像操控了全世界。一个穷途末路的男人,以女人的身体作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舞台,上演着哈姆雷特式的复仇剧。他有太多想要杀死的叔父了,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侮辱了他,夺走了他的东西,迫使他对他们俯首称臣。
11岁那年,他的父亲被打死在牛棚里。同一天,他们敲掉了他的两颗门牙,好像有意要教会他以牙还牙的道理。值得说明的是,在他的记忆里,我父亲可不是什么好货色。在他父亲出事的时候,我父亲和别的孩子一块儿奚落他,嘲笑他。
13岁那年,母亲带着妹妹仓皇改嫁,留下了他,因为他太大了,又一脸凶狠,继父觉得自己没办法将他驯养起来了。他和祖父一起过。祖父不久就瘫痪在床上,墙上钟表的指针都比他的移动幅度要大。他喂他吃饭,帮他端屎端尿,对着他大声吼叫。
15岁那年,祖父终于死了,他竟然有一点难过,就好像自己饲养的宠物死了那样。
18岁那年,他下乡。喜欢上一个叫惠玲的女孩,并且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信。惠玲犹豫了一番,做出明智的选择,将信交到公社的支部书记手里。在那封信中,人们不仅读出了蠢蠢欲动的情欲,还读出了他不正确的政治立场。他被送去采石场劳改。
21岁那年,他因为得了肝炎而提前释放,大队不愿意再接收他,他就回到城里。祖父的房子被姑母一家占了,他就在院子里搭了一间简易的木棚。
22岁那年,他进了街道上的麻袋加工厂。每天缝麻袋,然后拉着板车将它们送到棉花仓库。
23岁那年,街道工厂关了,他整天游逛着,间或接一点散活。住在同一幢楼上的小莉从乡下返城。这是离他最近的姑娘,他于是与她谈恋爱。
26岁那年,他们结婚,小莉家好容易攒了一点钱,打了几件水曲柳的家具。
27岁那年,儿子小雷出世。
28岁那年,他南下,跟着几个朋友走私香烟。赚到第一笔钱。接下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买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生平第一次穿上西装,还镶上了缺失的门牙。
32岁那年,他与合伙的朋友发生内讧。几个朋友一起打压他,让他专门负责最危险的运送环节。半年后,运送的卡车在途中被警察拦截。他被逮捕入狱,毫不犹豫地供出同谋。
33岁那年,小莉很坚决地提出离婚,很快带着小雷改嫁。他在牢里和人打架,假牙脱落。
36岁那年,他刑满释放。在朋友开的小饭馆里帮忙。后来因为调戏老板娘被赶走。
38岁那年,他学会驾驶,开辆小面包车帮海鲜酒楼运送水产品。小赚一点钱,勉强够抽烟,喝酒,嫖廉价的妓女。
42岁那年,和一个寡妇同居,三个月后,寡妇卷着他微不足道的积蓄跑掉了。
46岁那年,意外与惠玲重逢。惠玲因歉疚而接济他。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于将她勾引到手。从此,惠玲常常背着丈夫与他偷情。
47岁那年,他逼迫惠玲离婚。惠玲不肯。他独自去见惠玲的丈夫,将他们的事告诉他。惠玲一家被闹得鸡飞狗跳,她终于和丈夫离婚,想要投奔他的时候,被他拒绝。他本以为自己终于报了仇,然而过了不久,患玲和她的丈夫竟然又复婚了。
50岁那年,他为一间公司开车,因为偷窃被开除。后来转为开出租车,直到遇见我父亲。他认为我父亲收留他是为了羞辱他。如果可以,他希望找个机会将我父亲弄个人仰马翻。
与惠玲重逢的一段,无疑是故事的高潮。她在他多年的性幻想中担纲主角。劳改的那几年,他的寄托是出来后向她复仇。这些令我想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政治与性的碰撞,蹿起可怕的欲望火苗。他与她做爱的时候,狠狠地打她,掐她的脖子,让她背诵当年的那封信。他们假装是躺在当年的草垛里幽会,假装被人发现,赤身裸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假装他们在众目睽睽下继续做爱……我好像就躲在围观的人群里看着他们。
但他们的疯狂将我卷了进去。我和惠玲重叠在一起,我变成了她。我和她一起叫喊着,哭泣着,窒息,休克。他抽搐着将仇恨射进我的身体里,我们一起抵达了极乐。
应该就是在那时,我被命中了。那个孩子被栽种在我的子宫里。
7
那个孩子像个阴谋,长得无声无息。我没有任何身体反应地度过三个月,才去医院检查。而后我使用药物流产,以为已经将它打掉了。后来发现它竟然还在,却为时已晚。医生们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结实的胚胎。
我不得不将它生下来。
当时,我害怕极了,只想找个人来分担。当然,这个人是叶澎。我对他撒谎,自己怀了他的孩子,现在只能生下来了。
他惊恐地看着我,好像我的肚皮里装着的是一颗地雷。我知道他不喜欢孩子。一个喜欢世界末日的人,怎么会喜欢孩子呢?可是我没有想到,孩子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他从十九楼上跳下来。“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份责任。”这是他留给我的遗言。可是,这难道不是我想对他说的话吗?我再次为我们的默契而感到惊异。或许要过一些年,我想起他才会感到很悲伤。没准儿记忆可以充当胶水,牢牢地将我们粘在一起,亲密无间。
办完他的丧事,他的父母来看望我,为他们儿子的懦弱向我道歉,乞求我能够给他们照顾我和孩子的机会。我父亲替我答允了。“如果不让他们花些精力和钱,我们可实在太亏了。”我那做商人的父亲说。
从此,我得到了“双倍”的照顾,我被他们无微不至地软禁起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杜仲,也没有想念过他。故事说尽了,他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就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讲的那样。故事里那位暴戾的国王,一定过着和我一样空虚的生活。他不要面前这位属于自己的美人,却只想听一个别人的故事。他不要价值千金的春宵一刻,却只想短暂地逃逸出此时此地。他必须脱离他自己,才有可能寻找到一丝生趣。
8
当我将那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身体里空荡荡的。杜仲就像消失在地平线上的一艘帆船,载着他的故事走向茫茫大海。
医生将紫薯色的婴儿包裹起来。他做得很吃力,因为它重得好似铅球。是个男孩。他们抱过来给我看。我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
他忽然张开嘴巴哭起来。我分明看到,他光滑的口腔正中,立着两颗糯米大小的门牙,闪着狡黠的光芒。
原载《鲤·荷尔蒙》2010年版
点评
“我”是一个会算命的女孩,不是用竹签,不是用手相,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在别人绚如烟花的青春里“我”感受到的是孤独与寂寞,因此,“我”渴望逃离现实,渴望介入到别人的生活中去,我找到了一种方式:性。“我”在一次次的性爱里阅读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阅读别人的故事成了“我”获取欢乐的一种方式。于“我”而言,性是一扇门,在那个打开的世界里“我”找到了生的价值与意义。在这篇充满文学实验意味的小说里,张悦然展现的是青春一代的孤绝与迷茫,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正常的性和爱的热情,夫妻之间亲密却并非无间,逃离现实和否定自我成为生活的常态,“我”背对丈夫和家庭继续着疯狂的探险,在一个个黑暗的深渊中飞翔又坠落。在性自由的语境下,主人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了自我的放逐。丈夫叶澎的死标志着传统婚姻和性观念的死亡和终结,而杜仲的消失和婴儿的出世也打破了主人公虚幻的逃离梦想,被迫回到冰冷的现实,这是青春一代的叛逆和迷茫,也是现实的生存之殇。
(崔庆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