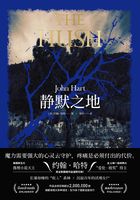吴君
曹丹丹有个愿望,就是能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不是出差旅游看风景,拍几张相片便走那种,而是像北京人那样,早晨看日出,晚上看日落,除了正常吃饭,饿的时候,吃一条街边买回来的煎饼果子和豆浆。当然住的地方要在十二条或是它的周边。房间简单舒适,出门方便。门的左边挂自己喜欢的小画框,右边挂上从丽江带回来的蜡染信口袋。床上铺的也是喜欢的图案。这些情景早在脑子里想过多次。有了这,哪怕天天吃糠咽菜也行。至于以后还回不回来再另说。愿望在心里埋了很久,差不多快要打包封存之际,被江艳萍重新挖了出来。
曹丹丹有半年时间没有联系她。哪怕再空虑,也忍着,她不愿跟她联系。她觉得这个女人太做作,声音娇滴滴,喜欢抢别人风头。同是女性,谁受得了这个。直到那个闷热的下午,当时没有风,天上也没有一片云彩,她正拿着一沓学生作业走神,犹豫着是把这有限的钱放进股市还是在深圳关外买间七万元的单身公寓之时,按到了江艳萍的信息。她说,她准条离开深圳,去北京发展了。曹丹丹对着这条信息发了很久的呆。有几个学生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她记不起后面的时间是怎么过的。
当晚曹丹丹便失眠了。江艳萍的话好像在报复谁一样,不仅报复了深圳,还报复了她曹丹丹。要说对深圳的恨,曹丹丹未必会比别人少。如果不是因为女儿太小,转学麻烦,也许早离开这里了。现在凭什么她江艳萍说走就走,把她一个人留在这个没有四季的城市里。要走也应该是一起走才对啊。过去怎么说的,在那些酒后或是失眠的夜里,两个人计划了多少啊。最后她就这么被抛弃了。江艳萍这么做,曹丹丹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她甚至觉得一天都待不下去。
去北京是自己的梦想啊。想了半辈子,却被别人实现了。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江艳萍。她的心里空空落落,充满了挫败感。毕竟江艳萍的条件一直不如自己,哪个时期都不如。她在心里掂量过很多次,只这一次,人家便赢了。如果没有江艳萍垫底,曹丹丹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沉到了谷底。十二条十二条,黑暗中,翻来覆去睡不着,用卷舌音念了好几遍,这是她在梦里去过无数次的地方。一下火车,慢了性子走,路上见到有人遛鸟,唱京剧。过了两条街,便拐进一条胡同,胡同边上有个椭圆形的水坑,积着雨天留下的脏水。虽然是脏水却能映出天上的云朵。为了方便过路人,那里永远放着几块石头或砖头。坑的另一头便是那地下室的门了,进了门就能见到被水泡得卷了皮的墙壁。要弯了身子走路,否则会被头顶上的水管子撞到。终于听见了一句,谁呀,声音很熟。正想着是谁的时候,便醒了,原来自己做了个梦。梦里的情景跟当年一样。那是十五年前班里有个叫刘涛的同学病了,学校派人送他回家。因为病是在学校得的,家长不接,跟学校吵,非要学校把人送到北京做了检查定了性才行。没办法,班主任只好找了两个同学跟着,需要有个女的,说是女生做事细。作为老乡曹丹丹便跟着来了。没钱住酒店,只好住了二十块钱的地下室,有的人当晚流鼻血了,可她没事。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她把这种喜欢藏起来,压迫着,不让任何人看出来。她甚至希望得病的不是刘涛而是自己,这样可以多些时间住在北京。睡不着的时候,曹丹丹脑子里总有洗漱室大镜子上的水蒸气和一个个半裸着上身的男人。看不清人的相貌。那些雾气,很是难忘。更关键的是见过雾气之前,她在胡同里见过一个长得像小流氓一样的人,骑了辆自行车,一只脚平放在地上,另一只则踩在脚镫上。他冰冷着声音问曹丹丹想不想跟他回去。
曹丹丹当时傻气,学着对方的卷舌音问,跟您回去干什么啊?
做我媳妇儿吧,对方换了只脚放在车镫上说。当时天气异常闷热,不远处好像还有知了和另外的一些鸟在叫。天上灰蒙蒙的。曹丹丹记得那男孩长了双细小的眼睛和胖胖的脸。
不行!曹丹丹撒欢似的跑了。她比什么时候跑得都快,不是害怕,而是快乐。那是她平生第一次有人跟她说这样的话,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她到了深圳,到了男女比例为一比七的城市。如果不是江艳萍,她会把愿望藏起,让自己现实起来,毕竟这是深圳,一天不去赚钱心就慌就会死的城市。就这么想啊想,翻了几个身,天就亮了。第二天站在镜子前刷牙,对着自己的黑眼圈,又轻轻念了一次,十二条。声音从干燥的嘴唇里出来,显得软弱无力。对着镜子又发了会儿呆,不知道要做什么。直到台湾佬也醒了,窸窸窣窣站在门口等着用卫生间,曹丹丹才想起今天还要替人多上一节课。中午还要去商场买个相机,他说要去大理采风。
不能用手机么,像素也很高。她说。
那不好看啊,人家都有真相机。台湾佬有些讨好地看着曹丹丹。他是个台湾人,失业后到了大陆,住在珠海。网上认识了,便搬过来住了。
曹丹丹听了,心烦得很,倒不仅仅是钱的事,主要是想起他吃住不花一分钱,还口口声声大男人大男人的。这让她不舒服。如果不是男女比例失衡,她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她常常对江艳萍说,女人到深圳,都会被打折,谁也不例外。过了三十五就不是打折问题,而是倒贴。什么世道呀。她差点要说,到深圳后从没有一个人跟她提过结婚,包括前任也是逼到对方没路了,才结的。多数人只想上床而不想负责。之前什么甜言蜜语都敢说,如果稍稍矜持下,他连争取一下都不会,马上向后转了。如果遇人不淑还要“呸”你一口。当然罗老师不是这种人,关于结婚的话,至少提了不下五十回。江艳萍也有同感,觉得深圳不适合女人。两个人为此还喝醉了,说了许多平时没说的话,当然包括曹丹丹的秘密,北京,十二条。
我支持你!真的。江艳萍眼泪汪汪。仿佛也是她的十二条。她的这副表情让曹丹丹反倒冷静下来。她觉得自己不能跟谁都走得太近,尤其是江艳萍这种,既不是同学又不是老乡,只是饭局上认识的。
曹丹丹对着台湾佬说,最近我心烦,你回避一下吧。她又下逐客令了。每次心情不好,都会让他回去住。她不想与人交心更不想和谁吵架。
“原来那个房都退了,再找也要花点时间。”显然台湾佬对这个临时决定有些不满,手里端着牙刷,上面是刚刚挤出的牙膏,想和曹丹丹再说几句。
曹丹丹径直走出门,不看对方一眼。她怕对方再啰唆。江艳萍的事,让她心乱。之前她都有些想妥协,跟台湾人结婚算了,反正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了。现在想法又变了,她觉得台湾佬身体和钱包都不行,连买个小东西都要她出钱。如果结婚,自己很不合算,等于白养一个人。
一出了门,就把电话打给了江艳萍,确认-下,去北京的事是不是发错了,或是心血来潮之举。因为在她眼里这个江艳萍做事没谱,就是发信息也是一会儿风一会儿雨,总是要表现自己浪漫的一面。上次还说要拯救某个贫困县的妇女,说她们太苦了,有的连县城都没去过。曹丹丹心里想,人家未必是苦,再苦还能有深圳女人苦吗?还有一次,说要报名去西藏支教,她这么做的目的,也能理解,就是让曹丹丹羡慕,毕竟她只是个代课老师,一天到晚拴在学生身上,哪也去不成,稍有闪失,饭碗就不保了。江艳萍是个营养师,平时总是飞来飞去,在全国授课,难见人影,每次都是她约曹丹丹,而曹丹丹却难约到她。要么就是在外地呢,要么就说正在上课,不方便。曹丹丹觉得这种关系让自己很被动,想了几次不来往了没意思,可最后还是交往了四五年。
她对着电话说,你这个决定真是太好了,深圳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痛苦指数应该排全国第一。我早想离开了,你看看那些外省人,都去海南了。
显然这话没什么逻辑,江艳萍在电话那端笑了说,我是去北京,不是海南,又不想炒房。顿了下,她换个口气说,深圳也不错呀,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城市。曹丹丹听了这话,很不舒服,如果以往,会顶她几句。当然这种机会也不多,平时说话江艳萍都是请教口吻。看起来人一阔脸就变这话不假。曹丹丹心里不服,可嘴上还是不争气,说了句,你这一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江艳萍说,北京也欢迎你呀。曹丹丹想到了对方小人得志那副样儿,就想给自己一个耳光,不光自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虎落平阳被犬欺,还不争气表现出了下贱。放下电话,心里堵得慌,明显觉得江艳萍是气她,好像她已经是个北京人一样,随便就可以同情谁。
刚拐上四楼,就见到了走廊上的一个男孩。曹丹丹猜测他等很久了,也许他又带来了母亲的什么亲笔信。
有事吗?她心里软了下,这个初二男生得了抑郁症。喜欢浓妆的母亲哭着求过曹丹丹帮忙。有一次拿了三千块钱让她收下,被曹丹丹拒绝了。学校明文规定,不能当家教。已经有政策解决代课教师的转正,这个关节上一定不能出错。给这个孩子补课,除了拿些外快,也有同情的意思。
你愿意再来陪孩子吗?他只听你的话,找谁都不行。平时我不在家,可以让他爸爸陪你。这女人临行前对她挤了下眼睛。曹丹丹心想,真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把老公都拿出来交换了。不久前还鼻涕眼泪地向她哭诉,自己男人多花心。
她摸了摸男孩的额头,想问他吃药了没有,就见男孩笑了,说,老师,你能不能不这么煽情。不过我爸喜欢你这种款。
去你妈的!老娘懒得理你。曹丹丹头也不回,在心里骂了句,便进了教室。教室没有因为她进来而安静。曹丹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想,这地方真是没法待了。
正式听江艳萍说北京的事,是曹丹丹为她饯行的晚上。看着江艳萍满面红光的样子,她故意装作不在乎,眼睛继续瞄着电视,耳朵听着江艳萍说话。附和的人没几个,都是男的,彼此不认识,更不知道怎么表态。电视里正在重播征婚节目。虽然这个节目与她的生活没关系,那里全是三十以内的美女。她总是把女主角当成自己,试图去选择那些勇敢的男生。她正在为节目里的六号惋惜,就听见江艳萍说自己那位是个北京人,有一幢三百平米的别墅,曹丹丹把全部的身子坐回位子上,虽然装出了不在意,眼睛却已经细细打量对方了。
江艳萍披肩下面是一件紧身的旗袍,头发梳成民国时期样式,口红是深色的,甚至连举手投足也是那种范儿。如果在平时,曹丹丹根本不想听她说话,不愿意看见她拿足了姿态去表演。她在心里冷笑。她觉得江艳萍没有任何进步。最初的时候,她穿的是纱,而这种纱,人们早用来做窗帘布了,后面则改成穿旗袍,但像她这种干瘦的身材,把缺点都放大了。这种表现需要成本,就是必须有观众有饭局。比如这次饭局又是她张罗的。当然这次不同,不是生日,不是庆功,是为她送行。冲动之下曹丹丹主动提出了买单,当然过后也会后悔,毕竟自己的钱也要掂量着花。江艳萍那边娇气地说多谢老姐啊。曹丹丹心里想,自己是被江艳萍发出的声音忽悠了。她甚至怀疑她是从声讯台学来的,温柔缠绵。生气的时候会在心里笑话她,你对一个同性温柔什么呢。每次放下电话,曹丹丹都忍不住在心里说,做作的女人。尽管她们是几年的朋友,可是她不习惯对方的做人做事。比如她的厚脸皮,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出风头。当然两个人在一起,她不会这样。可能是共同语言说完了。主要的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她喜欢热闹,非要去人多的场合。每次都有些不认识的面孔。如果一帮朋友吃饭,哪怕中间只有一个熟人,被她知道了,无论多远,她都能找到。有次一个女孩儿过生日,是个小老板张罗的,显然对那个女孩有点意思。来的时候,江艳萍还带了本挂历给请客的人。曹丹丹就是这个聚会上认识的江艳萍。过生日的朋友是个单身,看见浓妆艳抹的江艳萍马上不高兴了。江艳萍倒也不客气,坐下来便展示自己的挂历,那是一本印着甲骨文的挂历。这种字体,没人认识,场面显得有点尴尬。随后她又向座位上的男人们派发名片。一边递名片,一边介绍自己单身,琴棋书画样样拿手之类。一圈还没走完,寿星女的脸就黑了,饭局被江艳萍搅了。比如她还对曹丹丹说虽然离了婚,却还是把婆婆一家从农村接过来住了。
曹丹丹惊讶,你不是单身了吗?
是啊,可我跟他们一家还是好朋友啊。说话的时候,江艳萍眼睛散在各种菜上,最后夹了一小条黄皮鱼放进自己碗里,慢慢挑着刺。
这样一来,曹丹丹就很生气。江艳萍让关外的人口素质更加低下,让女性打折的事实继续下去。她心里想,关外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不仅聚集了各路妖魔鬼怪,还批量出产一些伪小资。
有一次,江艳萍心急火燎地约她,说要介绍个女孩给她认识。认识一下吧,我的小姑子,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曹丹丹冷笑着回答,你没病吧,他们一家那样对你,她哥哥抛弃了你,你却让我成为她的朋友。她差点把矫情这个词用上。
她样子非常恳切,说,要是你不想认识,你给她介绍几个朋友也行,或者吃饭的时候带上她。
什么?曹丹丹半天说不出话。江艳萍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奇怪。
为了缓和气氛,曹丹丹转了一个话题,你上次说你要学釉彩最后怎么样了?
江艳萍看着自己的手指说,早毕业了。
什么时候你送我一张画啊?曹丹丹说。
我已经改学琵琶了。显然她对这迟来的发问有些不满,画画是两年前说的事。
过去曹丹丹一直对江艳萍画画有些不解,在她眼里那种东西必须科班出身,更重要的是要有才华。她调侃江艳萍,对了,你说的那个人怎么样,他是不是卖画的?
什么卖画,俗,人家那是专家。她更正了说法。随后又说,是我亲密爱人。她目光温柔了许多。
你再婚了?曹丹丹有些一头雾水。
显然她不愿听到“再”这个字,扬了扬左边的眉毛,说,他是鉴定明瓷的学者。她的声音已经显得有些干燥,没有一点水分。
这句话如同一把榔头,把曹丹丹刚刚还气呼呼的身体砸瘪了。她怯怯地问了句,他对你还好吧?
哎,好得让人受不了,太黏人,总怕失去我,把我当宝贝。这样一来,我只好从家里那儿搬出来,也算成全他们吧。那一对人也真可怜,东藏西躲的。她指的是前夫。
原来这样啊,曹丹丹倒抽了口冷气,原来是她主动扔了男人。她心里想,嗯,不错,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办事就是麻利。
说话的时候,客人陆续到了。曹丹丹只是欠了欠身子。江艳萍便站到门前去迎了。
都坐下后,又进来了一个小个子,穿着曹丹丹讨厌的白衣服白裤子。江艳萍硬是把这人请到主位上。他刚一落座,眼睛便盯着曹丹丹问,你还记得我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所有人都听见了,他叫出了她的名字。
曹丹丹礼貌地笑了笑,没说话。
他报上他的名字,方荣。
曹丹丹眼睛发着呆,还是想不出这人是谁。
我记得你,当年你在电影院门前等人,我路过,你还对我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