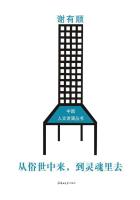临近傍晚时分,秦觉远伫立在秦淮河畔,默默注视阴沉沉的天空中,伴着寒风翻卷落下的鹅毛大雪。他身后站在两个脸蛋冻得通红,不住呵气暖手,跺脚,年约十一二岁上下的小丫鬟。
“秦爷,风雪这么大,姑娘他们今儿大约会在栖霞寺留宿了。”
桃叶缩紧冷风直灌的脖颈,搓搓手,跺几下冻得麻木的双脚,瞧瞧周围提早打烊的店家,小声提醒。
她原名大丫,和妹妹小丫俱是土生土长的江宁六合山里人,前几日刚被人牙子卖到这户据说是从京城里搬来的董姓富商家中。
虽然只在董家待了几日,她也没见过多少大世面,但桃叶隐隐约约察觉出七七一行人并非像他们说的一般,仅仅是京城里经营了几家商铺的普通人家。光是看李爷、秦爷、詹爷他们对董姑娘毕恭毕敬的态度,桃叶便觉得她服侍的那位小姑娘来头不小,於是,与七七说话愈发显得小心谨慎。
秦觉远掉过头,看了两眼冻得浑身发抖的两个小丫鬟,心思一动,微微笑道:“你们俩先回去烧点热水候着。保不准过一歇他们就回来了。”
在北边待久了,习惯屋子里一到冬天便烧热坑。秦觉远初回江南的几日,还真有些不大适应南边沁骨入髓的湿冷。后见七七和李甫他们都没说什么,他也就忍下不说了。
性子活泼的桃根一听可以回去了,急忙拉拉还在犹豫的姐姐桃根,圆乎乎的小脸蛋上露出恳求。桃根看看冻得受不住的妹妹,低下头,朝无视风雪的秦觉远蹲身拜谢,姊妹俩抱在一起,顶着风雪,一步一滑地走回去。
桃叶桃根走后没多久,一辆藏青色呢子的马车,在李甫、詹德奎他们的护卫下,沿着石板路缓缓行来。
七七端坐在马车中,静静分析孔四贞透露的消息,吴三桂在云南五华山府邸的规模堪比紫禁城,俨然是一个分工明细,次序井然的小朝廷。山后头的库房里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堆了十来间,他不但雇用了工匠私自铸造钱币,还在锻造各式兵器。据说武器库房里的剑、枪、弓矢都堆得放不下了。
这些信息里究竟代表了些什么意思?自是不言而喻了。
眼瞅着情势越来越不利于己方,七七的阵脚也禁不住乱了。她很害怕由于她的介入,历史会朝着不一样的角度前进。若真是如此,那康熙将来的路会愈加曲折艰辛。静默半响,她撩开帘子的一角,窥看秦淮河两旁的动静,视线凝在一道不顾风雪伫立在堤岸旁熟悉的颀长人影身上。
“李甫,你过去同秦先生讲一声,让他先回屋子里去暖暖手脚吧。”她软软的声音很快就被冷冽的寒风吹得支离破碎。骑马守在车旁的陈潢听了,微笑赞许。
李甫闻言,持着缰绳驱马赶到秦觉远跟前,翻身下马,拱手道:“觉远兄,劳你费心在外等候了。”
秦觉远冲青骢马上的陈潢点点头,微微笑道:“不妨事。倒是你们一路辛苦了。没遇到什么事吧?”他朝着马车望望,例行问了句。
“路上救了一个冻僵了的喇嘛,因带着不方便,便请栖霞寺的僧人代为照看了。”李甫简略的回答。
“喇嘛?这事倒有点蹊跷了。”南边甚少见到喇嘛,秦觉远惊讶之余,不免生出几分疑虑。
“觉远兄也如此认为?”
李甫因受了宫刑,朝廷里边的大小官员面上讨好巴结,然一转身,人人都把他看成长公主养的一条狗。秦觉远、吴六一他们都是性情爽直的人,丝毫不会因他受过的刑罚而低看他。
秦觉远眼光一亮,追问道:“你可是查到什么要紧的线索了?”
李甫斟酌下,缓缓道出心中的疑惑:“他嘴里的呓语仿佛是在喊额吉,还提到了什么父汗,准葛尔部什么的。依他的话语来断,他有可能是蒙古准葛尔部台吉的儿子。我曾听长公主提过,不少蒙古人喜欢到西藏的喇嘛寺里学习……”
这时,一阵瘆人毛发的哭声悠悠荡荡地随风飘荡在空中,紧跟着,又是一阵哭天抢地的打骂声,俩人寻声望去,只见一名披头散发,哭哭啼啼,衣衫不整的少妇被一群人推搡拖拽着往江宁府衙的方向走去。
俩人侧耳静静细听,听到周围看热闹的街坊邻人都在小声议论,说是那女人命苦,嫁给了一个痨病相公不算,还摊上了一个伤风败俗的婆婆刘氏。那病痨鬼死的真是冤那!可怜他媳妇年纪轻轻的守寡不算,还要背上人命官司。
俩人听了几句,相互对望一眼,不约而同的转身回家。这种事,不是隐名埋姓藏在乌衣巷里的他们能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