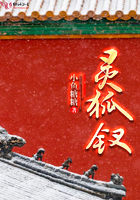“呸呸呸!”王美蓉骂他,“你个乌鸦嘴!”
吃完饭李虎把同学们安排到茶馆喝茶,打麻将,他要带吕悦去看三岔河“天翻地覆”的变化。
“你喝了那么多酒,”吕悦说,“快回家休息吧。”
“别啊,你难得回来一趟。”李虎替她拉开了车门,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你行吗?”吕悦犹豫着。
“说谁不行啊?”李虎说。等着上车的同学听见他的话,哈哈笑起来。
“没事儿,我天天这么喝,你放心上来吧。”
吕悦上了车,车里面弥漫着浓重的酒味儿,好像有瓶他们没看见的酒洒在车里了。
他们在市区里转了转,李虎问吕悦想去哪儿,她想了想,“以前我们住的房子还在吗?”
“在。”李虎边答边掉转了车头。
二十年前,吕悦住过的这栋三层红砖楼是三岔河县的标志性建筑,住户除了县领导,就是吕悦妈妈这样从省里来的专家。“小红楼”如今破败不堪,住户们在窗外拉起绳子,晾晒着衣物,楼前的水泥花坛残缺不全,里面被人种上了白菜和小葱。
“佳人已乘黄鹤去,”李虎跟着她下了车,伸了一个懒腰,“此地空余黄鹤楼。”
“你还挺酸的呢,”吕悦笑了,“像个文艺青年。”
“我是陪我儿子背古诗时,背下来几首诗。”李虎说,“上学的时候哪正经上过课啊,天天跟正明打篮球了。”
“走吧。”吕悦说。
李虎带吕悦去看市旅游局刚开发出来的景点,景点在市郊,车子停在松江边儿上一个新崭崭的凉亭旁边,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定情谷。
吕悦四下看了看,问李虎:“定情谷在哪儿呢?”
“那儿!”李虎指了指前方的一处崖壁。
那处崖壁像一幅宽银幕从山上垂挂而下,直至松江,青山隐隐,绿水悠悠,确实是处好景致。
“看那上面,像不像有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李虎指着崖壁,“像不像小龙女和杨过?他们身后那两条岩缝,像不像两把剑?我们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正好是雨季,岩缝里有流水,被阳光一晃,真是刀光剑影啊。”
“那也不能叫定情谷啊,定情崖更贴切点儿。”
“对,下次我让他们改过来。”
回来的时候李虎带吕悦顺路去了他的煤矿。李虎的煤矿很大,是中等国有煤矿的规模,挖掘出来的煤堆得像山一样。见李虎来了,两个面色跟煤差不多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李虎给他们递烟,三个人把烟抽完的时候,李虎的事情也交代得差不多了。他扔了烟头,用鞋底碾碎,走过来指着矿井跟吕悦说:“别看只有这一个入口,里面却有五条巷道呢,从山的底部插了进去。”
“像一个魔爪。”吕悦笑着说。
晚饭王美蓉请大家吃狗肉。她自己经营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狗肉馆,在三岔河市小有名气。她让朝鲜族厨师现杀了一条五十多斤的黄狗,用喷火枪烤光了狗毛,烧焦炭架大铁锅,锅里面添加了各种香料、几味草药,以及黄豆、辣椒、干白菜丝炖了四五个小时。
店里弥漫着热气和湿气,直扑到人脸上来。
“闻到狗肉香,”有人感慨,“神仙也跳墙啊。”
“我们是小本买卖,条件简陋,”王美蓉跟吕悦客气,“跟李虎比不了,人家是大老板大手笔。”
“我还有大的东西呢,”李虎冲王美蓉笑,“你想看看不?”
“去死!”王美蓉笑啐了李虎一口,请大家入席。
“看,”李虎让吕悦坐在自己身边,指了指吧台说,“白蛇传。”
店里吧台上有个特别大的玻璃罐子,里面泡了几棵人参,一只灵芝,还有一青一白缠绕在一起的两条蛇。
“好玩儿吧?”王美蓉笑嘻嘻地说,“今天咱就喝‘白蛇传’,这酒可有劲儿了。”
吕悦又恶心又害怕,直摆手。
李虎给小武二平打电话,让他们送几箱特级松江醇过来,还特别嘱咐他们给吕悦带两瓶五味子酒来。
“一样是老同学,”有人打趣,“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店面小,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光坐着都会流汗。几盆狗肉汤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房间简直变成桑拿房了。狗肉汤炖得绵长浓香,一碗热汤喝下去,汗湿衣衫。席间有人间或感慨了几句杨正明的英年早逝,但大家主要的话题都放在了同学情谊上。有一个男生跟吕悦单独喝了杯酒,说:“当年,你是咱们学校的林青霞啊。”
“可不是嘛,全校有一半男生都在暗恋吕悦。”
有一个小地痞头目也看上了吕悦,带着几个兄弟来学校,并跟以杨正明、李虎为首的班级男生打过一次群架。“那真是场硬仗。”有人冲李虎笑,“你的头上还有个疤呢吧?”
“可不是?”李虎把身体屈向桌面,指了指自己头顶上的一块疤,“正明管这道疤叫马里亚那海沟。”
“我怎么不知道呢?”吕悦很吃惊。李虎受伤的事情她有印象,他以前上学时总穿他哥哥的旧鞋,那些鞋又大又旧,趿拉着,他的头上缠了绷带,斜背着个破旧的书包,像个俘虏惹人发笑。
“他们也没占着什么便宜。”李虎说,“我那块有机玻璃板你们记得吧?格尺那么宽,有一厘米厚,玻璃板的尖角正好敲到那家伙的脑瓜顶上了,那血呼啦涌出来,跟个红盖头似的把他的脸都盖住了,我当时以为把他打死了呢。”
“我也以为出人命了呢。”
“幸亏正明他爸是副县长,有公安局长替我们撑腰,要不然,那些地痞不血洗了县一中才怪呢。”
“那天打完架是正明陪我回家的。”李虎说,“我爸万万没想到我跟县长的儿子是好朋友。那次他非但没因为我打架揍我,还对我刮目相看,让我妈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吃呢。”
“。是因为我吗?”吕悦难以置信,“你们没弄错吗?!”
“当然是因为你!”有人说。
“有一段时间晚上放学的时候,总有一些男生跟在你后面,你记不记得?”
吕悦记得的。因为这些男生的尾随,她妈妈还拿话敲打过她,要她自尊,自爱,自重,还含沙射影地讲了一些生理卫生方面的事情。她又委屈又憋闷,好几天吃不下饭,对跟在她屁股后面的男生面寒如霜,怒目相对。
“那都是为了保护你,怕那些小流氓对你下手。”
“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王美蓉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真不知道。”吕悦说。
“吕悦那会儿对正明都不正眼看,不知道也很正常。”李虎说,“她不食人间烟火嘛。我记得有一次咱们去东山秋游,在山上野了一天,都滚得跟泥猴儿似的。下山的时候一溜儿土坡,路陡得收不住脚,到了山底下休息时,咱们都把鞋脱下来,磕鞋窠里的土啊小石子啊什么的。吕悦脱了鞋,脚上的白袜子雪白雪白的,我和正明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咱们一样爬山,一样下山,别人都是两脚泥,她的袜子怎么就能跟两只小白兔似的呢?”
事情一做完,吕悦就起身去浴室了。
花洒喷出来的凉水让她一激灵,但她没躲开,任由凉水冲刷着头发,直至冷水转温,温水又转热,水流变成一件大衣,从头到脚覆盖,拥裹住她。
她的头还是晕的,酒精让她血液发了疯,在血管里面横冲直撞。但在她身体的内部,在某个房间里面,意识黑衣黑面,在对她刚刚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你怎么能跟李虎上床呢?
是很愚蠢。她承认。
吕悦洗了好半天,一遍又一遍地打浴液。她没带浴衣进来,她用两条毛巾把头发缠好,把两条浴巾全扯了下来,一个裹紧身体,另一个披肩似的搭在肩膀上,她从镜子里面打量自己。非洲病人。
打开门,她先听到李虎的鼾声,像漏气的手风琴,伴随着咝咝的呼气声,高一阵低一阵地响着。房间里弥漫着酒和香水百合混杂的气息,既暧昧浓烈,又含混污浊。她的目光渐渐适应了房间内的光线,家具、物品、鲜花、水果,从幽暗中显露出轮廓。她从自己的箱子里找出干净的衣服,抱到小客厅里,仔细穿好。被李虎从她身上扯下来的衣服,散落在床的四周,她一件件地捡起来,这些衣服像路线图,勾勒出事情发生的脉络。李虎的手劲儿很大,身体很硬,哀求她的时候却像个小孩子。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他受了委屈似的叹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让我这样。”
她试图把他推开的时候,摸到了他头顶上那个“马里亚那海沟”,她的理智在那一瞬间踉跄了一下,栽进马里亚那海沟里去了。
吕悦在小客厅打开了一个壁灯,烧水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她的身体很疲惫,脑子里像个蜂房,无数的蜜蜂在跳舞。蜜蜂是用跳舞来表达思想的,吕悦的思想却变成蜜蜂般的碎片儿。她需要理顺一下思路,让飞舞的蜜蜂回到各自的蜂巢。在远方城市里当大学教授的生活,时不时地,会让她觉得沉闷无趣,但当她的视线从三岔河出发时,她发觉她的象牙塔生活如此高雅脱俗,气度雍容,那些刻板的秩序、规定,从远处看,像一块块古堡的基石,确保了生活的稳固和安全。
好吧,吕悦对自己说,她回三岔河参加了一个葬礼,就让这个葬礼把有关三岔河的一切都埋葬掉吧。
喝完咖啡,吕悦打开了窗子,夜风像歌剧里面绵长的高音,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悠远,而风声的下面,松江水流淌的哗哗声,则是乐队不眠不休的演奏。
吕悦醒来时,发现自己仍旧躺在沙发上,阳光明媚,从窗外直泻而入。她的身上盖了一条毛毯,她掀开毛毯坐起身时,毛絮在阳光里面跳动着,宛若显微镜下的细菌。
她看了眼表,快中午了。
吕悦洗漱完毕,化好妆,刚要收拾行李,有人敲门。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没舍得叫醒你。”李虎举起手中的袋子,“新鲜的苹果芒,特别甜。”
李虎的T恤衫也是黄色的,质地精良,衬得他的皮肤越发的黑红、粗糙。吕悦想象了一下他穿着这身衣服,开着“宝马”越野车出现在她学校的情形,偶尔遇上她的同事,他再甩几句古诗,那可真够热闹的。
李虎把芒果拎进卫生间洗了洗,甩着水珠出来,他没找到合适的盘子,把芒果放到了功夫茶茶台上面。他从卧室把水果刀拿出来。“我来吧。”吕悦把刀接过来。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吕悦坐下来,拿起芒果削皮。
“急啥啊?好不容易来一趟,”李虎在她身边坐下,“多住几天!”
“我是来送送正明的,”吕悦往后挪了挪,专注于手头上的刀和果皮,“事情办完了,当然得回去了。”
“正明的事儿办完了,那我的事儿呢?”
“你的什么事儿啊?”
“你说呢?”
吕悦抬起头,把削好的芒果递给李虎。
“一个芒果就把我打发了?”李虎接过芒果时问。
“芒果是你的,”吕悦又拿起一个芒果来削,“你自己打发自己。”
“到底是教授啊,”李虎笑了,“说话跟俄罗斯套盒似的。”
吕悦没接他的话茬儿。
李虎往她身边凑了凑,“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
“你胡说什么啊?”吕悦又往后挪了挪,后背顶到沙发扶手了。
“那就是瞧得起我了?”李虎又往前蹭了蹭,“我要是追你,能追得上吗?”
吕悦放下手里的芒果,身体朝后倾斜,看着李虎,“你真的离过三次婚?”
“当然了。”
“为什么?”
“抵挡不住诱惑呗。现在的女孩子都老生猛了,话直接给我撂到桌面儿上了,她们有美貌和青春,我有金钱和智慧,大家资源共享,OK不OK?哪有像你这样儿的,跟个果子似的挂在树尖尖上,只能看,不能摸。”
“我和你认识的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吕悦打断了李虎,清了清嗓子,“我。昨天的事情是个意外,是一场梦,现在天亮了。”
“天还会再黑的。”
李虎注意到吕悦的脸色,收敛了笑容。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李虎咬了一口芒果,从茶几的纸盒里面抽出几张纸巾接住滴落的果汁,“真他妈甜!你尝尝。”
“你先吃吧。”吕悦示意了一下手里正削着的芒果。
李虎把芒果吃完,把果核扔到纸巾里,随手放到茶几上。
“昨天的事情倒不是什么意外,但咱们这个年纪了,经历的不少,见过的就更多,谁还会为谁一片丹心在玉壶啊?正明倒是惦记了你一辈子,算是海枯石烂了。那有啥用啊?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你,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起这个人。”
“你别胡。”
“就是这么回事儿。”李虎说,直视着吕悦,“你敢说,你想起过三岔河吗?想起过杨正明吗?当初我们差点儿为你把命丢了,你不也不知道吗?”
吕悦说不出话来。
“你看你刚才紧张的,脸绷得跟个石膏像似的。”李虎笑,“你怕啥啊?怕我纠缠你?像电影里那个男的似的,天天上你们家楼下喊,吕悦,我爱你。”
房间里面突然沉寂下来,静得能让吕悦听见“吕悦,我爱你”发出的声波在空气里微微震动着,她也能听见李虎的心跳声,以及自己的心跳声,她还能听见窗外,松江水水流的声音,仍旧像乐队的伴奏,从容舒缓。
李虎的眼睛向下看着自己的胸部,惊异的表情好像那把刀不是吕悦捅进去的,而是刀自己从他的身体里长出来的。
“我不知道怎么会……”吕悦也看着那个刀把,她也觉得那把刀是自己长出来的,“我只是想让你闭嘴!”
原载《作家》2009年第10期
点评
《三岔河》的故事始于三岔河当年的高干子弟。“副县长”的儿子杨正明的葬礼,在“同学情谊”的感召下,一群中年人跨越了20年的时光,努力将岁月长河中关于青春期的记忆捞起来,装裱成册,用来感动自己和他人。那些年三岔河的男生一起追的女孩。吕悦,作为从省里来的专家的女儿一直鹤立鸡群,是20年前三岔河懵懂少年的梦中情人,而她自己显然对这段经历早已淡漠。20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杨正明遭遇了父母先后去世、与妻子离婚并且无子的人生,在对吕悦的回忆中耗尽了时光,最后面目全非地殒命于车祸。而当年那个平头百姓的儿子李虎却混成了财大气粗的“虎哥”,俨然三岔河的风云人物。
故事的前半段进行得波澜不惊,吕悦顺理成章地成了众星捧月的焦点,“虎哥”的侠骨柔情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一众亲友的赞许。颇具戏谑讽刺意味的是,在杨正明尸骨未寒的时候,“虎哥”就急不可耐地把这个已故同窗倾注了一生情感的女人抱到了自己的床上,看似酒后乱性实则处心积虑。吕悦显然只想把这一夜情缘当成一个错误的插曲,而李虎却口出狂言,于是一把水果刀进了李虎的胸膛。小说自始至终没有交代吕悦现在的情感婚姻状况,原本温情的同学聚首,却落得以如此狗血的情节收场,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的可能。
(王秀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