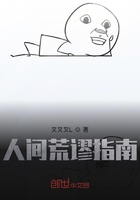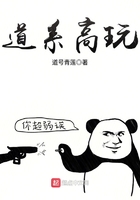“学校外面的铁道口又出了一件事故,”祝平副教授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一个20来岁的姑娘。”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一下,像是在犹豫什么。他于是吸引住教研室里全部的人。
教研室约有20多平方米,位于庞大教学楼的6楼右侧。这时在教研室里坐着的还有周去副教授,于布教授,以及同样是副教授的诗人罗派昂。他们本来什么都没有干,可也并不想集中注意力听某一个人说话。他们很少集体听一个人说话,一般只是两三个人交谈。有时候某位老师在传达街道新闻时也是这样,只有这位老师面对着的那位在听,其他的即使听到了,仍只装作没听见。这会他们都看着祝平,这情形就有了一点意思。并不因为祝平老师有什么号召力或特别的吸引力,他只是个50出头的男性教师,脸色昏暗,形容憔悴,绝对没有什么看头。
罗派昂觉得自己肯定是第一次这么明确地观看数年的同事祝平,一直以来尽管每星期起码都要见上一面,却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罗派昂一向认为祝平副教授的相貌极符合一个由一体化时代过来,清贫、受冷落、如今畏缩着又被激发了贪欲、时而满腹牢骚的平民知识分子模样,现在他更细致地证实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这几年大多数的人都老得快,教研室的几个人眼见得胖的愈胖,瘦的愈瘦,祝平老师自然更是如此,他的两颊过早地有了几点老人斑。罗派昂感叹着。罗派昂不知道于布和周去老师怎么看,他转过头,发现他们两位注意的不是一回事。
周去说:“那个铁道口真奇怪呀,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他一直关注着事件,这样他当然不会细看祝平。
于布则说:“什么姑娘?”不知他刚才想什么去了,话只听明白一半。姑娘二字倒对他仍有诱导的力量。
“刚才我从街上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穿过铁道口的时候,正好有一个火车头过来……”祝平开始叙述他的经历,以便带出他所见的那个事件。在这时刻,罗派昂的视线滑出了窗口。罗派昂正好站在窗边,他一边听着祝平讲,一边就去看窗外。
窗口对着学校大门,经过花圃,近处有一条河流平静地展现着自己绿亮的表面。河那边建着一些俗气花哨的民房,有的两层,有的三层,都贴着瓷砖。再远去是连绵的小山坡,山坡上隔一段距离竖着高压电线杆。有一座山坡被挖开了,露出浅红色的岩石来。视线再往右边点,那里房屋密集起来,一条大马路引导着房屋的排列走向。这是一幅支离破碎的靠近郊区的城区风景图,画面混乱不堪,但由于在阳光下,倒有着印象派画的明亮与确切。
罗派昂的目光像一张透明水中的空网,由远向近逐步收回,却惊讶地停滞在学校大门口。他分明看见校门口和门内的小广场上有许多人拥推着向外走,差不多每个人手中都提着装有一条大毛毯的透明印花塑料包。广场上旗帜摇曳,半空间飘荡着硕大的气球,球下吊着大幅标语,上书:“庆祝XX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罗派昂一时惊奇不已,因为校庆已是八个月前的事。那时是深秋,现在已接近初夏。眼前景象如此逼真,那些提着学校赠送的大毛毯的人都是校外的来宾,他们显得兴高采烈。校内的老师们大致都很平静,他们也领到了每人二百元的资金,只是觉得理所当然。那些天,老师们依然表情呆滞(在与来宾们比较之下显示出来的)地走进教学大楼,讲完课后离去。反正罗派昂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眼下这一景象重又出现,像是被复制出来。
复制的场景就像梦境,罗派昂这时仔细地看,那些提包的人都像木偶一样机械地鱼贯而出,然后在视觉的边沿处消失。就像在电影画面上。
罗派昂定了定神,他感觉到周围十分的安静,没有一丝声音。画面中这么多人没有喧闹声,就好像那些人的动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现实凸块一样。这是现实中最经常出现的场面,意义已懒得充实其间了。他也能体会到自己事实所处的教研室这个小空间,可他也没有听到祝平继续说话的声响。
他于是努力将视线朝幻觉(他认为是幻觉)的画面深处推去,如要穿透它。这会他办到了。他到达了不久前系里举办的一次学术报告会的会场,他坐在第七排的旁边位子。那次的确是这样,他想。接着他果然看见第一排坐着特邀的学校各关键部门的领导们,如他努力记忆起来的一样。会议开始了,主持人请系主任讲话,而后那些领导们按序轮着讲,然后主持人宣布老师进行学术报告,第一位报告的老师向讲台走去,这时那些第一排的人基本都站了起来,他们面带微笑,朝会场门口鱼贯而去。在门边他们停了一下,每人领取了一个信封。那里面是50元钱。后来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会议结束,蜂拥出的老师们也在门边停了一下,每人领到30元钱,没有装信封。赤裸裸的这点钱。由于我们听完了报告,所以减去了20元,罗派昂当初想。现在他已经感觉到那种自嘲的幼稚性和轻浮。
仿佛视线又一次扑空(罗派昂的意念带着他的目光像水一样在溢出,随意地往低处流漫),疲倦了,落回到真实、温暖、可依靠的场景中来。
罗派昂现在看着教研室的窗台,阳光让上面的积尘变得非常清晰有层次,还有一股暖烘烘的干土味。他没有回头,也还没来得及想自己刚才是怎么回事,怎么尽跑到毫无相干的事情上去了(从相反的艺术观念思考,也许那是生存的最明确背景,如别的小说里所常选择写的——此处括号内语由作者注,并非罗派昂所思),像在唱歌中跑调一样,而且跑得很远。眼下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啊,他意识到这点,因为他已经又在听见祝平说话的声音。祝平说:
“我走到火车道口的时候,阻拦行人与车辆的横木已放下来。当时那个穿着鲜艳毛衣和格子布裙(这家伙看女人倒够细致的,真没想到,罗派昂听到这里时想,我还以为他最关心钱呢)的姑娘就从我身边挤到前面去。我看见她低下头,又弯下腰,穿过陈旧的横木走到了铁道当中。那时一个火车头由右边过来,离道口还有十几米的样子,它开得并不快。”
说话的人喘了一口气,好像挺费力似的。——实际上,罗派昂从瞻望窗外失去听觉能力到他恢复听,他不曾漏掉祝平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听到的仍是连续的叙述,“我走到火车道口”一句紧接着上面断掉的那句,并没有间隔。他的意念漫溢只是瞬息间。或者说不占据现实中的时间。——现在,周去、于布和罗派昂都已经集中起注意力来听祝平的讲述,他们都已经想知道那个姑娘接着会怎样。
当然在座的每一个老师都熟悉那个铁道口。那段铁道与学校外边那条大马路并行,铁道在靠学校一侧,通向校门的路又与大马路垂直相交,如此从市内出来必须越过铁道才能到达这所大学。建立有一根横木的道口就这样形成了。为便于行走与车辆开过,道口的铁轨间还铺着水泥路面,铁轨嵌在水泥路面间,当中有一道可容火车铁轮经过的缝隙。
难道这样一条缝隙会是致命的吗,或者是道口的其他一些物体,自然最有可能的是来回奔驰着的火车。火车的力量太巨大了,哪怕仅仅是一个车头,它只需随便这么擦一下或推撞一次人的身体,后果就可想而知。罗派昂这时候的推想紧紧围绕着铁道口(似乎他在有意控制自己),他已经回过头朝着事件的述说者祝平,但他没有看祝平,也没有看其他两位老师。他观看着事件本身(这有待于继续听)和它发生的处所。
他想起那段铁路其实很少有火车开过,似乎是某个大工厂的专用线,一天顶多有三五趟,其中两趟可能还只是一个车头而已。铁轨都生锈了,没有主干线上被磨出的光亮,尽管那亮光总也显得很沉着,但到底使人感到有一股锐气。这里却是另一回事。行人倒常常喜欢沿着这段铁路走,而有意不去走与它并行的大马路的人行道。马路上灰土太大,密集来往的汽车进一步卷起尘埃,令人难以呼吸。铁道和它的两边则生长着杂草,初夏更开满着各种细小的花朵,尤其那些紫色的小喇叭花,成片成群,呈现着另一种勃勃的生机。它对行人,对年轻的大学生们,对教师,对恋人都是一种诱惑。
大概在前一年吧,罗派昂的记忆猛然清晰起来。他在记忆里状画着当时并非亲历的一件事故。
黄昏的时候,人们以为这段铁路上不会再过火车了,一般情况下也的确如此。那是五月,一对女孩(一年级的女大学生)在离那个道口不太远的铁轨上坐着闲聊,她们因此没有丝毫警惕性。生命的提防程序被关闭着(在这和平的年代,又有几个人不会这样呢)。她们俩的手上都采集了一束深紫色的小喇叭花。这些细致的花朵和她们谈论的东西,以及说话时的情态何等融洽。她们全然没有感觉到一个火车头正在朝她们驰来。是什么细碎的生存记忆与话语能让人如此沉迷于其中,一个蒸汽火车头的巨大声响和路轨的震动都没有使她们察觉从而产生惊慌。这不是一个极大的谜,那些交谈中的事与语言,包括声调,大多数人都会熟悉。没有真正值得迷醉的内容,也就是说,生命在没有重量和意义的时刻恰恰放松着自己,直至放弃。罗派昂作如是想,他闭起了眼睛,不欲看见其后的景象。可他更清楚地望到了,又一次,看到过去的事物。
无比坚实笨重、过时的暴力的蒸汽火车头冲压过来时,那一瞬间空气被可怕地犁开,挤压向四周和前方。矮小的植物同样倒伏下来,它们顺应着那股力量,避免了被摧折与粉碎。司机没有看到前面有人坐着,那些花朵和草丛扰乱了他的视觉。两个女孩在最终的刹那感受到了撞击,但主要是车头前面被剧烈压缩的空气的冲击(她们可能已经惊恐地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她们幸运地被预先向一边冲击出铁轨,只有一个女孩的手臂在火车头的挡板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柔软的手臂立刻破裂开来,小块骨头和一部分肉体溅飞起来。那些碎片与喇叭花的花朵混合在一起向空中洒泼。谁也没有看清这个情景,黑夜几乎刹那间过来淹没住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