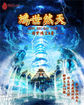那个深夜我坐在火炉前感觉到睡意不断袭来,巨大的睡意连寒冷都阻挡不住。实际上寒冷在鼓动着它,我的想象因此时时被构织进梦幻的边缘。这使我想到对于生命,冰冻很难被判定为一种打击,它倒更像仅仅针对灵魂的引导。它弃置躯体不顾,将心灵诱向无形之地,这个过程缓慢而绵长,几乎令人感动。那晚车厢的铁板温度已降至最低,车厢内的货物全被冻得缩小了。四个青年挤成一团,可他们之间的那点热气连塞寒流的牙缝也不够。他们只好各自收缩起来,这就像那些没有生命的货物一样了。他们一动不动,当他们意识到该动动时,已经动弹不得。他们都已不想说话,可以说他们过早地进入自我的心灵内取暖,将自己的身体弃置到了一边。他们的灵魂被引诱、被拖得很长,躯体便渐渐冷却下去。我差不多能够看到车厢内飞舞着众多由冰冻所致的人的梦幻,有彩色的,灰色的,它们不断出现,又飞速地被冻结收缩成一个个黑点。
那晚还没有到深夜,事情就临近结束。那节车厢的空间最后在增大,由于所有的物体都在缩小,包括那些梦幻。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很纯净,像水流的冻结,最后获得的是加倍透彻的冰。没人听到有什么声响,包括那些可能嘈杂的无声的梦。只能说他们遭遇了死亡,当他们在梦境中直接走进一片黑暗时。对于他们来说,这里面如果具有困难的性质,那也只是梦魇的,虚幻不实的,就像梦中经常都会出现的艰难奔跑。他们没有实际的疼痛与恐惧,因为这不是死亡刻意到达的方式。
我当然无法想象出他们众多的梦境图像,我仅仅按约定俗成的路子想,那里面会出现火吧。是不是还会有雪原和马匹,这个念头令我一惊。仿佛死亡一下子濒临我的生存之地。我猛然惊回到那个平静的积雪夜晚,我和我那位年长的朋友还有以下一段对话。其时我们默然无声地策转马头,背朝着铁路,继续前行。无风的原野显得更加空旷与寂静,我不由紧紧地偎着马脖子,仿佛要以此来取暖,或获得同伴。终于还是我打破静默问道:
“他们常常出现吗?”
“不。”我的朋友回答说,“只在积雪的夜晚,听到马蹄声响时。听说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在西面牧马。”
“可今晚雪这么厚,马蹄无声啊!”
“是的。”他叹息了一声,接着鼻子嗡嗡地说:“雪吸收了马蹄音,又把它们传向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具有过分浪漫的虚指成分在内。我想起来,这有可能成为那晚我们继续前行时,却迷了路的原因。本来那两匹马据朋友说是去过我们要去的那个农业团驻地的,可两匹马一齐把方向给弄错了,它们背负着我们在茫茫雪野上驰骋的结果,是远离了目的地。后来我们只好照原路返回,照着我们自己的马留下的马蹄印。我发现路上别无任何痕迹,这让我想起雪今晨刚停。难得的积雪之夜,我们失去了目的地,可独占有了依然纯净的处女雪野。这种含意的发现,使这次空旷间的骑马之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致它后来竟在梦中延续。因为我想不起我们是怎样回至营地的,那个结尾似被我的记忆抹去了。
我也一直没弄清四个青年的尸体为何会被扔在这段路基上,以后又怎样被收走的。这对我并不重要,对死者其实也一样。死者不需要什么善后与完整的结局,或诸如此类的什么。死亡与其说是个结局,不若说是对结局的放弃。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段路基的确与死亡非常贴近。就在第二年的秋天,我的另一个接触不多的同乡朋友也选择在此处卧轨自杀了。没有什么重大的原因,只是对于陌生、艰辛的高原生活,他过早地失去希望,也不愿猜想未来可能的改变。当然也可能他对包含改变在内的生活整体失望。总之,他在一个太阳高悬、无比明朗的上午悄悄离开正在挖地干活的众人,独自走到了那段铁路上。他知道十点钟有一趟客车,他在那里有耐心地等了二十分钟。这段时间里,他把外衣脱下叠好放在一边,然后跪在路基上等着。列车自然刹车了,可惯性还是冲过来,死亡就坐在惯性上。他被停留在第五节车厢下,断成了三大块,一些零星小块则飞溅到路轨外,其中有他的心脏与肺叶。
或许这终归是些琐碎无奇、一般的生命剥离状态,我曾经不无苦恼地想。平庸岁月里的暗淡死亡,如此无声无息,只占据着极小的空间。它们似乎经不起思考的磨砺,就已成为碎末。其意义单薄,我唯恐穿透这层薄膜,便触摸到一派虚空。我其实就在这样一种接近沮丧的心情中,萌生了追问意义厚重状态所在的迫切念头。那段时间我大半由此热衷于阅读历史。果然在那里面布满着死亡,死亡甚至是主要的环节。我偶然在一册粗糙的历史文本中读到这样一段措辞枯燥,实则应该惊心动魄的文字:
“罗伯斯比尔派掌权时期,对“左派”的反对和右派的攻击,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一七九四年三月逮捕企图发动暴动的阿贝尔等人,并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同月,丹东及其同伙也被逮捕,经审讯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四月间,政府根据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处死了萧梅特。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共和二年热月九日)在巴黎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等被捕,第二天,罗伯斯比尔和其他二十二人未经审讯被送上了断头台。”
二百多字,所述时间仅几个月,断头台这个词就出现三次,另外一次用处死一词代替。这给我们指示了明确的死亡道具,它与铁路或寒流全然不同。它是死亡直接的手段,历史在此处由于死亡的密集而浓缩。这是否就加重了死亡的质量?或者说,我在这里期待到了什么?我最终并没有解决我所携带的问题,没有满足我对历史的渴求。我有了更多疑惑。我觉得死亡在这里面仍然是一种轻,对生命来说,这种方式的惊心动魄之处在于迅速。由于它身处历史更体现出这一点,如此而已。
我所熟悉的死亡却似乎处在弥漫的(群众的?)空间中,它们是单个生命漫步中的时而相遇。它们只需打动我这样的个体,我得以此为足。我这样想,就会停止那种不会有结果的追寻。
现在我该来写写我后来的梦境,在那里我继续着那次骑马之行。我说梦,是由于我不能区别梦与曾经的现实间的差异,它们都是记忆。我记得我和那位比我稍稍年长的朋友各骑着一匹马奔跑过雪原,朋友那匹马仍是白色的,我的马变成了棕红色。我的马个子高大,在雪地上像冲天而起的火焰,它就那样活泼地跳跃着,向前急驰。我在马背上能感觉到那种火热和悬空朝前的振奋与快感,有几分钟,这样的状况是以慢镜头的速度进行着的,它使我渴望梦境持续、渴望时间停顿。
之后我的背景不再是一片雪地,也没有夜空,它完全成了一种黑色,或者说无色的状态。朋友的白色马在前面渐渐消失,像穿越某种东西的包裹而逝。我一点也不惊慌,我知道我在等待着一道空隙出现,它必将出现。在此之前,我仍得在此黑暗中奔舞(此时我身下的马匹踊跃如在舞蹈)。我将遭遇死亡,但我不再会看见那些死者的身影和死尸的碎块,在无色中什么都看不见。
这样的情景在我继续生存的岁月里我又经历过几次(我的睡眠多梦),每次都相同,后来一直是那匹棕红色的马驮着我,这种场景总在无比的快感中戛然而止,但不令我失望。我永远不记得我们如何回到营地,当我们发现迷路时,两匹马已朝另一个方向跑出很远,我们起码要用相似的时间跑完归程。可我记得我一直没有跑完它,无论那是现实还是梦。直到那个时刻到来,我策马而入,我想我可以将之称为一次通过生存的虚隙。